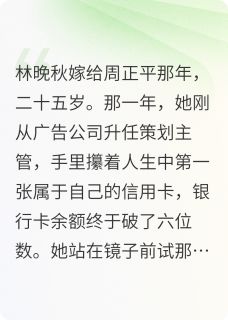
林晚秋嫁给周正平那年,二十五岁。那一年,她刚从广告公司升任策划主管,
手里攥着人生中第一张属于自己的信用卡,银行卡余额终于破了六位数。
她站在镜子前试那件红底金丝绣花的旗袍时,手指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
而是因为一种近乎仪式感的期待——她终于要嫁人了,不是为了逃离原生家庭的压抑,
也不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洞,而是因为她以为,自己真的找到了可以共度余生的人。
周正平是她大学学姐介绍的相亲对象,比她大三岁,做IT项目管理,收入稳定,性格温和,
说话不急不躁。第一次见面,他在咖啡馆点了一杯美式,没加糖,也没看手机,
全程认真听她讲工作上的烦心事。临走时,他替她拉开椅子,说:“你说话的样子,
像春天的风。”她笑了,心却悄悄动了一下。三个月后,他们决定领证。没有盛大婚礼,
只请了双方父母吃顿饭。她说:“民政局一进门就领证,不拖泥带水,
才像我们这种务实的人。”他点头:“对,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演出来的。
”那天阳光正好。她站在民政局门口等他,穿旗袍,踩低跟鞋,发髻挽得一丝不苟。
阳光斜斜地洒在她脸上,照得眼角微微泛起细纹——那是熬夜改方案留下的痕迹,
也是二十五岁女人无法回避的真实。可她不在乎。她笑起来像春水初融,眉眼弯弯,
唇角一点红,像蘸了胭脂的笔尖。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美得刚刚好,不多一分,不少一寸。
周正平来得迟,衬衫领子歪着,头发乱糟糟的,手里拎着一袋刚买的煎饼果子。
他咧嘴一笑:“等久了吧?客户临时改方案,跑晚了。”林晚秋没怪他。她接过煎饼果子,
咬了一口,脆皮在嘴里咔嚓作响,芝麻香混着酱料的味道在舌尖炸开。她说:“没事,
反正今天也不上班。”他笑出声,牵起她的手走进民政局。工作人员问他们要不要拍纪念照,
他摇头:“下次补。”她却悄悄想:**这大概就是我要的一生了——平凡,
但踏实;没有轰轰烈烈,却有细水长流的暖意。**两人领了证,去附近小馆子吃了顿火锅,
辣得满脸通红,喝了一瓶啤酒。那天晚上他们住在婚庆公司包的“蜜月套房”里,
床单是粉红色的,墙上贴着“百年好合”的剪纸。周正平喝多了,搂着她说:“晚秋,
我这辈子就认你一个女人。”她信了。她真的信了。结婚三年,
林晚秋把日子过得像一碗温热的小米粥——不烫嘴,也不凉心。她每天六点半起床,
熬粥、煎蛋、切水果,把周正平的西装熨得一丝不苟。他出门前总要亲她一下,
说句“老婆辛苦了”,声音低低的,带着刚睡醒的沙哑。她喜欢听这句话。喜欢到每次听到,
心都会轻轻颤一下。她曾偷偷录下他说这句话的声音,存进手机备忘录里。
夜里睡不着的时候,就拿出来听一遍。**那声音像一把钥匙,打开她心里某个柔软的抽屉,
里面装着对婚姻的所有幻想与信任。**周末他们去超市采购,推着购物车在生鲜区转悠。
周正平挑排骨,她挑青菜;他拿啤酒,她拿酸奶。结账时他总会多买一盒巧克力,
说是“给老婆的小惊喜”。回家后两人窝在沙发上追剧,她靠在他肩上,
他说:“这样的日子,过一辈子也挺好。”林晚秋点头,心想:是啊,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变故是从一条短信开始的。那天她洗完澡出来,
顺手拿起周正平放在床头的手机回微信。屏幕亮起,一条新消息跳出来:“今天晚上还来吗?
我买了你爱喝的乌龙茶。”发信人备注是“小陈”。林晚秋愣住。她记得这个“小陈”,
是周正平公司新来的实习生,二十出头,齐肩短发,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上个月团建,
她还见过一面,小姑娘穿着白T恤牛仔裤,站在周正平旁边拍照,笑得格外甜。
那时她还笑着对同事说:“你们领导带新人真上心啊。”对方打趣:“可不是嘛,
天天一起加班。”她当时只当是玩笑。可现在,这条短信像一根针,猛地扎进她心里。
她手指僵在屏幕上,心跳像被什么攥住了,一下比一下重,一下比一下疼。她盯着那行字,
反复读了好几遍,仿佛只要读得够多,就能让它变成别的意思。“还来吗?
”——说明这不是第一次。“我买了你爱喝的乌龙茶”——说明他们之间有共同的喜好,
有默契,甚至……有生活。她忽然想起最近几周,周正平总说“项目赶进度,要加班”。
她曾体贴地给他送过夜宵,结果他在电话里说:“别来了,客户在,不方便。”她信了。
她甚至为自己的善解人意感到骄傲。可现在呢?她没点开聊天记录,也没翻相册,
只是默默把手机放回原处,躺下关灯。那一夜她睁着眼到凌晨两点,
听着身边人均匀的呼吸声,第一次觉得这张床陌生得像别人的家。
**她问自己:我哪里不够好?是我胖了?是我不再精致?还是我太安静,
不像那个女孩笑得那么甜?**她翻了个身,背对着他。黑暗中,眼泪无声滑落。
第二天周正平照常上班,临走前还摸了摸她的脸:“晚上想吃什么?我带回来。
”她笑着说:“都行,你看着买。”他走了。门关上的那一刻,林晚秋坐起身,拿起手机,
点开那个“小陈”的微信头像——一张对着镜子**的照片,背景是办公室玻璃墙,
阳光洒在她脸上,青春得刺眼。林晚秋翻了翻朋友圈,
全是健身打卡、咖啡拉花、周末露营的照片。最新一条是三天前发的:“加班到十点,
有人陪我吃夜宵就好了。”配图是一碗泡面,旁边摆着一瓶可乐。她冷笑一声,退出来,
删了好友。但她没闹。她知道,闹了也没用。周正平那种男人,嘴上认错比谁都快,
心里照样我行我素。她妈常说:“男人偷腥,就像狗闻屎,闻一次就想第二次。”可离婚?
她没准备好。她还想赌一把。于是她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做饭、洗衣、陪笑。
周正平似乎也察觉到什么,那阵子格外殷勤,下班早了,还主动洗碗。她以为他收心了。
直到那个雨夜。她加班到九点,打车回家。小区门口路灯坏了,她撑着伞往里走,
忽然看见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楼道口。车窗半开,里面坐着两个人。是周正平。
他搂着一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正低头亲她脖子。女人仰着头,笑声清脆,像银铃。
林晚秋站在雨里,伞歪了,雨水顺着发梢流进衣领。她没动,也没喊。她只是看着,
像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电影。直到那辆车开走,她才慢慢走上楼。钥匙**锁孔时手在抖。
屋里漆黑一片,她打开灯,看见茶几上放着周正平的手机——他忘了拿。她走过去,解锁,
点开微信。聊天记录还在。“今天能不能去你家?我老公出差了。”——是那个女人发的。
“别急,等我找个理由回来。”——周正平回。下面还有一张照片,是卧室床头柜,
上面摆着一只青瓷花瓶,插着几支干枯的玫瑰。林晚秋认得那只花瓶,是她去年生日,
周正平送的礼物。她坐在沙发上,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那是她的卧室,她的床头柜,
她的花瓶。而现在,那个女人正躺在她的床上,用着她的杯子,呼吸着她丈夫的气息。
**她忽然笑了。笑得肩膀发抖,眼泪却没流下来。她想:这婚,不过也得过,过也过不好。
可我林晚秋不是软柿子,捏扁搓圆任人摆布。既然你敢在外面风流,那我也不是泥塑木雕。
她开始悄悄攒钱。她本就在广告公司做策划,收入不低,但婚后一直由周正平管账。
她借口要报瑜伽班、买护肤品,每月从工资里抠出五千块,存进一张不常用的银行卡。
又把旧首饰、名牌包挂上网卖,三个月攒了八万多。她还重新练起了瑜伽。
结婚后她胖了十斤,腰身松了,脸上也少了光泽。现在她每天五点起床,跑步五公里,
回家做三十分钟拉伸。她买新衣服,剪了短发,染成深栗色,衬得皮肤更白。
同事都说她像换了个人。她只是笑,不说原因。她等的是时机。机会来得比她想的快。
那天下班,她路过一家咖啡馆,透过玻璃窗看见周正平和那个“小陈”坐在角落。
两人靠得很近,女孩的手搭在他手臂上,正低头笑。林晚秋没进去。她转身去了对面商场,
买了一条酒红色丝绒连衣裙,一双细高跟鞋,又去美容院做了个**护理。晚上八点,
她化了精致的妆,喷了香水,发了条朋友圈:“三年没跳舞了,今晚重出江湖。
”配图是她对着镜子拍的背影,裙摆微扬,锁骨线条优美。十分钟不到,点赞上百。
有个叫“沈砚”的男人评论:“惊艳如初遇。”林晚秋认识他。是大学学长,比她大五岁,
离异,做艺术品投资,朋友圈常晒拍卖会、古董字画。他们加了微信但从没聊过,
只偶尔点个赞。她回了个微笑表情。半小时后,他私信:“真去跳舞?我正好在城西会所,
要不要来坐坐?”她回:“好啊,地址发我。”她知道这一步跨出去就回不了头,
可她不在乎了。会所藏在老洋房区,门口没有招牌,只有青铜门环。侍者引她上二楼,
推开一扇雕花木门。沈砚坐在窗边,穿深灰西装,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他抬头看她,
眼睛亮了一下:“比照片还好看。”音乐是爵士乐,低沉慵懒。他邀她跳舞,她没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