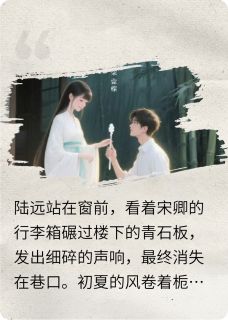
陆远站在窗前,看着宋卿的行李箱碾过楼下的青石板,发出细碎的声响,最终消失在巷口。
初夏的风卷着栀子花的香气涌进来,却吹不散客厅里残留的、属于她的气息,
反而像针一样扎进心里。“你心里的那个人,从来不是我。”她离开前的声音还悬在空气里,
像根细刺,扎得他喉头发紧。可他分明将整颗心都捧给了她——从高中教室的并肩刷题,
到大学图书馆的默契对视,他们早约好毕业就去领红本本,让出租屋的墙染上喜字的暖。
他甚至已经看好了城郊的小公寓,首付凑得七七八八,
钥匙就藏在书架第三层的《婚姻法》里。变故藏在那些被月光拉长的夜里。
宋卿第一次听见他梦呓时,正蜷在他怀里数窗棂的影子。“阿晴,等我。
”那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在她心上砸出个坑。她僵着身子不敢动,直到天光爬上窗帘,
才敢悄悄转头看他的睡颜。睫毛在眼下投出浅影,和平日里没什么不同,
可那声“阿晴”像生了根,在她脑子里盘桓不去。“阿晴是谁?”她第二天问,
指尖攥着他的衬衫衣角,指节泛白。陆远把她揉进怀里,下巴抵着她发顶,
胡茬蹭得她颈窝发痒。“卿卿,我们从校服走到学士服,从学士服走到婚纱。
你是我这辈子第一个想娶的人。”他顿了顿,声音里带着笑意。“许是你把‘阿卿’听岔了?
我夜里总念叨你,说不定舌头打结了呢。”宋卿望着他眼底的坦荡,
劝自己是夜风吹乱了听觉。她甚至找闺蜜反复比对“晴”和“卿”的发音,
在得到“确实有点像”的答案后,偷偷松了口气。直到某个凌晨,
她再次被“阿晴”两个字惊醒,睁眼正对上陆远的目光。那里面的失落像潮水,
漫过她的脚踝,瞬间淹没了所有侥幸。他大约是刚从梦里醒来,眼神还蒙着雾。看清是她时,
那雾里浮出的失望太真切,让她想起小时候弄丢了最喜欢的布娃娃的自己。
“我们……算了吧。”宋卿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敲碎了满室的寂静。陆远伸手想抓她,
却被她躲开,指尖只擦过她的袖口,空落落的。宋卿走后,陆远把自己关在屋里。
窗帘拉得密不透风,外卖盒在脚边堆成小山,手机屏幕暗了又亮,最终只剩一片死寂。
他反复回想宋卿的话,翻遍了二十多年的记忆,阿晴是谁?他的人生里从来没有这号人物。
可那句梦话像诅咒,盘旋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不知过了多久,他的低血糖犯了,
以前他就不在乎这些,总觉得坐下缓一缓就好了。可宋卿总是担心,
包里每次都会准备一些糖果。这次就剩下陆远一个人,一阵天旋地转袭来。
他像被扔进滚筒洗衣机,头晕目眩,慢慢的,他失去了意识。再睁眼时,
雕花房梁正垂着蜀锦帐幔,鼻尖缠着淡淡的檀香。“这是……”他踉跄着下床,
酸枝木拔步床的凉意透过薄薄的月白长衫渗进来。脚踩在冰凉的青砖上,他打了个寒颤,
低头看见自己穿着宽袍大袖,袖口绣着暗纹,陌生得像别人的身体。铜镜里映出张熟悉的脸,
只是短发支棱着,与这身古人装束格格不入,像幅被泼了墨的工笔画。
“吱呀——”木门被推开,逆光里立着个少女。十七八岁的年纪,湖蓝色绫裙扫过地面,
裙摆绣着的梅花似要落进风里;同色短袄外松松系着月白宫绦,羊脂玉玉佩随动作轻晃,
撞出细碎的响。她发髻梳成望仙髻,金累丝嵌猫眼石簪子垂着珠串,扫过脸颊时,
倒比窗外的日光更晃眼。“果然醒了。”她挑眉,声音脆得像嚼冰糖,带着点娇纵的好奇。
这是林府大**林晚宁。前日她替父亲施粥归来,
见他穿着“怪衣”(后来陆远才知道那是T恤牛仔裤)倒在府门前,怕污了门楣,
便让人拖了进来。“想拿你原来的衣服?”林晚宁指尖划过楠木小几上的琉璃灯,
灯光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先还九两医药费——诊金、药钱、还有这几日的饭食,
一分都不能少。”陆远摸遍了身上的口袋,只摸出半块皱巴巴的纸巾。他张了张嘴,
想说自己身无分文,却看见林晚宁眼里的狡黠。“没钱也简单,”她转身朝门外走,
裙裾扫过地面像流水,“留在府里干活抵债。明日起,随我去城外施粥。”陆远别无选择。
在这个没有时钟的时代,日子像被抻长的棉线。他跟着下人们扫地、劈柴,
听着晨钟暮鼓判断时辰,夜里躺在通铺的硬板床上,总想起宋卿煮的番茄鸡蛋面。直到某天,
他在花园角落撞见林晚宁——她正蹲在石凳旁,手里转着个竹蜻蜓,
阳光穿过叶片落在她发顶,镀上层金边。那竹蜻蜓的螺旋桨是竹片削的,转轴磨得光滑,
分明是现代孩子的玩物。陆远的心脏猛地一跳,冲过去时带起的风差点掀翻石桌上的茶盏。
“这东西哪来的?”他抓住林晚宁的手腕,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林晚宁被他吓了一跳,
甩开手揉了揉腕子:“凶什么?是虞姐姐给的。”她见陆远眼神发直,补充道,
“虞姐姐住在城外山里,医术很好,就是性子冷淡,不爱见外人。
”陆远看着自己被甩开的手,猛地发觉自己失了礼。再怎么说,这也是林府的大**。
看到林晚宁也没责骂他,且目前自己也有事求得她帮忙,他回了回神,
毕恭毕敬道:“我能做更多这样的东西,”陆远的声音略微发颤,
“纸飞机、陀螺、七巧板……你能不能让我见见她?”他有种预感,
这个“虞姐姐”或许和他一样,是不小心掉进这个时空的“异类”。
林晚宁摇头:“虞姐姐不喜欢被外人打扰。”陆远瞬间蔫了,好不容易找到“同类”,
不能轻易放掉这条线索啊。而转机藏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意外里。那日午后,
林晚宁在池塘边喂鱼,不知怎的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水里。惊叫声刺破了林府的宁静,
下人们慌作一团,却没一个敢下水——这池塘去年刚淹死过一个小厮,大家都怕得很。
陆远赶到时,只看见水面上漂浮的湖蓝色裙角,像朵被打湿的花。他想都没想就跳了下去。
五月的水还带着凉意,浸透了粗布短打,冻得他牙齿打颤。林晚宁在水里扑腾,双手乱抓,
好几次差点把陆远也拖下去。他想起大学游泳课学的技巧,绕到她身后托住她的腰,
尽量避开她的手。“别慌!”他大声说道,声音被水呛得断断续续,“跟着我呼气!
”岸上人影晃动,有人扔下来竹竿,可林晚宁已经吓得没了力气。陆远咬紧牙关,
踩着水将她往岸边推,每划一下,都感觉力气在流失。他的眼前开始发黑,
耳边是自己粗重的喘息和林晚宁的呜咽,直到后背撞上石阶,
才有人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拉上去。陆远瘫在草地上,大口喘着气,全身冻得青紫,
牙齿不住地打颤。他看着林晚宁被丫鬟们裹着棉被抬走,意识模糊前,
只听见林父的声音:“这小子……倒还有些用处。”林晚宁醒来后,
对陆远的态度彻底变了。她不再叫他“抵债的”,偶尔还会让丫鬟给他送些点心。
三日后的傍晚,她坐在花园的秋千上,晃悠着双腿说:“我可以帮你带件东西给虞姐姐。
但她见不见你,我可保证不了。”陆远几乎要跳起来,他向林晚宁道谢后回到自己的住所。
连夜找来了宣纸和竹片,裁、折、粘,指尖被竹片划破了也没察觉。天亮时,
他手里攥着只纸飞机——机翼被他细心地涂上了朱砂,像只展翅的红鸟。
林晚宁看到纸飞机时,眼里闪过丝惊讶,随即又恢复了平静。“虞姐姐也有这个,
”她接过纸飞机抛了抛,“去年我去看她,她窗台上摆着好几个呢。”陆远的心沉了沉,
又拿出连夜削好的木制陀螺:“这个呢?她也有吗?”林晚宁点头:“有。比你的还精致,
上面刻着花纹呢。”陆远盯着自己手里的陀螺,忽然笑了。他抬头看向林晚宁,
眼里闪着奇异的光:“我知道该送什么了。”他凑近她,声音压得很低,
“我要送她一个只有我们那个……只有我才会的东西。”三日后,林晚宁带着陆远上了山。
马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林晚宁掀起车帘,指着远处云雾里的竹屋:“虞姐姐就住那儿。
”她转头打量着陆远,眉头皱了皱,“你确定要这样?要是被虞姐姐发现了,
怕是要把我们赶下山。”陆远摸了摸脸上的八戒面具——那是他自己打磨了三天做的,
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下巴和嘴唇。为什么不做孙悟空的?三天时间太赶了啊。
孙悟空面具的细节又太多了。“只有这样才有机会,”“那这个面具的作用是?
”林晚宁疑惑问道。他深吸一口气,“你的虞姐姐不是不喜欢外人到访吗?
这个是我们那的国民男主的师弟。如果她和我是老乡,她一定会有所顾及,
不会轻易将我拒之门外的。”陆远解释道。“你放心,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竹屋藏在竹林深处,周围种着药草,空气中飘着苦香。
一个穿月白长袍的女子正蹲在竹篱边捣药,素手握着石杵,动作轻缓,
阳光穿过竹叶落在她身上,像笼着层光晕。她二十二三的模样,头发高束成髻,
只插着支普通的木簪,几缕碎发垂在颈边,随着动作轻轻晃动。“虞姐姐!”林晚宁跑过去,
声音里带着撒娇的意味。女子抬起头,陆远的呼吸瞬间停了。她的眉眼很淡,
像水墨画里晕开的墨,可那双眼睛……清澈得像山涧的泉水,却又藏着化不开的忧愁。
陆远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既熟悉又陌生。“小宁怎么来了?”女子的声音很轻,
像风吹过竹林。她的目光扫过陆远,带着几分警惕。“给你带了个礼物,
”林晚宁拉着女子的手,朝陆远使了个眼色,“保证你喜欢。”陆远深吸一口气,
随着记忆里的旋律动了起来。那是他小时候被母亲逼着学的双人舞,本以为早就忘了,
此刻肢体却像有了自己的意识——旋转、踮脚、伸手,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无比。
他不知道虞晴能不能看懂,只知道这是他唯一的机会。石杵落在地上的声音惊飞了枝头的鸟。
虞晴站在原地,眼睛盯着陆远的动作,身体竟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她的动作比陆远更熟练,像排练过千百遍,两人的指尖在空中相触又分开,旋转时衣袂翻飞,
像两只纠缠的蝶。一滴泪落在虞晴的手背上,冰凉的。她猛地回过神,后退一步,
撞在身后的竹架上,药篓里的草药撒了一地。“抱歉,”她别过脸擦了擦眼睛,
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公子的舞姿……让我想起了故人。”陆远摘下面具,
心跳得像要炸开。“虞姑娘,”他往前走了一步,“你认识我,对不对?或者说,
你认识‘我们’来自的地方?”虞晴的目光落在他脸上,瞳孔骤然收缩。
她手里的药杵“哐当”一声掉在地上,嘴唇哆嗦着,像是要说什么,最终却眼前一黑,
直直地倒了下去。“虞姐姐!”林晚宁惊叫着扑过去。等虞晴醒来时,想再看看那个人。
“来人,将陆远叫进来吧。”林晚宁吩咐道。“小宁,你说他叫……叫陆远?
”虞晴听到这个名字后,抓着林晚宁的胳膊,急声问道。“是的,姐姐,您先别激动,
丫头一会就叫进来了。”虞晴听后,理了理头发,安静地坐在床沿,
指尖抚过腕间的木簪——那是几年前的新婚夜,他消失后留下的唯一物件。
簪子的木质温润,刻着朵小小的梅花,是他亲手雕的。侍女走进来:“**,门外无人。
”“他怎能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林晚宁还想说些什么,虞晴轻轻按住她:“此生能见一面,
足矣。”她对守在床边的林晚宁说,声音轻得像叹息。窗外的竹影晃了晃,像谁的脚步。
消毒水的味道钻入鼻腔时,陆远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宋卿趴在床边睡着了,
眼下有淡淡的青黑。他动了动手指,她立刻惊醒,眼里的红血丝像蛛网。“你醒了?
”她的声音沙哑,起身去倒热水,“医生说你是低血糖加上脱水,昏迷了三天。
”陆远接过水杯,指尖碰到她的手,烫得像火烧。他张了张嘴,想说自己去了古代,
遇见了一个叫虞晴的女子,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话听起来太荒唐了。
宋卿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我给你炖了鸡汤,趁热喝。”她顿了顿,
声音低了下去,“陆远,你不用折腾自己,以后你一个人要注意点,家里多准备点糖。
”陆远想说些什么,看到宋卿忙前忙后,只能继续喝鸡汤。“卿卿,我……”“好了,阿远,
我去叫医生,如果没有什么大碍的话,我们就回家吧。”宋卿怕陆远说出一些什么话,
找个理由就出去了。她和陆远可以说是一起长大,他是什么样的人,自己也是很清楚的。
自己只是因为一句梦话就否定自己与陆远的全部,实在是太幼稚了。想了两三天,
她打算回去和陆远说清楚,就看到陆远因为低血糖休克在家。要是没人发现,
那后果……等他好了,等回家后,再好好说这个事情吧。这样想着,宋卿叫来了医生。
等医生和宋卿赶到病房的时候,病房里空无一人。仿佛没有人住过一样。宋卿走近病床旁,
只有残留的余温提醒她,刚刚的人是真实存在过的。“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