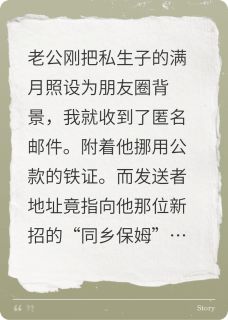
老公刚把私生子的满月照设为朋友圈背景,我就收到了匿名邮件。
附着他挪用公款的铁证。
而发送者地址竟指向他那位新招的“同乡保姆”阿芬。
我以为是小三上位前的清理门户,直到阿芬深夜敲开我的门。
“唐**,你想不想让他进去?”她亮出工牌,是财务审计公司首席调查员。
“三年,足够你把他啃你的骨头,连本带利,一根根,亲手拆出来。”
“你前脚走,后脚他就能把你爹半生的厂子赔掉做赌资!”
我捏着那叠足以送他进监狱的证据,却听见病房里仪器的滴答声。
“姐不图财,”她眼神锐利如刀,“我只要他进去。”
手机突然震动,跳出来老公的消息:“亲爱的,妈说宝宝满月酒定在你爸厂子食堂。”
手机屏幕的光刺得我眼睛生疼。
就在十分钟前,朋友圈刷出我丈夫顾远航的最新动态——一张精心修过的满月照。粉雕玉琢的小婴儿被簇拥在中间,旁边是顾远航深情凝望年轻女人的侧脸,一家三口,画面温馨得扎眼。背景,赫然是我爸一手创立、如今全靠我撑着的那间“鑫源食品”包装车间的食堂大厅。配文:“宝贝满月啦!感谢生命馈赠的礼物,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家”?我盯着那两个字,指甲无意识地掐进掌心,留下几道深红的月牙痕。我和顾远航的家,早在他三年前把那个叫莉莉的女人招进厂里当会计助理时,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我爸去年中风倒下,厂子风雨飘摇,我更没精力去撕他那点破事。只是没想到,他能下作**到这种地步,把野种和他小情儿的满月宴,直接定在老爷子昏迷不醒的厂里!
一股腥甜冲上喉咙口,被我生生咽了回去。
就在这时,电脑屏幕右下角弹出一封新邮件提醒。陌生的发件人,标题只有冰冷的几个字:“顾远航的秘密,唐欣亲启。”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手指有些抖地点击鼠标。
附件下载完毕,点开。清晰的转账记录截图、伪造的采购合同扫描件、甚至还有几段录音文件的文字转译稿……每一笔钱款、每一张票据,都精准地指向鑫源食品的公账,最终流入一个陌生的私人账户。数额触目惊心,累计起来,足够把整个厂子掏空三次还不止!而那个账户的名字……顾远航。
邮件最下方,一行小字标注着技术提取的发件原始地址。那串IP……我盯着它,呼吸都停滞了一瞬。那不是我厂里的内网地址吗?而且,指向的机器编号…是行政部那台老旧的公用打印机?
那个区域,能接触到那台打印机的,除了行政文员,就是…负责打扫那里的清洁工——那个顾远航老家来的、叫阿芬的女人!刚进来不到两个月。
是莉莉!她带着儿子登堂入室还不够?现在是要釜底抽薪,联手那个保姆,把这些年我辛苦填补厂里亏空的证据发给我,逼我自己滚蛋?还是想用这个威胁我,让我在股权**书上签字?
办公室的冷气开得很足,我却觉得一股冰寒从脊椎骨直冲头顶,又被心头的怒火烧灼着。这对狗男女!
凌晨一点,厂区死寂一片,连路灯都昏暗得像是要熄灭。我把自己关在狭小的财务办公室里,桌上铺开那堆打印出来的“证据”,像一个冰冷的漩涡,要把我最后一点力气抽干。我爸半生的心血,我妈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让我守住的承诺……都在一张张虚伪的报表上一点点化为乌有。而吸干这个厂的,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丈夫!
咚、咚咚。
轻轻的叩门声,像深夜坟墓边的啄木鸟,敲得人心头发紧。
“谁?”我厉声问,猛地抬头,心脏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门从外面被推开一条缝,昏黄的廊灯光线下,露出一张熟悉的脸。是阿芬。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头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有眼珠子在阴影里格外亮。
“是我,芬姐。”她声音很平,带着点四川口音,径直走了进来,随手把门在身后轻轻掩上。动作自然得像在自己家。
我全身的肌肉瞬间绷紧,警惕地盯着她,手指下意识地摸向桌下固定着的水杯。“这么晚?有事?”
阿芬没回答,目光精准地落在我摊开在桌面上的那些打印件上,停顿了一秒,然后慢吞吞地从她那个磨得发白的工作服大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是个黑色的硬质卡片,她手指一翻,将那工牌正面朝向我。
借着窗外微弱的光,那工牌上的烫金徽标清晰无比——金鼎国际财务审计与风险调查。下面一行小字:首席独立调查员,林雪芬。
首席…林雪芬?阿芬?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有片刻的空白。金鼎?!那个在业内以铁面著称、号称没有查不出的账、只接受匿名委托、收费高到令人咂舌的事务所?她怎么会是……首席调查员?
“唐**,”她开口了,声音还是那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却完全褪去了平时的木讷和平淡,透着一股金属般的冷冽和锐利,“那些,够不够?”
她往前走了一步,站在我桌对面,那双藏在朴素眼镜片后的眼睛,此刻亮得像淬了寒冰的刀锋,直直地刺向我。
“够他进去待上三年,稳稳当当。”
我下意识地吞咽了一下,喉咙干得发痛。震惊像潮水一样淹没我,原来那个IP…根本不是警告,是她给我的信号?她故意暴露自己?为什么?
“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她微微偏了下头,像是在盘算一件普通不过的商品,“足够你喘口气。把他啃你的骨头,连本带利,一根,一根,亲手拆出来。”
每个字都像冰珠子砸在鼓面上。她怎么知道顾远航这些年是怎么榨取厂里、榨取我家的?连我咬牙替他遮掩、拿娘家钱填窟窿的事,她都清楚?
“他现在就在医院守着他那个宝贝儿子。你觉得,你前脚要是……出了什么事,或者干脆撒手,”她的眼神瞟向我放在桌上的手机,“他后脚会怎么做?”
我猛地看向手机,屏幕是黑的。但下午他发来的那条信息,像梦魇一样浮现:“亲爱的,妈说宝宝满月酒就定在你爸厂子食堂了,喜庆热闹!”
用我爸昏迷不醒的地方,给他和别的女人的儿子办满月宴!
“他会立刻把厂子最后那点底子,”林雪芬的声音冷得像西伯利亚的风,“押上赌桌!或者直接打包贱卖!反正,姓唐的招牌倒了,他才好改姓顾!”
一股巨大的恶心和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是的,他能!为了赌,他连我爸的救命药钱都敢挪!他甚至可能盼着我死!我手撑着桌面才没让自己软下去,手背因为用力而青筋毕露,指甲划拉在木头上,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
她到底想干什么?帮我?代价是什么?
就在这窒息般的沉默里,搁在桌面上的手机突然亮了,无声地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的名字,像毒蛇一样——顾远航。
林雪芬瞥了一眼那跳动的名字,嘴角勾起一丝极淡、极冷的弧度,仿佛早就料到。她没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我,那双眼睛深不见底,又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笃定。
空气凝固了。手机执拗地震着,震得我手腕发麻。我盯着屏幕上“顾远航”三个字,胃里翻江倒海。
“姐不图财,”林雪芬的声音再次响起,平静得吓人,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我只要他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