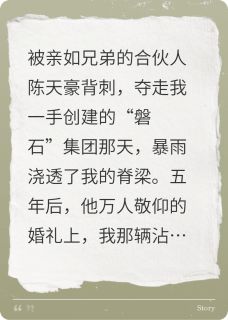
被亲如兄弟的合伙人陈天豪背刺,夺走我一手创建的“磐石”集团那天,
暴雨浇透了我的脊梁。五年后,他万人敬仰的婚礼上,我那辆沾满灰尘的越野撞碎了香槟塔。
“林肆哥?”他强作镇定,嗓音却在发抖,“外面传你破产了...”我点燃一支烟,
烟雾缭绕中凝视他身后巨大的上市倒计时牌。“破产?”我吐出一个烟圈。
“老子是回来抄底的,从你的尸骨上!”闪光灯骤然聚焦,他精心设计的名利盛宴,
成了我的修罗场。他身后的金融巨鳄们面色剧变,
因为他们认出了我身侧的老者——那个曾撼动半壁江山的资本界幽灵,金九龄。
【第一章】暴雨归墟窗玻璃上爬满了水痕,被外面暴烈的霓虹切割成无数蠕动的伤口。
引擎粗暴的嘶吼穿透厚重的隔音玻璃,压过了雨点砸在车顶的鼓噪。我盯着前方,
金色拱门像张愚蠢的大嘴,吞进去衣着光鲜的男女,“百年好合”四个字镶在拱顶,
比霓虹灯更刺眼。雨水顺着扭曲变形的前引擎盖往下淌,汇入柏油路乌黑的河流。
油门还焊死在脚底,这辆灰扑扑的硬派越野,像头刚在泥潭里打过滚又饥肠辘辘的巨兽。砰!
车身猛地一震。不是撞击声,是轮子碾断了什么东西,塑料碎裂的脆响夹在引擎声里,
微不足道。是拱门基座的装饰条?还是地上铺的红绸缎?管它呢。
车子撞开最后半扇斜歪的红木栅栏,像头蛮牛,一头扎进了宴会场地正中央!
世界陡然安静了一刹。轮胎摩擦过光滑湿透的大理石地面,发出濒死般的尖啸,
精准无比地停在了那座香槟塔前面。水晶杯堆成的金字塔像是被施了定身咒,
折射着穹顶璀璨的吊灯光芒,梦幻得不真实。然后,“哗啦——!
”整个金字塔彻底崩溃、解体。晶莹的水晶碎块如同冰雹般飞溅,
昂贵的金色酒液混合着砸碎的冰屑,像泼脏水一样轰然倾泻,浇了前方几个倒霉蛋满头满身。
女人的尖叫穿透了停滞的空气,尖锐地刮擦着耳膜。“草!眼瞎啊!”“谁他妈的车!
”混乱像是引线瞬间被点燃。几个穿着黑西装、安保模样的壮汉提着甩棍扑了上来,
脸上横肉跳动,眼神凶狠得像要吃人。车门从里面被猛地推开。
脚踩在湿漉漉、溅满香槟的大理石上,发出清晰粘滞的声响。一个冲在最前面的光头安保,
甩棍带着风朝我肩膀抽过来。我没退,左手闪电般探出,准确地钳住了他握棍的手腕,
右手成掌,看也没看,快而狠地切在他小臂神经丛的位置。力道不算大,但角度刁钻。“呃!
”一声憋闷的痛哼。甩棍脱手,当啷掉地。他整条手臂瞬间麻痹,人踉跄着歪向一边。
第二个紧随其后,拳头捣向我面门。侧身,左臂屈肘向外一格,卸开拳锋的同时,
借着对方的冲劲旋身,右腿膝弯精准顶在他扑过来的胸腹隔膜处。动作简洁得近乎残忍,
带着荒野打磨出的冷硬质感。第二个闷哼着软倒在地。第三个脚步顿了一下,眼神里有犹豫。
场子里的空气凝固了,只剩下急促呼吸和被压抑的咒骂。
那些衣着光鲜的宾客像是被按了暂停键,
脸上凝固着惊恐、茫然、好奇……还有被搅局的愤怒。“林肆哥?
”一个声音穿透了这片凝固的喧哗,带着难以置信的震惊。
陈天豪从人群深处分开一条道挤过来。那身量体裁衣的顶级杰尼亚西装,
在他紧绷的身体上勒出了僵硬的褶皱。那张总是挂着或精明或儒雅笑容的脸,此刻血色褪尽,
只剩下纸一样的白,嘴唇却泛着不正常的青紫。他的视线死死钉在我身上,
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地翻搅、碎裂。他强撑着往前又挪了半步,
眼角的肌肉在不受控制地细微抽动。“外面…外面都传,你不是…不是早就破产了吗?
”喉咙滚动着,声音像砂纸打磨铁锈,“在东南亚那边…彻底输光了?”呵。
我从洗得发旧的冲锋衣内袋里掏出一包“中华”,抖出一根,叼在嘴里。
塑料打火机在雨声和死寂中被擦亮。跳跃的橙红色火苗舔舐过烟丝,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猛吸一口,辛辣滚烫的烟雾灌入肺腑,再被狠狠逼出来。白色的烟圈悠悠荡荡往上飘,
扭曲着散开,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的目光穿透眼前缭绕的烟雾,
越过陈天豪那张强装镇定的脸,落在他身后。大厅尽头,
整个墙面被一块巨大的LED屏幕占据。屏幕上,
子倒计时正在冰冷地跳动着:【磐石集团·上市倒计时:06:15:48】红得滴血。
红得像当年那个暴雨夜,他从我手里骗走核心算法时,电脑屏幕上刺眼的错误警告。
红得像他用卑鄙手段将我扫地出门时,嘴角那抹得意又残忍的冷笑。破产?东南亚?
我夹烟的右手抬起来,食指随意地掸了掸烟灰。烟灰飘飘洒洒,
落在他一尘不染的纯黑手工皮鞋尖上。“破…产?”我看着他,一字一顿,
声音低沉得近乎耳语,像生锈的刀刃刮过骨头,压着那沸腾了五年、烧穿五脏六腑的岩浆,
“耗子,老子是回来抄底的。”指尖几乎要点到他鼻子上,
我的目光钉死在他身后那刺眼的倒计时上,每一个字都淬着冰渣:“从你的——尸骨上!
”几乎在我最后一个字音落地的瞬间,现场那些原本对准了奢华婚礼场景的专业长焦镜头,
像是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齐刷刷地、毫不犹豫地调转方向。
冰冷的快门声如同爆豆般噼啪炸响!成片刺目的白光毫不留情地泼洒在我身上,
勾勒出洗得发白的冲锋衣边缘磨损的毛边,照亮了我脸上经年不散的阴霾,
也将陈天豪骤然扭曲的惨白面庞和他身后巨幕上那滴血的倒计时——一同淹没了进去!
精心编织的名利盛宴、处心积虑的辉煌典礼…这耗费了无数心血的修罗场,
灯光、镜头、窃窃私语、惊疑的目光,此刻全都成了烙在他陈天豪身上的刑具!
他精心涂抹的光鲜外壳,被我迎头撞得稀巴烂,暴露出底下腐烂的本相!“谁放你进来的?
谁?!保安!保安死哪里去了!”陈天豪彻底撕掉了最后的伪装,脖颈上青筋暴起,
嘶吼得破了音。他猛地扭头,
眼睛血红地瞪向角落一个穿着深灰条纹西装、神情阴鸷的胖子——他的安保主管。
胖子主管如梦初醒,脸上的肥肉剧烈抖动,对着领口通讯器狂吼:“动起来!
把这疯子给我拖出去!叫外面的进来!快!”他声音又尖又急,
显然也是被这突发的变故吓掉了魂。更多更壮的黑衣安保像闻到味的鬣狗,
从角落、从门口、从各个通道口扑了过来。人潮的阴影瞬间将我围拢,
空气被挤压得粘稠沉重。几道魁梧的黑影带着恶风扑到跟前,
粗壮的手臂带着锁喉的意图抓向我的咽喉。就在这时,
一直处于风暴中心、安静停在我身旁的越野车,副驾驶的车窗无声地滑下了十公分左右。
一只枯瘦、遍布老人斑的手稳稳地从那道缝隙里伸了出来。没有动作,没有声音。
那只手的手腕上,一块斑驳的、连表针都不再走动的卡西欧电子表异常扎眼。
一个扑得最猛的安保,位置刚好对着那只手的方向。他脸上的狰狞杀气瞬间僵住,
脚步硬生生一顿,像是突然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法,
连带着他后面两个同伴也下意识地刹住了冲锋的势头。就在这微妙的、近乎冻结的空隙里,
一个低沉沙哑、却蕴含着某种奇特穿透力的嗓音,不高不响,却仿佛盖过了全场的喧哗骚动,
清晰地从副驾驶座传来:“阿豪?”就两个字。陈天豪如同被高压电猛地贯过全身,
所有的嘶吼叫嚣戛然而止。他那双充血的、狂怒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那只枯槁的手,
目光仿佛黏在了那块破旧的电子表上。五秒钟,仅仅五秒,
他那张猪肝色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尽最后一丝血色,由猪肝变成了死人一样的灰败,
唇边甚至控制不住地开始细微痉挛。他身后那庞大的观礼嘉宾阵容中,
一个戴金丝眼镜、气质精干威严的中年男人倒吸一口冷气,眼镜都滑到了鼻尖也忘了扶,
失声低呼:“金…金九龄?!”他旁边一位保养得宜、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老太太,
手里摇晃着的香槟杯猛地一晃,酒液泼溅在价值不菲的礼服上,她却毫无察觉,
脸上是一种混杂着极度震惊和一丝畏惧的表情,死死盯着那只手。
更远处几位西服革履、气度不凡的成功人士,脸色也纷纷变得极其难看,
互相交换着只有他们自己才懂的眼神。那个安保主管脸上的表情更是跟见了鬼一样,
肥肉堆叠的胖脸瞬间一片惨绿,嘴唇哆嗦着,喉结上下滚动,想喊什么,
却一个音节都发不出,只能对着扑上来的保安疯狂地摆手,示意他们停下!
暴起的安保们不明所以,但在主管那惊恐到近乎扭曲的阻拦手势下,动作硬生生僵在原地,
惊疑不定地看着陈天豪以及那群骤然失态的显贵们。凝固的不仅仅是安保。
那些刚刚还对着我疯狂按快门、试图捕捉爆炸性新闻的记者们,
手中的相机也仿佛在这一刻集体失灵。快门声稀疏、犹豫下来。
一部分目光死死锁定了那只枯槁的手和腕上的破表,
似乎在极力确认;另一部分则惊疑不定地在陈天豪和他那群贵宾们青红交错的脸上扫来扫去,
嗅到了远超眼前冲突的、足以掀翻整个沪上滩的秘密风暴正在暗流涌动!
整个婚礼现场的气氛,从暴力冲突的临界点,
陡然坠入了一种更深沉、更令人窒息的诡异死寂之中!这死寂如冰层,
表面之下是汹涌的暗流和即将冲破冰面的未知巨兽!
【第二章】金爷与牌桌那只枯槁的手收了回去,车窗缓慢升起,
隔绝了那张只在传说里存在的模糊面庞。车里再无动静。但仅仅是一只手,一个称谓,
就已经在陈天豪和他那帮贵宾们心中引爆了一颗无形的炸弹。空气黏稠得像凝固的沥青。
“金…金老…您…您怎么会……”陈天豪的声音彻底变了调,抖得不成样子,像是喉管漏风,
先前那副掌控一切、张牙舞爪的派头碎了一地,只剩下**裸的惊恐和难以置信。
他艰难地挪动脚步,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讨好笑容,试图凑近车窗解释。我猛地踏前一步,
堵在他和车门之间,动作快得像一道影子,肩膀重重撞开他的胳膊。“咚!”这一撞没收力,
沉闷的响声在安静的大厅里格外刺耳。陈天豪猝不及防,“蹭蹭蹭”狼狈倒退好几步,
踉跄着差点撞到后面的巨幕倒计时牌。精心梳理的头发乱了,西装皱巴巴贴在身上,
刚才还像个发怒公鸡,现在活脱脱一只落水野狗。他身后那群衣冠楚楚的贵宾们,
包括刚才认出手表的金丝眼镜和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脸色更难看了。有人眉头紧锁,
有人眼神闪烁,交换着更加复杂的目光。显然,金九龄的身份被那破旧电子表坐实了。
这个本该只存在于陈天豪“辉煌履历”传说背景里的、如传说般销声匿迹的老人,
居然坐在那辆撞翻他婚礼的破车上!而且还和我一起出现!
这信息量足够炸翻整个沪上的牌局!“耗子,”我的声音不高,
压过了他粗重的喘息和外围那些压抑不住的议论,像钝刀子在磨石上刮,
“记不记得当年在这‘凯撒宫’,你从我这赢走的是什么?
”陈天豪扶住旁边一把椅子的靠背才稳住身形,他喘着粗气,脸上青白交加,
眼神惊疑不定地在我和那紧闭的车门之间来回扫视。他不明白我提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场牌局,他出千赢走的,是磐石集团核心的基石和未来——那份价值连城的核心算法合约。
我没有看他精彩纷呈的脸色。目光投向那群贵宾席最前端、最显眼的位置——周世元,
沪上创投圈的隐形教父,陈天豪背后最大的金主。这位周先生端坐不动,
手上把玩着一枚温润的玉扳指,脸上看不出喜怒,
但那双精光内敛的眼睛正沉静地穿过混乱的人群,准确地落在我身上。他旁边,
就是那个金丝眼镜和头发一丝不苟的老太太,两人的表情在周世元的平静下,
显得更加紧绷惊疑。好戏才开场。
我径直走向宴会厅中央那个为了仪式暂停、但赌台设备还依旧闪耀的小型精品拍卖台。
随手拖过一把高脚椅,椅子腿在光洁地板上划出刺耳的摩擦声。拉开椅子,大马金刀地坐下。
腰后硬邦邦的枪柄抵着脊柱的冰冷触感时刻提醒着我,这场赌局从一开始,就没有退路可言。
但此刻不是动火器的时候,牌桌上的战斗,
有牌桌上的规矩——尤其是当着周世元这种精明的老狐狸的面。拍卖师是个瘦高的中年人,
脸上标准的职业微笑早就撑不住了,惊恐地看着我。
我从冲锋衣的内袋里摸出一个不起眼的深棕色小牛皮钱夹,看起来也有些年头了,
边缘磨得发亮。抽出一张同样磨出毛边、却印着独特金色蜂鸟纹样的纯黑卡片,
随手拍在光滑的赌桌上。黑卡落在桌面,发出一声沉闷的轻响。整个大厅死寂了一瞬。
那几个离得近的贵宾,尤其是那个金丝眼镜和头发一丝不苟的老太太,再次倒抽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