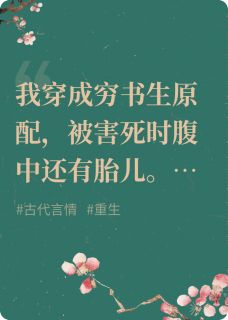
浣衣房的日子,是泡在冰冷的脏水和无休止的搓揉捶打中度过的。
粗粝的皂角磨得挽月(沈青黛)原本就带薄茧的手指红肿破皮,寒风一吹,裂开细小的血口,钻心的疼。沉重的木桶,冰冷的石板,永远洗不完的绫罗绸缎……这具年轻却同样疲惫的身体,每日都在极限的边缘挣扎。
然而,肉体的苦楚丝毫无法麻木她灵魂深处的恨火。每一件送来的华服,都可能是柳含烟那个**穿过的;每一桶倒掉的脏水,都冲刷不掉她记忆中那片刺目的猩红。她像一块沉默的石头,埋首在堆积如山的衣物里,耳朵却竖得比最警觉的兔子还高,捕捉着每一个飘过浣衣房墙角的、关于这座丞相府主人们的只言片语。
“听说了吗?昨儿柳夫人又得了宫里赏的新样宫花,啧啧,那叫一个金贵……”
“老爷越发倚重大公子了,前朝好些事都交给他办呢……”
“大公子?唉,可惜了……柳夫人那性子,亲生的又如何?还不是……”
大公子?梁煜?
挽月搓洗衣物的手猛地一顿。冰冷的水浸着裂口,刺得她一个激灵。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暖阁门帘掀开时,那个冲进来的、肩头落雪的少年身影,和他那双死死盯着血泊、黑沉绝望的眼睛。
十年了,柳含烟的儿子……如今是什么模样?成了他父亲梁文柏最得力的臂膀?还是……也成了那对豺狼虎豹的帮凶?
一丝冰冷的、带着试探意味的算计,悄然爬上她的心头。复仇的路径千头万绪,如同浓雾中的迷宫。梁文柏位高权重,柳含烟背靠大树,她一个孤魂野鬼附身的小小婢女,想撼动这座巍峨的相府,无异于蚍蜉撼树。或许……这个梁煜,会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缺口?是柳含烟唯一的儿子,也是她沈青黛名义上唯一的“庶子”。
机会,在三个月后一个突如其来的混乱清晨降临。
相府二管家周嬷嬷,一个在仆役间颇有几分体面的管事娘子,因着昨夜贪杯多喝了几盅,早起时一脚踏空,竟从后院的石阶上滚了下去,摔断了腿骨,需得静养数月。她原本负责内院一部分针线女红和器皿清点的差事,顿时空悬出来。
一时间,各房的管事娘子心思都活络起来,削尖了脑袋想把自己的人塞进去。挽月混在浣衣房看热闹的人群里,听着那些压低的议论,心念电转。这是个机会,一个能稍微靠近内院核心的机会!但以她一个浣衣粗使丫头的身份,连递句话的资格都没有。
她需要一个跳板,一个能在管事娘子面前说得上话的人。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目光最终落在一个姓孙的管事娘子身上。此人贪财,且与周嬷嬷有些龃龉。挽月用这几个月省下的、少得可怜的月钱,加上一点从库房废料里偷偷捡拾、自己费心打磨的劣质玉料,做成了一对还算精巧的耳坠子,趁人不备,塞给了孙嬷嬷身边一个贪嘴的小丫头。
几日后,当孙嬷嬷在众多“孝敬”中看到这对耳坠子,又听小丫头“无意”说起挽月手巧,曾在老家学过些针线,心思便动了动。横竖是个不起眼的位置,安插个识趣又便宜的人,总好过让对头的人占了去。
于是,在一个飘着细雪的午后,挽月被调离了臭气熏天的浣衣房,成了内院针线房一个负责清点、跑腿的三等小丫头。虽然依旧低微,但至少,她能踏进那曾经属于她的、如今被柳含烟占据的内院了。
第一次踏入内院回廊,看着那些依稀熟悉却又透着物是人非的景致,挽月只觉得一股腥甜之气直冲喉头。她死死咬着牙关,指甲再次掐进掌心,用疼痛提醒自己隐忍。
她开始更加谨慎地编织她的网。凭借前世当家主母的眼光和手腕,她将针线房的琐事打理得井井有条,甚至能不动声色地替管事嬷嬷补上一些账目上的小纰漏。她说话轻声细语,做事勤快妥帖,从不逾矩,很快便得了管事嬷嬷几分青眼,一些稍微体面点的跑腿差事,比如给各房主子送些新制的衣物、绣品,也开始落到她头上。
她第一次见到柳含烟,是在一个暖阳和煦的午后,去送新做的春衫。
柳含烟斜倚在铺着厚厚锦垫的贵妃榻上,几个丫头围着她捶腿捏肩。十年光阴,并未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反而因着养尊处优,更添了几分成**人的慵懒风韵。她穿着最时兴的云锦,发髻上簪着赤金点翠的步摇,指尖染着鲜红的蔻丹,正懒洋洋地捻着一颗蜜饯。
挽月低着头,捧着托盘,恭恭敬敬地跪下行礼:“奴婢针线房挽月,给夫人送新制的春衫。”
柳含烟眼皮都没抬一下,只从鼻子里轻轻“嗯”了一声,示意旁边的丫头接过去。挽月垂下的眼睫剧烈地颤抖着,几乎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抑制住扑上去撕碎那张脸的冲动。就是这张脸,带着温婉的笑意,将那碗毒药递到了她的唇边!
“夫人,您瞧这料子,多衬您的气色。”一个伶俐的大丫头抖开衣衫奉承着。
柳含烟这才随意地瞥了一眼,嘴角勾起一丝满意的弧度。那笑容,与十年前暖阁里递药时的笑容,诡异地重合在一起。
挽月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直窜上头顶,血液都几乎凝固。
“抬起头来。”柳含烟的声音带着一丝漫不经心的慵懒,目光终于落在了跪在地上的小丫头身上。
挽月依言缓缓抬头,眼神依旧低垂着,不敢直视,只露出半张粗糙暗黄的脸。
柳含烟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片刻,像是在看一件微不足道的器物,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对年轻女子的本能挑剔。随即,那点兴趣便消失了,她挥了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行了,下去吧。”
“是,夫人。”挽月的声音平静无波,再次深深叩首,才起身,垂着眼,倒退着出了暖阁。
直到走出那扇隔绝了暖香和冰冷现实的门,走到无人回廊的转角,挽月才猛地靠在冰冷的廊柱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后背的冷汗早已浸透了薄薄的夹袄。指甲深深陷入廊柱粗糙的木头纹理里,留下几道血痕。
恨意如同毒藤,缠绕着她的心脏,越收越紧。快了……柳含烟,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机会,在又一次送东西时悄然出现。这次是去书房外院,给梁文柏送一件紧急缝补好的朝服。
刚走到书房外的月亮门附近,便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着怒火的呵斥声,间或夹杂着瓷器碎裂的脆响。
“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我养你们何用!”是梁文柏的声音,十年宦海,那声音里的威严和戾气更重了。
紧接着,一个穿着靛蓝色锦袍、身形颀长的年轻男子,脸色阴沉地快步从书房里退了出来,险些撞到端着托盘的挽月。他身后跟着两个噤若寒蝉的幕僚。
挽月慌忙退后一步,低下头,心跳却骤然加速。是他!梁煜!
十年光阴,早已褪尽了少年的单薄青涩。眼前的男子身量极高,肩背宽阔,裹在精致的锦袍里,透着一股迫人的英挺之气。他的面容继承了梁文柏的轮廓,却更加深刻冷峻,剑眉斜飞入鬓,鼻梁高挺,薄唇紧抿成一条冷硬的直线。那双眼睛……挽月飞快地抬眼一瞥,心头猛地一凛。那双眼睛,比记忆中更加幽深,如同不见底的寒潭,里面翻滚着她看不懂的沉郁和……某种近乎暴戾的阴鸷。此刻,那阴鸷正毫不掩饰地翻涌着,显然是在里面受了极大的斥责。
他看也没看旁边低眉顺眼的小丫头,径直大步流星地离去,带起一阵冷风。他身后的一个幕僚经过时,低声咒骂了一句:“……都是那姓李的御史多事!捅到御前,害公子……”
御史?御前?挽月的心猛地一跳。她垂着头,端着托盘的手稳如磐石,耳朵却捕捉着每一个字。
书房里的怒骂还在继续。她定了定神,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对着守在外面的小厮通报:“针线房挽月,奉管事嬷嬷命,送补好的朝服来。”
小厮进去通传,片刻后出来,脸色也不好看:“进去吧,仔细点,相爷正恼着呢。”
挽月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走进书房。浓郁的书墨香气混合着一种沉檀的冷香,扑面而来。地上果然有碎裂的瓷片,茶水洇湿了昂贵的地毯。梁文柏背对着门口,负手站在巨大的紫檀木书案后,看着墙上挂着的《万里江山图》,背影紧绷,透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
十年了。这个曾在她面前许下山盟海誓,又亲手将她推入地狱的男人。挽月的指尖在托盘下微微颤抖,几乎要控制不住将托盘砸向他后脑的冲动。她死死咬着下唇内侧,直到尝到一丝血腥味,才勉强压下那股翻腾的杀意。
“相爷,”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卑微,“您的朝服补好了。”
梁文柏没有回头,只冷冷地“嗯”了一声,带着浓浓的不耐烦。
挽月将托盘轻轻放在一旁的矮几上,动作轻巧无声。目光飞快地扫过书案。案头堆着几份摊开的奏章,其中一份的墨迹似乎格外新,一行字跳入她的眼帘:“……私吞河道银两……证据确凿……”旁边朱笔批着刺眼的“彻查”二字。
她心头剧震!河道银两?这可是泼天的大罪!难道刚才梁文柏斥责梁煜,幕僚提到御史和御前,就是因为此事?梁煜……似乎卷进去了?而且看情形,对他极为不利!
一个大胆得近乎疯狂的念头,如同毒蛇吐信,骤然在她脑海中清晰起来。接近梁煜!利用他!利用这场危机!
她不动声色地退出了书房,如同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回到针线房僻静的后院,她独自坐在冰冷的石阶上,望着阴沉沉的天空,手指无意识地在地上划拉着。
如何接近?如何让他注意到自己这样一个低微的婢女?她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他记住,甚至产生兴趣的契机。不能是刻意的勾引,那太低劣,也太危险。
几天后,机会竟自己送上门来。
柳含烟不知从哪里得了一盆极为名贵的“十八学士”山茶,稀罕得不行,特意叫针线房手艺最好的绣娘去描样子,说要绣在屏风上。偏巧那绣娘染了风寒,病倒了。管事嬷嬷急得团团转,生怕误了柳夫人的事吃挂落。
挽月站了出来,声音不大,却清晰:“嬷嬷,奴婢……奴婢在家时,曾跟过画师学过几天描红,或许……可以试试?”
管事嬷嬷将信将疑地看着她。挽月也不多话,当即寻了纸笔,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朵山茶花的轮廓,虽显稚嫩,但形态气韵竟抓得颇有几分神似。
“哎哟!你这丫头!”管事嬷嬷又惊又喜,“还有这本事!快!快去夫人院里!”
挽月再次踏入了柳含烟的暖阁。这一次,她的心境冰冷如铁。她专注地对着那盆开得正盛的山茶,一笔一划地描摹着。姿态卑微,神情专注,仿佛眼中只有这花,再无其他。
她描得极慢,极细致。直到天色渐晚,华灯初上,暖阁里点起了明亮的烛火。终于,一阵沉稳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停在了暖阁门口。
“母亲。”是梁煜的声音,比上次在书房外听到时,似乎更沉冷了几分,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柳含烟正由丫头伺候着用晚膳,闻言也只是淡淡应了一声:“回来了?可用过饭了?”
“用过了。”梁煜走了进来,目光随意扫过室内,掠过那盆名贵的山茶,最后落在了暖阁角落里,那个伏在案几上、对着花枝专注描摹的瘦小身影上。
挽月仿佛被惊动,手微微一抖,一滴墨汁落在了刚描好的花瓣上,瞬间晕染开一小片污迹。她像是吓坏了,慌忙抬头,正对上梁煜投来的、带着审视意味的冰冷目光。
那是一双极其锐利的眼睛,像淬了寒冰的鹰隼。挽月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脸上恰到好处地浮现出惊惶和无措,手指紧紧捏着笔杆,指节泛白,身体微微颤抖着,如同受惊的小鹿。她迅速低下头,声音细若蚊呐,带着哭腔:“奴婢……奴婢该死……弄污了画……”
柳含烟这才注意到这边,皱了皱眉,有些不悦。
梁煜的目光在那张因惊惶而显得格外苍白的小脸上停留了一瞬。少女的轮廓在昏黄烛光下显得有些模糊,但那双骤然抬起的眼睛里,除了惊惧,似乎还有一丝极力压抑的、更深的东西……像是一闪而过的倔强?抑或是别的什么?快得让他抓不住。
他移开目光,语气淡漠地对柳含烟道:“不过一张画稿,污了再描便是。何必动气。”说罢,不再看角落,径直走到一旁坐下,端起丫鬟奉上的热茶。
柳含烟见他开口,便也懒得再计较,挥挥手:“罢了罢了,明日再描吧,仔细点!下去!”
“谢夫人!谢大公子!”挽月如蒙大赦,慌乱地收拾好画具,几乎是踉跄着退了出去。
走出暖阁,夜风一吹,她才发觉自己后背的衣衫已经被冷汗完全浸透。刚才那一瞬间的对视,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带来的压迫感,几乎让她窒息。
他看到了吗?看到自己眼中那一闪而逝、几乎无法控制的恨意了吗?
她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第一步,她迈出去了。她在他眼中,不再是一个完全模糊的背景。她的名字——挽月,或许,已经被他记下了。
一张无形而危险的网,正随着她小心翼翼的步履,向着那个名为梁煜的男人,悄然张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