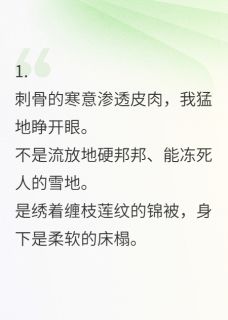
1.刺骨的寒意渗透皮肉,我猛地睁开眼。不是流放地硬邦邦、能冻死人的雪地。
是绣着缠枝莲纹的锦被,身下是柔软的床榻。鼻尖萦绕着熟悉的、闺房里冷梅香气。
我僵硬地转动脖颈,环视四周。这里是丞相府,我的闺房。墙角的铜漏正滴着水,
寂静得可怕。我回来了。回到了丞相府被满门抄斩的前一夜。前世,这个时候的我,
还在灯下羞涩地抚摸着即将出嫁的嫁衣,憧憬着与世子表哥的美好未来。何其可笑。
那个温柔多情的世子表哥,转头就递上了构陷我苏氏满门谋反的奏章。而我,苏晚卿,
堂堂丞相嫡女,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在流放路上受尽欺凌,病死雪地。
彻骨的恨意涌上心头,几乎要将我撕裂。不,不能恨。现在最重要的是,活下去。“**!
**您醒了?”贴身侍女画屏端着水盆进来,见我坐起,又惊又喜。“您都睡了一天了,
晚膳也没用,可吓死奴婢了。”她放下水盆,担忧地探向我的额头:“可还难受?
”我避开她的手,声音沙哑:“画屏,现在什么时辰了?”“戌时刚过。”画屏答道,
又忍不住絮叨,“老爷和少爷也不知怎么了,昨日被宫里的人请去,至今未归,
夫人急得在佛堂跪了一天……府里人心惶惶的,
奴婢瞧见好些个下人都在偷偷收拾东西……”我打断她:“父亲和兄长,回不来了。
”画屏脸色煞白:“**,您、您说什么胡话!”我没有解释。再过两个时辰,子时一到,
禁军便会踏破丞相府的大门。男丁处斩,家产充公,女眷……要么贬为官妓,
要么流放三千里。前世的我,选择了后者,那是一条比死更难熬的路。这一次,
我绝不会重蹈覆辙。“**,咱们快想想办法啊!要不,奴婢去求求夫人,
看能不能从后门偷偷送您出去?”画屏急得快哭了。送我出去?天真。满城风雨欲来,
此刻京城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何况,就算逃出京城,又能去哪里?
天下之大,莫非王土。没有身份、没有倚仗的逃犯,只有死路一条。“画屏,
”我掀开被子下床,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你去取我箱笼里那件月白色的素面长裙来,
再帮我梳个最简单的发髻。”画屏愣住:“**,这个时候……”“快去!
”我的语气带着不容置喙的冷意。她不敢再问,连忙去了。我走到梳妆台前,
看着铜镜里那张尚显稚嫩,却因死过一次而褪去所有天真的脸。金银细软、传家宝物,
这些都带不走,也没用了。我唯一能抓住的生机,只有一个人。那个权倾朝野,
冷酷嗜杀的摄政王,萧玦。今夜,他会亲自带队查抄苏府。
2.画屏手脚麻利地为我换上素裙,梳好发髻。我挥退她:“你留在房里,
无论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来。”她还想说什么,被我一个眼神制止,只能含泪点头。
我走到内室暗格,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小的、用油布包好的东西。这是父亲的书房密信,
记录着他与兵部尚书私下往来的账目,涉及军饷亏空。前世,父亲因此被构陷,
但这东西却阴差阳错落入我手。我本想以此为父亲翻案,却最终无力回天,只得带着它惨死。
这一世,它将是我的敲门砖,我的“投名状”。我知道萧玦一直想扳倒兵部尚书,这东西,
他一定会感兴趣。我将油布包紧紧揣入怀中,深吸一口气,推开房门。夜色浓重,
府中只有零星几盏灯火,更显寂寥。我凭着记忆,
小心翼翼地避开巡夜的家丁和那些慌不择路、试图卷款私逃的下人,
一路潜行到相府西北角最偏僻的一个侧门。我知道,萧玦的车驾会从门外那条暗巷经过。
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冰冷的夜风吹透单薄的衣衫,我却感觉不到冷。心脏在胸腔里狂跳,
几乎要蹦出来。**着冰冷的墙壁,努力平复呼吸。赌上性命的一步,一旦踏错,
便是万劫不复。远处传来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的辘辘声,由远及近。来了!
我攥紧了藏在袖中的油布包,指甲几乎掐进肉里。一列玄色车驾在夜色中缓缓驶来,
前后簇拥着十数名佩刀侍卫,沉默肃杀。正中的那辆马车,通体乌木,没有任何标识,
却透着令人窒息的威压。那就是萧玦的座驾。在车驾距离巷口还有十余步时,
我猛地冲了出去,毫不犹豫地跪倒在暗巷中央!“吁!”马车骤然停下。“什么人?大胆!
”前方的侍卫厉声呵斥,腰间的佩刀瞬间出鞘,寒光凛冽。我伏低身子,
额头抵着冰凉的地面,用尽全身力气高声道:“罪臣之女苏晚卿,有惊天密报,
欲献于摄政王殿下!”3.刀锋的寒意几乎贴上我的脖颈。我没有抬头,
额头紧贴着冰冷的石板,声音却清晰地穿透夜色:“罪臣苏宏安之女苏晚卿,有惊天密报,
愿献于摄政王殿下,以求苟活!”四周死寂。只有风声,还有马匹不安的响鼻声。
侍卫的刀没有收回,反而逼近了几分。我能感觉到那股杀气,冰冷,毫不犹豫。
只要马车里的人稍有不耐,我的头颅就会立刻滚落在地。怀里的油布包硌得我生疼,
那是父亲的罪证,也是我唯一的生机。我赌萧玦需要这个。赌他对扳倒兵部尚书的兴趣,
大于碾死一只蝼蚁的随意。时间一点一滴流逝,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熬。
恐惧攥紧了我的心脏,但我不能退缩,更不能发抖。我必须表现出足够的价值,
而非一个摇尾乞怜的可怜虫。“哦?”一个低沉、毫无温度的声音从车帘后传来,
像是寒冰碎裂。仅仅一个字,却带着令人窒息的威压。是他,萧玦。我攥紧了手心,
强迫自己冷静:“晚卿手中之物,关乎兵部尚书项上人头,更牵涉军饷大案。王爷过目便知。
”我没有直接说出内容,点到即止。既要勾起他的兴趣,又不能显得急不可耐。
车帘后的气息依旧冰冷,似乎在审视,在掂量。我能想象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
此刻正透过薄薄的帘子,将我从头到脚剖析得一清二楚。他会停下,
一定是因为“兵部尚书”这四个字。朝中皆知,兵部尚书是他的死对头。“抬起头来。
”他命令道。我缓缓抬起头,迎上那片幽深的黑暗。虽然看不清他的脸,
但我能感觉到那道视线,锐利如刀。我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带着几分豁出去的狡黠:“王爷,
民女别无所求,只求活着。”车厢内又是一阵沉默。我维持着抬头仰视的姿势,脖颈酸痛,
心跳如擂鼓。他在犹豫什么?是怀疑我的动机,还是觉得这交易不够分量?或者,
他根本不在乎兵部尚书的死活?不,不可能。前世,他为了扳倒此人,布了多少年的局。
我手中的东西,绝对是他需要的。“理由?”萧玦的声音再次响起,依旧听不出情绪。
不是问我献宝的理由,而是问我求活的理由。他想知道,我凭什么认为自己值得他出手。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咙的干涩:“王爷身边,从不缺杀人的刀。但晚卿这把刀,
淬过苏家的血,饮过切肤的恨,用起来,或许比寻常的刀更顺手,也更隐蔽。
”“晚卿愿做王爷手中最锋利、最不引人注意的那把刀,为王爷披荆斩棘。只求王爷,
给我一个苟活的机会。”我将姿态放得很低,却又暗示了自己的价值和狠厉。
我赌他需要一把来自地狱的刀,去对付那些朝堂上的魑魅魍魉。4.车帘微动,
似乎有人在里面低语了几句。片刻后,萧玦的声音再次传来,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玩味:“有点意思。”“带上她。”不是带回王府,也不是收入府中。
而是……侍卫收刀入鞘,粗鲁地将我从地上拽起,推搡着我走向马车。我踉跄了一下,
站稳脚跟,没有反抗。车门打开,一股冷冽的龙涎香气扑面而来。里面光线昏暗,
只能隐约看到一个身着玄色锦袍的男人端坐其中,身形挺拔,气势迫人。我不敢细看,
垂下眼睑,被侍卫塞进了车厢角落。马车重新启动,辘辘前行。方向……不对。
这不是去摄政王府的路。我的心猛地一沉。这是回……丞相府的路!他要带我回去?
回去看苏家被抄家?我猛地抬头,看向那个模糊的身影,他似乎并未看我,
只是靠在软垫上闭目养神。他是要试探我?还是单纯的恶趣味?让我亲眼看着家族覆灭,
哀嚎遍野?马车在丞相府门前停下。外面已经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禁军撞开大门的声音,
家仆的尖叫,女眷的哭喊,夹杂着器物破碎的声响,汇成一片绝望的嘈杂。这里,
曾是我生活了十六年的家。此刻,却成了人间炼狱。车门打开,萧玦率先下了车。
他身姿如松,立于一片混乱之中,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仿佛在欣赏一出早已写好剧本的戏。侍卫将我推下车。我站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
强迫自己站直身体。昔日熟悉的亭台楼阁,此刻被粗暴的士兵践踏。
一件件珍宝被随意地搬出,扔上板车。父亲、母亲、兄长……他们的身影在人群中被推搡着,
脸上是绝望和茫然。我的族人,我的亲人。前世,我为这一幕哭瞎了双眼。今生,
我的眼中只有一片冰冷的平静。萧玦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注视,侧过头,
冰冷的视线落在我脸上。我迎上他的目光,扯了扯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是的,
我回来了。看着吧,所有欠了我的,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全部讨回来!他的眸色,
似乎深沉了一瞬。5.判决下来得很快,苏家女眷,流放三千里,往极北苦寒之地。我,
苏晚卿,因“主动投靠”并献上“有用信息”,得摄政王萧玦“格外开恩”。
免去了教坊司的命运,却也成了他眼皮子底下的一名罪奴,跟随流放队伍。
这所谓的“恩典”,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更像一柄悬在我头顶的刀。队伍启程那日,
天色阴沉。我穿着粗布囚衣,混在昔日锦衣玉食的女眷中,显得格格不入。
她们看向我的眼神,混杂着嫉妒、怨恨,还有毫不掩饰的鄙夷。“瞧瞧,到底是大姐姐,
有手段,都这时候了还能攀上高枝。”说话的是我那庶妹苏晚柔,她向来嫉妒我的嫡女身份,
此刻更是尖酸刻薄。旁边的三婶娘也阴阳怪气地附和:“可不是,
咱们都得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受苦,人家却能得王爷青眼,啧啧。”她们的声音不大不小,
恰好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押送的官差听见了,只是冷漠地扫了我一眼,并未呵斥。
我垂着眼,仿佛没听见。萧玦的人确实给了我一些“优待”。比如,
每天能分到一块不算太硬的黑面馒头,还有一小囊浑浊的饮水。这点微不足道的生存物资,
在食不果腹、人人自危的流放队伍里,足以引爆最原始的恶意。她们不敢明着对我动手,
毕竟我是摄政王“点名”要留下的。但那些怨毒的视线,几乎要将我洞穿。
我默默承受着官差的呵斥,忍受着脚底磨出的血泡,还有越来越沉重的镣铐。我知道,
眼下的隐忍,是为了将来更彻底的爆发。示弱,只会引来鬣狗。必须找个机会,让她们知道,
我苏晚卿,即便沦为阶下囚,也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机会很快就来了。
队伍行至一处荒滩,短暂休息。官差们聚在一起赌钱,囚犯们则瘫坐在地上,
争抢着最后一点水。我找到一个避风的角落,刚打开水囊,准备润润干裂的嘴唇。
一个枯瘦的身影猛地撞了过来。啪嗒一声,我那宝贝的水囊掉在地上,仅剩的半囊水,
瞬间渗入干燥的沙土。是张嬷嬷。前世在流放路上,她没少克扣我的吃食,甚至在我病重时,
将我推出破庙,任我自生自灭。如今,她枯黄的脸上,带着一丝得逞的快意。
周围几个和她相熟的婆子也发出低低的嗤笑。我慢慢抬起头,看着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只有一片死寂的平静。张嬷嬷被我看得有些发毛,
强撑着嚷道:“看什么看?自己不小心,还怪老婆子我?”我没说话,只是缓缓站起身,
拍了拍囚衣上的尘土。然后,在所有人诧异的注视下,我弯腰,捡起了空空的水囊。那眼神,
让张嬷嬷莫名地打了个寒颤。队伍继续前行,日头更毒。下一个取水点在一处浑浊的溪流旁。
地势有些陡峭,岸边布满了湿滑的青苔。官差们不耐烦地催促着,限定了取水时间。
囚犯们蜂拥而上,推搡着,争抢着靠近水源。我故意落在后面,观察着地形。
张嬷嬷仗着自己还有几分力气,挤在前面,好不容易打满了水囊,正要转身。我算准了时机,
在她转身的瞬间,“不小心”被后面的人推搡了一下,踉跄着撞向她。同时,我的脚尖,
极其隐蔽地勾了一下她站立不稳的脚踝。“哎哟!”张嬷嬷惊呼一声,脚下一滑,
整个人失去平衡,噗通一声摔倒在地。满满一囊水泼了她自己一身,混合着岸边的污泥,
让她瞬间变成了一个泥人。更倒霉的是,她摔倒时,
还撞翻了旁边一个凶神恶煞的女囚的水罐。那女囚本就憋着火,立刻破口大骂,
对着张嬷嬷拳打脚踢。“你个老不死的!找死是不是!”混乱引来了官差。他们本就烦躁,
见张嬷嬷一身污泥,又惹是生非,二话不说,扬起鞭子就抽了过去。“磨蹭什么!
耽误了行程,扒了你的皮!”鞭子落在皮肉上的声音,凄厉的惨叫声,还有官差的怒骂声,
交织在一起。我冷漠地站在人群外围,看着这一切。用最低的成本,达成了最好的效果。
周围看向我的眼神,多了一丝畏惧。这就够了。6.这一切,自然落入了暗处那双眼睛里。
萧玦派来“看管”我的人,如同影子,无处不在。想必,此刻我的所作所为,
已经一字不落地传回了萧玦耳中。他会怎么想?觉得我心肠歹毒,手段狠辣?还是,
觉得我这把“刀”,磨得更锋利了些?我无从得知,也不甚在意。我只在乎,能不能活下去,
能不能抓住一切机会,让那些曾经欺辱我、背叛我的人,付出代价。夜幕降临,
队伍在一片空旷的戈壁扎营。秋夜的风,已经带着刺骨的寒意。我分到的被褥单薄,
几乎无法抵御寒冷。前世,我就是这样一点点被冻垮了身子。我蜷缩在角落,
尽量减少热量的流失,牙齿忍不住微微打颤。就在我意识模糊,几乎要冻僵的时候。
我感觉身下的被褥似乎动了一下。有什么东西,硬硬的,暖暖的,被塞了进来。我一个激灵,
瞬间清醒。伸手一摸,是一个小巧的铜制手炉。里面残余的炭火,散发着微弱却珍贵的暖意。
谁给的?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望向不远处。在众多简陋的帐篷中,有一顶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材质和驻扎位置都透着不同的随行帐篷。那是萧玦的。是他吗?那个冷酷的,
视人命如草芥的摄政王?他为什么要给我一个暖炉?是心血来潮的施舍?
还是对他那件“有趣宠物”的另类关照?我握紧了那个小小的暖炉,感受着掌心传来的温度。
心绪,却前所未有的复杂。那个暖炉,最终还是冷了。正如萧玦这个人,
偶尔流露出的那么点难以捉摸的“善意”,转瞬即逝,虚无缥缈。我把它藏在贴身衣物里,
铜的冰冷触感提醒着我,依靠别人是多么可笑。7队伍进入了一片真正的荒原。黄沙漫漫,
寸草不生,烈日悬空,将地面烤得滚烫。水源开始枯竭,仅有的那点存粮也见了底。
恐慌如同瘟疫,比疾病蔓延得更快。我记得这里。前世,就是在这片绝望之地,
我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无人问津,无人施舍一口热水,最后身体彻底垮掉,
为冻毙流放路埋下了伏笔。咳嗽声在队伍中断断续续地响起,有人开始病倒。
押送的官差愈发暴躁,对病倒的囚犯非打即骂,丢在原地任其自生自灭也是常有的事。
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体面。凭借着模糊却深刻的记忆,我脱离了大队伍一些,
在一处不起眼的沙丘背面,找到了一小片湿润的沙地。往下挖了不到半尺,
果然渗出了浑浊却救命的水源。我用破陶碗小心地盛着,过滤掉大部分泥沙。
附近还生长着几种不起眼的、带着小刺的绿色植物。前世逃亡时,曾有老者告诉我,
这种叫“刺蓬”的东西,根茎可以少量食用,还能缓解水土不服引起的腹泻。我挖了些根茎,
用衣角擦去泥土,藏好。做完这一切,我悄悄回到了队伍边缘,
只将找到的水和少量根茎分给了始终跟在我身边的忠仆翠环。她早已饿得面黄肌瘦,
看到水和食物,眼圈瞬间红了,却懂事地没发出任何声音,只是狼吞虎咽。
“**……”她声音哽咽。“嘘,活下去。”我拍了拍她的手。不远处,
为了争夺官差丢下的半块发霉饼子,我的好婶娘和另一个囚犯撕打在一起,头发散乱,
衣衫不整,泼妇一般。曾经高高在上、锦衣玉食的贵妇人们,如今为了几口吃的、一口水,
就能扭打成一团,丑态百出,毫无尊严可言。她们看向我的方向,充满了嫉妒和怨毒。
大概是奇怪为何我还如此“干净整洁”。我垂下眼睑,内心毫无波澜。这些所谓的亲族,
前世在我落难时,哪个不是落井下石?她们的死活,与我何干?复仇的火焰,
在我心中烧得更旺,支撑着我在这炼狱中保持清醒。我的异常举动,
终究还是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队伍里,有一个穿着囚服却气质迥异的老者。他头发花白,
腰杆却挺得笔直,据说是前朝的礼部侍郎,因谏言忤逆了萧玦,才落得如此下场。
他观察我好几天了。此刻,他拄着一根树枝,慢慢踱到我附近。“小姑娘,在这等绝境,
还能如此镇定自若,不简单呐。”他声音沙哑,带着审视。我抬起头,
平静地回视他:“老大人过奖了,不过是想活下去罢了。”这老狐狸,看似闲聊,实则试探。
他笑了笑,皱纹堆叠:“老夫观你并非池中之物。这流放之路,危机四伏,单打独斗,难呐。
若你我能相互照应……”拉拢我?还是想利用我?前世的教训告诉我,不可轻信任何人,
尤其是这种官场失意、心机深沉之辈。我微微欠身:“老大人说笑了。
晚卿如今不过一介罪奴,朝不保夕,如何能与老大人相互照应?只求苟延残喘罢了。
”我态度恭敬,却滴水不漏,既不攀附,也不得罪。老者眼中闪过一丝意味不明的光,
不再多言,转身离开。傍晚时分,天色骤变。狂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而来。沙尘暴!
队伍瞬间大乱,风沙迷眼,人人自顾不暇,官差的呵斥声都被风声吞没。能见度极低,
一片混乱。这正是我需要的时机。我用布巾蒙住口鼻,顶着狂风,悄悄逆着人流移动。
混乱中,我看见了那个对我一直隐含恶意的庶妹苏婉柔。
她正惊慌失措地护着怀里的一个小布袋,那里装着她仅剩的干粮。前几天,
她还仗着有几分姿色,试图勾引一个年轻的官差,换取一点额外的食物,
结果被那官差的老婆当众扇了几个耳光,颜面尽失。这笔账,她似乎也算在了我头上。
我低下身,趁着风沙最大、无人注意的瞬间,快速靠近她。手指一动,
将我之前偷偷收集的一种带有毒性的草籽粉末,无声无息地撒进了她那宝贝似的干粮袋里。
做完这一切,我立刻退开,混入慌乱的人群中,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8.风沙终于停歇。
灰蒙蒙的天空下,队伍狼狈不堪。人人脸上、身上都覆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咳嗽声此起彼伏。
我清理着身上的沙尘,动作不紧不慢。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沉寂。“啊——我的肚子!
好痛!”是苏婉柔。她蜷缩在地上,脸色惨白,额头冒着冷汗,捂着肚子翻滚哀嚎,
嘴角甚至溢出了白沫。几个官差皱着眉上前查看。苏婉柔用尽力气抬起手,
颤抖地指向我:“是她!是苏晚卿!她在风沙里……靠近我……在我的干粮袋里下毒!
她要害死我!”所有人的视线瞬间聚焦在我身上。有惊愕,有怀疑,
更多的是幸灾乐祸和怨毒。尤其是那些曾经巴结我、如今却处处看我不顺眼的苏家旁支女眷。
“我就说她不对劲!一个娇滴滴的大**,怎么可能这么能熬!”“肯定是她!
嫉妒婉柔还有吃的!”嘈杂的议论声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我站在原地,
掸了掸衣袖上最后的沙土,迎着那些不善的视线,表情平静。苏婉柔还在哭嚎:“官爷!
就是她!我的干粮……肯定被她动了手脚!我只吃了那个啊!”一个领头的官差走到我面前,
脸色不善:“她说你下毒,可有此事?”我抬眼看他,语气无波无澜:“大人明鉴,
我与庶妹同为流放之人,身无长物,哪来的毒药?又为何要害她?”“你胡说!你就是恨我!
”苏婉柔挣扎着尖叫,“你肯定是藏了什么阴毒的东西!”我没理会她的嘶吼,
转向官差:“大人若不信,可搜我的身,也可检查我的物品。看看是否有她所说的毒药。
”我又看向地上痛苦的苏婉柔:“庶妹,沙尘暴时人人自顾不暇,
你确定自己只吃了布袋里的干粮?那风沙那么大,地上有什么东西吹进嘴里,
或是慌乱中捡了什么不认识的野果充饥,也未可知。”我这话意有所指。
苏婉柔的哭嚎顿了一下,眼神闪过一丝慌乱,但随即更凄厉地喊道:“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乱吃!就是你下的毒!”她一口咬定。但我捕捉到了她那一瞬间的心虚。看来,
我之前偷偷扔在她附近的几颗有毒野果,她果然没忍住。“大人,”我再次开口,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我所食用的,不过是些沿途寻来的野菜根茎,喏,就是这些。
”我从贴身的破布包里,拿出几根洗剥干净、但看起来依然粗糙的草根和野菜叶子。
“这些东西,或许队伍里有长于乡野之人能够辨认,是否有毒,一问便知。
”我特意看向了那个前朝礼部侍郎。他正站在人群外围,神色莫测地看着这场闹剧。
官差顺着我的示意看过去,显然也认得这位特殊的“囚犯”。“老先生,你可认得这些东西?
”官差扬声问道。老侍郎拄着树枝,慢悠悠走上前,拿起我手中的一根草药闻了闻,
又看了看叶子:“此乃『清风藤』,可解暑气,无毒。这个是『地黄』的根茎,
饥荒时可充饥,性微寒,亦无毒。”他放下草药,浑浊的眼睛扫过我和地上的苏婉柔,
慢条斯理地补充了一句:“不过,荒野之中,形似的草木甚多,有些颜色鲜艳的野果,
看似诱人,实则可能含有剧毒。饿极了,慌不择食,误食了也是常有的事。”这话一出,
苏婉柔的脸色更白了。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也露出了然的神色。官差不是傻子,看看我的坦荡,
看看老侍郎的话,再看看苏婉柔那明显心虚的反应,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他厉声呵斥苏婉柔:“够了!既无证据,休得胡言乱语,扰乱队伍!我看你就是饿晕了头,
自己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他又转向其他人:“都散了!再有下次,休怪我不客气!
”苏婉柔又惊又怕,还想辩解,却被官差不耐烦地打断:“来人,给她灌点水,
找个角落让她待着,死不了就行!”没人再理会她的哭喊。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我冷静地收起我的“食物”,感受到周围投来的视线已经变了。有忌惮,有审视,
也有了那么一点点不易察觉的敬畏。我知道,这次立威是必须的。在这条流放路上,
善良和软弱只会招致毁灭。那个老侍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难明,然后转身走开。
远处的隐蔽角落,一道黑影悄无声息地退去,将这里发生的一切,
事无巨细地传回了千里之外。据说,摄政王萧玦听完汇报,批阅奏折的手,微微停顿了一下。
队伍继续前行。苏婉柔吃了大亏,又被官差警告,总算安分了不少,
只是看我的眼神如同淬了毒。我毫不在意。几日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第一个中转驿站。
说是驿站,其实不过是几间破败的土房,供押送的官差和过往的信使短暂歇脚。
流放犯只能在驿站外的空地上宿营。即便如此,能有片刻休整,也是难得。
官差们去驿站里喝酒打尖,对我们的看管松懈了不少。9.驿站的嘈杂几乎能掀翻屋顶。
官差的吆喝,流放犯的低泣,还有牲口的嘶鸣混杂在一起。我缩在墙角,
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水囊里的水带着一股土腥味,但我还是小口咽下。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闯入视线边缘。青色布衣,洗得发白,背微驼,正对着驿丞点头哈腰,
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张德!心脏骤然缩紧,随即是翻江倒海的恨意。前世,就是他,
父亲一手提拔的门生,在最关键的时候,呈上伪造的书信,狠狠地在苏家背后捅了一刀!
他怎么会在这里?看他这副落魄潦倒的样子,显然是被新主子用完就丢了。真是报应!
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注视,或者说,是认出了我这张尚有几分昔日模样的脸。
他朝着我的方向走来,脸上那谄媚的笑瞬间变成了毫不掩饰的鄙夷和恶意。“哟,
这不是苏大**吗?”他啧啧两声,围着我走了半圈,像是在打量一件货物,“怎么?
丞相府的金丝雀,如今也落到这步田地了?”他的声音不大不小,
刚好让周围几个竖着耳朵的流放犯听见。我垂下头,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嵌进掌心。
“苏大**,别来无恙啊。”张德显然很满意我的“示弱”,蹲下身,试图抬起我的下巴,
“啧,这小脸还是这么水灵,可惜了,要在这苦寒之地熬着。不如……”他的手即将碰到我。
我猛地抬起头,避开他的触碰,冷冷地看着他:“张大人,别来无恙。”他愣了一下,
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种反应。随即恼羞成怒:“放肆!一个罪奴,还敢这般态度?
”他扬手就要打下来。我没有躲闪,余光却瞥见不远处一个角落里,
坐着一个满脸横肉、眼神凶悍的壮汉。那人穿着囚服,手脚都戴着镣铐,
却依旧透着一股戾气。我记得他,是个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这次也被一同押送。
“张大人息怒。”我声音不大,却带着一丝奇特的意味,“您如今也是戴罪之身,
何必与我一个弱女子计较?万一惊动了官爷,
惹了那位……”我悄悄朝那凶悍的逃犯方向偏了偏头。张德顺着我的暗示看过去,
脸上闪过一丝忌惮,但随即被更大的屈辱感淹没。“你个**!死到临头还敢威胁我?
”他怒吼着,口沫横飞,“老子就算落魄了,捏死你也像捏死一只蚂蚁!
”他猛地朝我扑过来,想要抓住我的头发。就在他靠近的瞬间,我看似慌乱地向后一缩,
脚下“不小心”踢到了旁边一个装着杂物的破筐子。筐子翻倒,里面的东西滚落一地。其中,
有一块我之前藏起来的、磨得有些发亮的碎银,恰好滚到了那凶悍逃犯的脚边。
逃犯本就心情烦躁,被这动静一惊,低头看见脚边的碎银,眼中立刻放出贪婪的光。而张德,
此刻一心只想抓住我泄愤,根本没留意脚下,更没看到那块碎银。他扑了个空,身体前倾,
正好撞向那逃犯的方向。“滚开!”逃犯一把推开差点撞到他身上的张德,
同时迅速弯腰捡起了那块碎银。张德被推得一个趔趄,定睛一看,
发现自己的“猎物”没抓到,反而被一个囚犯推搡,顿时怒火中烧:“狗东西!你敢推我?
把东西交出来!”他大概以为那碎银是逃犯的,或者只是想找个由头发泄。
逃犯本就是亡命之徒,脾气暴戾,到手的银子哪肯交出?
更何况是被张德这种一看就是软柿子的小人呵斥。“找死!”逃犯低吼一声,
挥起带着镣铐的拳头就砸了过去。张德哪里是这亡命徒的对手?只一下就被打翻在地。
“哎呀!杀人啦!”我适时地发出一声惊呼,声音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恐惧和慌乱。
驿站里本就混乱,这一声尖叫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包括正在里面喝酒的官差。
几个官差骂骂咧咧地冲了出来,看到扭打在一起的两人,更是火冒三丈。“住手!
都给老子住手!”逃犯自然不听,对着地上的张德拳打脚踢。张德被打得鼻青脸肿,
哀嚎不止。我挤上前去,脸上满是“焦急”和“无辜”:“官爷,官爷!快拉开他们!
张大人他……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想跟这位大哥说句话,不知怎么就……就打起来了!
”我一边“劝架”,一边悄悄用脚尖将旁边一块尖锐的石头踢到了扭打的中心。
“张大人还说……说这位大哥看着不像好人……哎呀,官爷,您快管管吧!
”这话如同火上浇油。那逃犯下手更狠了。官差费了好大力气才将两人分开。
张德已经奄奄一息,脸上血肉模糊。“吵什么吵!都带走!”为首的官差怒喝道,
让人把凶悍的逃犯重新锁好,又嫌恶地踢了踢地上的张德,“还有这个废物,拖到柴房去,
死不了就让他自生自灭!”张德被两个衙役像拖死狗一样拖走了,连哼唧的力气都没有。
一场闹剧结束,周围的人看我的神情更加复杂。我低下头,退回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