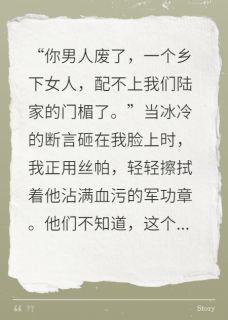
“你男人废了,一个乡下女人,配不上我们陆家的门楣了。”当冰冷的断言砸在我脸上时,
我正用丝帕,轻轻擦拭着他沾满血污的军功章。他们不知道,
这个躺在病床上被宣判死刑的男人,是我两世的执念。更不知道,我这双只会纳鞋底的手,
也能拿起手术刀,从阎王手里抢人。他们以为我是菟丝花,我偏要活成食人花,
把所有欺他、辱他、害他的人,全部拉下马!01“嫂子,不好了!陆营长出事了!
”尖锐的叫喊声刺破军区大院宁静的午后,我手里的搪瓷缸“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滚烫的开水溅在脚背上,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下一秒,我被一群穿着军装的男人围住,
为首的李政委脸色凝重如水:“苏晚同志,有个不幸的消息要通知你。
陆深在边境执行任务时遭遇伏击,身负重伤,目前……目前情况非常不乐观。”他话音未落,
身后大院里的军嫂们已经炸开了锅。“我就说这个苏晚是个扫把星吧?陆营长要不是娶了她,
能这么倒霉?”“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字都认不全几个,除了那张脸一无是处,这下好了,
陆营长成了废人,她不得哭死?”尖酸刻薄的话语像针一样扎过来,簇拥在我身边的,
是看热闹的嘴脸和幸灾乐祸的眼神。他们都在等,
等我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人”瘫在地上撒泼打滚,哭天抢地。可我没有。
我只是异常平静地拨开人群,目光直直地望向李政委,
声音里听不出一丝波澜:“带我去见他。”李政委愣住了,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种反应。
周围的议论声也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我叫苏晚,
大院里人人瞧不起的乡下媳妇。我的丈夫是战功赫赫的冷面兵王陆深。三個月前,
他从乡下把我接来,给了我一个家。没人知道,我是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的。上一世,
陆深为了救我,死在了我面前,那是我一辈子的梦魇。这一世,我只想护他周全。
“苏晚同志,你要有心理准备,陆深他……”李政委欲言又止。“他没死,就不是问题。
”我打断了他,眼神里是与我柔弱外表不相符的坚定。我抬手,
下意识地捻了捻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上那根快要脱落的线头。
这是我前世做高难度手术前的小动作,能让我瞬间冷静下来。现在,我的战场来了。陆深,
这一次,换我来救你。02军区总医院的特护病房外,白色走廊弥漫着刺鼻的来苏水味。
“病人颅内出血,脊椎神经严重受损,双腿彻底失去知觉,能保住命已经是奇迹了。
”主治医生赵院长摘下口罩,疲惫地对我摇了摇头,“苏晚同志,我们尽力了。
陆营长他……这辈子可能都只能在床上度过了。”旁边,陆深的母亲,我的婆婆张兰芝,
两眼一翻,当场晕了过去。一时间,兵荒马乱。我扶住摇摇欲坠的婆婆,
将她交给旁边的人照顾,然后平静地对赵院长说:“谢谢您,赵院长,
我想单独和陆深待一会儿。”赵院长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同情:“去吧,
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推开病房的门,陆深安静地躺在床上,脸上扣着氧气面罩,
昔日英气逼人的脸庞此刻苍白如纸。床头的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而微弱的“滴滴”声,
像在为他的生命倒计时。我走过去,俯下身,轻轻拂开他额前被汗水浸湿的碎发。“陆深,
我来了。”他没有任何反应。我深吸一口气,伸出手,看似笨拙地帮他**着手臂和双腿,
实则指尖精准地落在几个关键的穴位上。这是我前世作为顶级神经外科医生,
结合中西医理论独创的“唤醒疗法”,专门用于**深度昏迷病人的神经元。一下,
两下……我的动作不疾不徐,每一个按压的力度和频率都经过了精密的计算。
大约过了十分钟,奇迹发生了。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形,突然出现了一个微小但清晰的波动!
原本平稳的“滴滴”声,节奏加快了一瞬!恰好此时,一个年轻的护士推门进来换药,
她瞥了一眼监护仪,惊呼出声:“咦?病人的心率刚才是不是有变化?
”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再定睛一看,数据又恢复了平稳。我直起身,
对她微微一笑:“可能是我刚刚跟他说话,他听见了吧。”护士将信将疑地走了。我转过头,
看着陆深依旧沉睡的脸,嘴角勾起一抹无人察觉的弧度。陆深,欢迎回来。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我会让你重新站起来,站在所有人的面前,拿回属于你的一切。但在此之前,
我得先解决掉那些想趁你病,要你命的豺狼。03陆深出事,不仅仅是意外重伤那么简单。
第二天,两名穿着中山装,神情严肃的男人就找上了门。他们是军区纪律部门的,
前来调查陆深“里通外敌”的嫌疑。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大院里彻底引爆了。“天呐!
陆营长居然是叛徒?”“我就说苏晚这个女人有问题,说不定就是她唆使的!
”流言蜚语如潮水般将我淹没。而这次的“发难者”,
正是大院里一直与我作对的文工团台柱子,刘丽。她父亲是后勤部的副主任,
一直想把她嫁给陆深,却被我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截了胡。“调查员同志,
你们可要好好查查这个苏晚!”刘丽站在人群中,义愤填膺地指着我,“她一个乡下女人,
凭什么能嫁给陆深?我听说她来路不明,说不定就是敌特派来的!
”调查员的目光锐利地落在我身上。我没有理会刘丽的叫嚣,
只是平静地给两位调查员倒了杯水,轻声说:“同志,请问,你们说陆深里通外敌,
有证据吗?”“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搜到了这个。
”为首的调查员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封用外文写的信,
和一张陆深与一个金发男人的合影。刘丽立刻添油加醋:“看吧!人赃并获!陆深百口莫辩!
”我拿起那封信,看了一眼,笑了。“就凭这个?”我抬头看向调查员,
眼神清澈又带着一丝嘲讽,“同志,这上面的俄语语法错了三处,用词像是三十年前的风格,
还有,这张照片,P图的痕迹也太明显了点吧?你看这光影,跟玩似的,这技术,
搁我们村口照相馆的王大爷看了,都得说一句‘闹呢’。”我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
一个乡下女人,居然认识俄语?还知道P图?刘丽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你……你胡说!
你一个文盲,怎么可能懂这些!”“略懂。”我将信和照片推回调查员面前,
不咸不淡地开口,“我只是觉得,用这种漏洞百出的东西来陷害一个为国流过血的英雄,
是不是太儿戏了点?”我的目光转向刘丽,嘴角似笑非笑:“刘丽同志,你说得都对,
但你下一句话,最好能拿出点和你爹职位匹配的智商来,不然我真替王副主任的脸发愁。
”刘丽被我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为首的调查员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收起了信和照片,
神情缓和了许多:“苏晚同志,你的意见我们会记录在案。打扰了。”送走调查员,
我关上门,隔绝了门外所有的目光。靠在门板上,我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这只是开胃菜。
对方既然出手,就绝不会这么轻易收手。我需要钱,需要很多钱,不仅为了陆深的后续治疗,
更为了有足够的资本,去把幕后的黑手揪出来。04陆深的工资卡和家里的存款,
因为“调查”被冻结了。婆婆急得团团转,我却已经有了计划。眼下是八十年代末,
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了神州大地,市场经济开始萌芽。我知道,
这是一个遍地黄金的时代。我跟婆婆说要回娘家一趟筹钱,
然后换上了一身最不起眼的旧衣服,坐上了去市里的绿皮火车。我没回娘家,
而是直奔市里最大的机械厂——红星机械厂。凭借前世对机械工程的记忆,
我知道红星厂最近因为一台从德国进口的精密机床频繁故障而头疼不已,生产线几近瘫痪,
厂长急得嘴上都起了燎泡。我找到厂长办公室,开门见山:“厂长,我能修好你们的机床。
”五十多岁的孙厂长正对着一堆图纸发愁,闻言抬头看了我一眼,
见我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去去去,小姑娘家家的,
别在这儿添乱。”“如果我修不好,分文不取。”我平静地说道,“如果修好了,
我也不要多,给我这个数。”我伸出了五根手指。“五百?”孙厂长嗤笑一声。“五千。
”我纠正道。在人均月工资只有几十块的年代,五千块无疑是一笔巨款。
孙厂长像看疯子一样看着我,但看着车间里停摆的生产线,
最终还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咬牙道:“好!你要是真有这本事,别说五千,
我给你包个六千的大红包!”我被带到那台巨大的德国机床前,周围围了一圈厂里的技术员,
都用看神棍的眼神看着我。我没有理会他们,围着机床走了一圈,听了听声音,
又问了几个关于故障表现的问题,不到十分钟,就找到了症结所在。“不是机器的问题,
”我拿起一支粉笔,在一块小黑板上迅速画出了一个零件的结构图,
“是你们的操作流程和日常保养手册,翻译错了。这个‘阻尼调节阀’的扭矩参数,
应该根据环境湿度进行动态调整,而不是一个固定值。”我一边说,一边拿起扳手,
在几个技术员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精准地对机床的几个部位进行了微调。“好了。
”我拍了拍手上的灰尘,“现在可以开机了。”孙厂长将信将疑地按下了启动按钮。下一秒,
沉寂了半个月的机床,发出了流畅而平稳的轰鸣声。整个车间,
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孙厂长激动地握住我的手,眼眶都红了:“神了!
真是神了!姑娘,你真是我们厂的大救星!”当天,我带着一个装满了六千块现金的帆布包,
离开了机械厂。走出厂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手腕上,
一个前世做实验时被烫出的月牙形浅疤,在阳光下若隐若现。我摸了摸那个疤痕。陆深,
等我。我们的弹药,够了。05带着钱回到医院,
我立刻用“托关系从海外买来的特效药”为由,
给陆深安排上了最好的营养支持和“特殊治疗”。当然,这些都是幌子,真正的治疗,
全靠我每晚的“穴位**”和偷偷进行的针灸。半个月后,陆深在一个深夜,
悄无声息地睁开了眼睛。没有戏剧性的喊叫,没有剧烈的动作,他就那么安静地看着我,
黑曜石般的眸子里,是从未有过的震惊和迷茫。他醒了,但身体还不能动,也无法说话。
我假装没发现,像往常一样,一边给他擦拭身体,一边絮絮叨叨地跟他说话。“陆深,
你知道吗,大院里的王婶又在说我坏话了,说你一倒下我就得卷铺盖滚蛋。我当时就想,
她是不是忘了,我户口本上可是你配偶,合法继承人,她这么盼着我走,
是想替我还你欠下的‘风流债’?”“还有刘丽,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在病房门口晃悠,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盘丝洞呢。你说她图啥?图你不能动,还是图你身上这身病号服特别帅?
”我用最轻松的语气,讲述着这些天发生的一切,将那些糟心事都编成了段子。
陆深的眼珠随着我的身影转动,眼神从最初的震惊,慢慢变成了心疼、自责,最后,
是深深的、化不开的柔情。他看到我眼下的乌青,看到我为了省钱啃着干硬的馒头,
看到我深夜里靠在他的床边打盹,看到我用瘦弱的肩膀,为他撑起了一片天。我能感觉到,
他的心,正在被一点点填满。这天晚上,我正准备给他做新一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