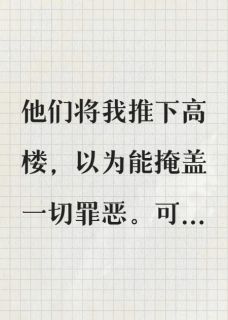
他们将我推下高楼,以为能掩盖一切罪恶。可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体成了地狱的容器,
装满了所有被他们残害的冤魂。现在,我们一起回来,讨还血债。【1】我重生了,
在霸凌我的校花乔雅的生日派对上。香槟塔折射着迷离的光,衣香鬓影间,
乔雅像个众星捧月的公主。她是今天的主角,而我,是她钦点的余兴节目。上一世,
就是在这里,他们逼我喝下一整瓶烈酒,把我打扮成小丑的模样,
拍下无数羞辱的照片发到校园墙。那是我坠入深渊的开始,无休止的欺凌,
直到我被他们从废弃的教学楼顶推下。冰冷的风刮过耳畔,身体失重的感觉,
我至今记忆犹新。可现在,我好好地站在这里。不,不只是我。我的脑海里,
拥挤着好几个尖利、怨毒的声音。「是她!乔雅!这个**,她把我关在体育器材室,
看着我哮喘发作活活憋死!」「还有那个张昊!他把我拖进厕所,打断了我的腿,
就因为我看了他女朋友一眼!」「陈曼那个长舌妇,她造谣我**,逼得我跳了河……」
这些声音,属于那些和我一样,被乔雅和她的团伙欺凌至死的冤魂。
我们一同被困在死亡的瞬间,又一同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塞回了我这具十六岁的身体里。
我的身体,成了他们的复仇容器。「林默,发什么呆呢?」乔雅的声音甜得发腻,
她端着一杯酒,袅袅婷婷地走到我面前,眼里的轻蔑和恶意毫不掩饰,「今天我生日,
你怎么也得表示一下吧?」周围的人发出一阵哄笑,等着看我的好戏。我抬起头,
对上她漂亮的眼睛。在他们惊愕的注视下,我没有像上一世那样瑟缩发抖,反而微微一笑。
我从身后拿出一个精致的纸盒,递了过去。「乔雅,生日快乐。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礼物。」
乔雅狐疑地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个纸人。那纸人穿着和她身上一模一样的公主裙,
梳着一样的发型,甚至连脸上那颗小小的泪痣都分毫不差。它被做得栩栩如生,
眉眼间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派对上的音乐仿佛停滞了一瞬。
一个跟班的女生尖叫起来:「天啊,好晦气!生日送纸人,林默你是不是疯了?」
乔雅的脸色也瞬间变得惨白,她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将盒子摔在地上。「林默!你什么意思!
」我弯下腰,温柔地捡起那个纸人,用指尖抚平它裙摆的褶皱,轻声说:「别怕,
她不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的声音很轻,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我看着乔雅,
笑容越发灿烂:「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手艺,叫『替身偶』。据说,
它可以替主人承受一切灾祸和病痛……当然了,也能分享一切。」我顿了顿,
一字一句地补充道:「包括,死亡。」乔雅的瞳孔骤然紧缩。
我将纸人小心翼翼地放回她手中,指尖若有若无地擦过她的手背,
冰冷得像一块刚从停尸间拿出来的寒冰。「收好哦,千万别弄丢了。」说完,我转身离开。
身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和乔雅那双淬了毒的眼睛。走出奢华的别墅,晚风吹起我的头发。
我脑海里的声音兴奋地尖叫起来。「对!就是这样!吓死她!」「不够!这还远远不够!
我要她死!」我抬头望着天上的月亮,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别急。游戏,才刚刚开始。
我们,一个一个来。【2】复仇的第一个目标,是陈曼。她是乔雅最忠实的走狗,
一张嘴比淬了毒的刀子还利。上一世,关于我「被包养」、「精神不正常」、「偷东西」
的谣言,全都出自她口。她享受着将别人踩在脚下,看他人在流言蜚语中痛苦挣扎的**。
那个因她而死的女孩,在我脑中哭诉着,
她的声音充满了泡沫破裂般的绝望:「我只是……只是穷了点,我拼命打工,
她就说我出去卖……我妈信了,打了我一顿,把我锁在家里,我就从窗户上跳了下去……」
「我知道了,」我轻声安抚她,「她的舌头,我会帮你拔掉。」我们家是开纸扎铺的,
爷爷是远近闻名的纸扎匠人。这项手艺传到我父亲这辈,已经没什么人信了,
只当是门赚死人钱的生意。可爷爷偷偷教过我,我们扎的,不只是给死人看的玩意儿,
更是与另一个世界沟通的媒介。放学后,我把自己关在老宅的工作间里。
空气中弥漫着竹篾和纸浆的清香。我点上一炷安魂香,脑海里那些嘈杂的声音渐渐平息,
只剩下那个跳河女孩微弱的哭泣。我闭上眼,用心感受她的怨与恨。然后,我动了手。
我没有用纸,而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泡过尸水的糯米纸。这种纸极阴,
最容易承载咒怨。我将它反复捶打,塑成一条鲜红的、还在微微颤动的舌头。舌根处,
我用朱砂画上了一道「噤声符」。最后,我将陈曼的一根头发缠在了纸舌的根部。
那是今天上课时,我趁她不备,从她椅子上捡来的。做完这一切,天已经黑了。
我将那条纸舌头悄悄塞进了陈曼的书包夹层里。第二天,好戏开场了。第一节是语文课,
老师让同学起来轮流朗读课文。轮到陈曼时,她像往常一样得意洋洋地站起来。
「《蜀道难》,噫吁嚱……」她刚开了个头,声音就卡住了,喉咙里发出一阵「嗬嗬」
的怪响,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全班同学都看向她。陈曼的脸涨得通红,
她使劲清了清嗓子,想继续往下读,可嘴巴张得老大,
却只能发出一些破碎的、不成调的音节。「呃……啊……危乎……高哉……」
她的声音变得嘶哑、难听,像砂纸在摩擦玻璃。「陈曼,你怎么了?嗓子不舒服吗?」
老师关切地问。陈曼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她拼命摇头,指着自己的嘴巴,想说什么,
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越急,喉咙里的声音就越古怪,最后,她在一片哄笑声中,
狼狈地坐了下去。一整天,陈曼都成了哑巴。不,比哑巴更可怕。她能发出声音,
但所有的话到了嘴边,都会变成毫无意义的噪音。到了下午,情况变得更加诡异。
她想说「给我一杯水」,说出口的却是「我是一条狗」。她想骂人,嘴里发出的却是「汪汪」
的狗叫。恐慌彻底攫住了她。她发疯似的冲出教室,跑向医务室。我们隔着窗户,
都能听到她那变了调的、惊恐的尖叫。我坐在座位上,面无表情地转着笔。脑海里,
跳河女孩的声音带着一丝解脱后的轻快:「谢谢你……」我没有回应。这点折磨,怎么够呢?
我要的,是她众叛亲离,被所有人当成疯子,在无尽的绝望和恐惧中,
体验我们曾体验过的一切。放学时,我看到陈曼的父母来接她。她哭着想向父母解释,
可嘴里说出的,却是各种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她母亲的脸色从担忧变成震惊,
最后变成愤怒和羞耻。「啪!」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陈曼脸上。「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
在学校都学了些什么!」我站在不远处,冷冷地看着这一幕。陈曼捂着脸,
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嘴里还在徒劳地发出「汪汪」的叫声。真可怜。可是,
当她用最恶毒的语言,把另一个女孩逼上绝路时,她又何曾有过一丝怜悯?我转身,
融入黄昏的人流中。下一个,张昊。那个喜欢用拳头解决一切的暴力狂。我仿佛已经能听到,
他骨头碎裂的声音了。【3】张昊是校篮球队的主力,人高马大,性格暴躁。
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那一身蛮力。被他打断腿的那个男生,
在我脑中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只是个书呆子,他把我堵在墙角,一脚一脚地踹我的膝盖,
听着骨头碎掉的声音,他还在笑……」「别怕,」我告诉他,「他会尝到百倍的痛苦。」
对付张昊,我用的是另一种纸扎——「刑偶」。这是爷爷严令禁止我触碰的东西,
因为它过于阴损,有伤天和。但我现在,早已不在乎什么天和了。
我找来一张画着张昊全身像的照片,贴在一具用柳条扎成的骨架上。柳枝通阴,最能引魂。
接着,我用黑狗血混合朱砂,在纸人身上画满了代表「伤」与「痛」的符咒。每一个符咒,
都对应着一处关节,一处要害。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拔下自己的一根头发,
用针刺破指尖,将血滴在头发上,然后,将这根头发,绑在了纸人的脖子上。以我之血为引,
以我之身为桥,将所有怨念,渡给张昊。「来吧,」我对着脑海中的声音低语,
「把他曾经施加给你们的痛苦,都还给他。」无数怨恨的意念,顺着我的血,
涌入那具小小的纸人。纸人无风自动,发出一阵「咔咔」的脆响,仿佛骨骼在被一寸寸折断。
第二天,是学校的篮球联赛。张昊作为王牌,万众瞩目。比赛开始,他像一头猛兽,
无人能挡。带球、过人、上篮,动作行云流水。乔雅和一群女生在场边为他尖叫。
我坐在观众席的最高处,无人注意的角落,怀里抱着那个用黑布包裹的「刑偶」。
张昊高高跃起,准备来一个势大力沉的灌篮。就在他身体升到最高点的时候,我伸出手,
用一根淬了清漆的竹针,狠狠刺向纸人的右膝。「啊——!」一声凄厉的惨叫,
划破了整个体育馆。张昊在半空中,身体诡异地一扭,然后像一块石头一样,
重重地摔在地上。他抱着自己的右膝,在地上痛苦地翻滚,额头上青筋暴起,汗如雨下。
「我的腿!我的腿断了!」他嘶吼着,声音里充满了不解和恐惧。队医和教练立刻冲了上去,
可检查了半天,却发现他的膝盖完好无损,甚至连一点红肿都没有。「张昊,
你别自己吓自己,没事的!」教练试图扶他起来。可张昊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刚一动,
就发出更惨烈的嚎叫:「别碰我!疼!好疼啊!」那种疼痛,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
却又真实地啃噬着他的神经。我坐在高处,冷漠地看着他。然后,我拿出竹针,
对准了纸人的左肩,刺下。「啊!我的肩膀!我的肩膀也断了!」张昊的哀嚎声再次响起,
他整个人蜷缩成一团,像一只被踩烂了的虾米。接下来,
是手腕、脚踝、肋骨……我每刺一下,张昊就会在球场中央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诉说着一处新的「骨折」。整个体育馆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诡异的一幕吓呆了。
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他们面前,被无形的酷刑一寸寸摧毁。乔雅脸上的笑容早已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惊恐的惨白。她看着在地上抽搐的张昊,又下意识地朝观众席望来。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她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毫不掩饰的冰冷和快意。恐惧,
像藤蔓一样,缠上了她的心脏。她终于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巧合。最终,
张昊像一滩烂泥一样被抬了出去。他还在不停地尖叫,说有无数只手在撕扯他的身体,
在折断他的骨头。医生给他做了最全面的检查,CT、核磁共振,结果显示,
他身体好得不能再好,连一丝软组织挫伤都没有。他被当成了癔症,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脑中那个被打断腿的男生,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声音里带着解脱:「他终于也尝到这种滋味了……」复仇的**,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我。
可在这**之下,却有一股更深沉的冰冷。脑海里的声音,并没有因为复仇的成功而平息,
反而变得更加亢奋和贪婪。「杀了他!杀了他!」「不够!远远不够!我要他们神魂俱灭!」
一个最清晰,也最怨毒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那是我之前从未分辨出来的,一个陌生的女声,
她带着一种诡异的蛊惑:「林默,你做得很好。但是,还不够。乔雅才是主谋,
我们不能放过她。听我的,我知道一个方法,可以让她……永世不得超生。」这个声音,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压过了其他所有鬼魂。我皱了皱眉,警惕地问:「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那声音咯咯地笑了起来,「重要的是,我是帮你的人。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乔雅为什么那么恨你,从你一转学过来,就处处针对你吗?」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我和乔雅,素不相识,无冤无仇。她的霸凌,
来得毫无缘由,却又狠毒至极。「为什么?」那个声音幽幽地说:「因为,你长得,
很像一个人。一个……被她亲手害死的人。她不是第一个,你,也不是最后一个。」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了。「她是谁?」「她叫……萧柔。是乔雅曾经最好的朋友。」
随着这个名字被说出,一段不属于我的、血淋淋的记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了我的大脑。
那是在一艘私人游艇上,奢华的派对,年轻的男女。乔雅和另一个女孩,萧柔,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争吵中,乔雅失手将萧柔推下了海。所有人都看到了,
但所有人都选择了沉默。他们伪造了萧柔失足落水的假象,乔雅的父母动用权势,
将一切压了下去。而我,林默,一个无辜的转校生,
仅仅因为眉眼间有几分像那个死去的萧柔,就成了乔雅的眼中钉,
成了她用来掩盖内心恐惧和罪恶的替代品。她要通过折磨我,来证明自己没有错,
来告诉自己,那个「萧柔」是懦弱的,是活该被欺负的。「现在,你明白了吗?」
萧柔的声音在我脑中回响,充满了刻骨的恨意,「她怕你,她恨你这张脸。所以,
我们要毁了她最在乎的东西——她自己的脸,她的骄傲,她的一切!」「听我的,林默。
我知道一种最恶毒的纸扎术,叫做『画皮』。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把她的脸,
画到另一张纸上。而她自己的脸,会慢慢腐烂,剥落,直到变成一具无脸的枯骨!」
萧柔的声音充满了诱惑,她描绘的复仇蓝图,精准地踩在了我最痛的神经上。我被霸凌,
被羞辱,被推下高楼。陈曼和张昊的下场,只是开胃菜。乔雅,这个罪恶的源头,
必须付出最惨痛的代价。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却升起一丝不安。萧柔的恨,
太纯粹、太黑暗了,甚至让我这个复仇者都感到心惊。她不只是想要复仇,
她想要的是彻底的毁灭。「你在犹豫什么?」萧柔的声音变得冰冷,
「难道你忘了你是怎么死的吗?忘了她在你坠楼时,那轻蔑的笑声了吗?还是说,
你享受和我们这些鬼魂共用一个身体?」最后一句话,像一根毒刺,扎进我的心里。是的,
我不想。我不想永远被这些怨念和仇恨填满。我想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身体,
属于我自己的生活。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完成他们的复仇,让他们安息。「好。」
我闭上眼睛,下定了决心,「告诉我,怎么做。」萧柔满意地笑了起来。而我没有注意到,
在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我手腕上那道重生后出现的,形似符咒的红色印记,
颜色变得更加深邃,妖异得如同滴血。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乔雅的反击,
也即将来临。她不是陈曼和张昊那种蠢货,她已经开始怀疑,并且,在用她自己的方式,
寻找对抗我的力量。【4】乔雅的反击比我预想的来得更快,也更直接。她没有选择报警,
也没有告诉老师和家长。她知道,这些常规的手段,对付不了我这种「非正常」的存在。
她直接找到了我们家的纸扎铺。那天下午,我正在店里帮父亲整理货架,
一辆黑色的保时捷停在了门口。乔雅穿着一身黑色的连衣裙,戴着墨镜,
在一群跟班的簇拥下,走了进来。她摘下墨镜,那双漂亮的眼睛里不再有平日的傲慢,
而是充满了戒备和一丝压抑不住的恐惧。「林老板,」她没有看我,而是直接对我父亲说,
「我听说,您是这里手艺最好的纸扎匠人?」我父亲是个老实本分的中年人,
一辈子与纸打交道,哪里见过这种阵仗,连忙点头:「**,您有什么需要?」
「我最近……总是睡不好,做噩梦。」乔雅的声音有些发紧,「听人说,
可能是撞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想请您帮忙,做个纸人,替我挡挡灾。」她一边说,
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瞥着我,那眼神像是在试探,又像是在警告。我站在一旁,心里冷笑。
她果然开始行动了。她想用我家的手艺,来对付我。真是可笑。
父亲并不知道其中的弯弯绕绕,只当是来了大生意,热情地介绍起来:「没问题,
替身挡灾的纸人我们经常做。您需要提供生辰八字,还有一根头发或者指甲……」
「不用那么麻烦。」乔雅打断他,目光直直地射向我,「就让她给我扎。」她指着我,
语气不容置疑。父亲愣住了:「小默她……她还只是学徒,手艺不精,怕是……」
「我就要她。」乔雅的声音冷了下来,「钱不是问题。」说罢,
她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钞票,拍在柜台上。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我却走了出来,
平静地看着乔雅:「好,我帮你扎。」父亲惊讶地看着我,我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乔雅,
你以为找到了破局的方法吗?你太天真了。你这是亲自把自己的命门,送到了我的手上。
「跟我来吧。」我领着乔雅,穿过店铺,走向后院那个阴森的工作间。她的跟班想跟进来,
被我拦在了门外。「扎纸人,最忌阳气过重,闲人免进。」工作间里,光线昏暗,
四壁挂满了各式各样表情诡异的纸人。乔雅一进来,就下意识地抱紧了胳膊,脸色更加苍白。
「坐。」我指了指屋子中央的一张椅子。她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下了。我没有立刻动手,
而是绕着她,不紧不慢地走了一圈,像是在打量一件货物。「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
乔雅报出了一串数字。我拿出纸笔,一边记录,一边状似无意地问:「你最近,
是不是总感觉有人在看着你?尤其是在照镜子的时候。」乔雅的身体猛地一僵。
「是不是觉得,镜子里的人,越来越不像你了?皮肤开始松弛,眼睛里出现血丝,
嘴角也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下耷拉?」我每说一句,她的脸色就白一分。「你怎么知道?!」
她失声叫道,声音里带着惊恐。我停下脚步,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因为,那是我做的。」乔雅的瞳孔瞬间放大,她想站起来,
却发现双腿一软,根本使不上力气。「你……你到底想怎么样?」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想怎么样?」我俯下身,凑到她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
「我想把你那张漂亮的脸蛋,一点一点,从你骨头上剥下来。就像你,
把我从教学楼上推下去一样。」「是你!果然是你!」乔雅尖叫起来,
恐惧让她暂时忘记了伪装,「林默你这个疯子!你不得好死!」「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直起身,冷冷地看着她,「所以,没什么好怕的了。现在,轮到你了。」
我不再理会她的咒骂,开始动手扎纸人。这一次,我没有用糯米纸,也没有用柳条。
我用的是爷爷珍藏多年,用来扎「镇物」的桃木屑和金箔纸。
萧柔的声音在我脑中疯狂地尖叫:「不要用这个!林默!用我教你的『画皮』术!
毁了她的脸!」我没有理她。萧柔的恨意太过霸道,太过纯粹,我已经开始隐隐感觉到,
她的目的或许并不只是复仇那么简单。她似乎在引诱我走向一条更黑暗、更无法回头的路。
我不能完全被她控制。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完成这场复仇。桃木驱邪,金箔镇煞。
我要扎的不是害人的「刑偶」,而是一个「锁魂偶」。我要把乔雅的魂,锁在这个纸人里。
让她清醒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一天天衰败,腐烂,却无能为力。让她尝尽无尽的孤独和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