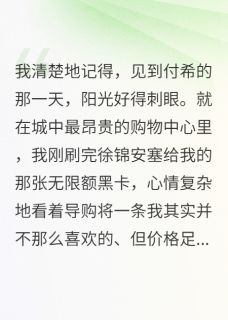
我清楚地记得,见到付希的那一天,阳光好得刺眼。就在城中最昂贵的购物中心里,
我刚刷完徐锦安塞给我的那张无限额黑卡,
购将一条我其实并不那么喜欢的、但价格足以让我从前在孤儿院吃上十年饱饭的裙子包起来。
一只柔软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我回头,对上一张笑得人畜无害的脸。她很可爱,
不是惊艳的美,但周身笼罩着一种奇异的光晕,让人忍不住想多看两眼,
心生好感——如果忽略掉她眼中那抹毫不掩饰的审视和玩味的话。“你好啊,
”她的声音甜得像裹了蜜,内容却冰冷刺骨,“辛苦你了,女配**。
把我家锦安弟弟……教养得还不错?”我瞳孔骤缩,浑身的血液似乎在这一瞬间冻住。
她知道了?她是谁?她仿佛能看透我的思想,轻笑出声,目光扫过我手中的黑卡,
语气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怜悯:“看来他对你这个‘姐姐’确实大方。不过,
情节的力量真是有趣,不是吗?即使过程有偏差,该走的过场还是要走。比如,我来了。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明白的,林溪。
”她凑近一步,声音压得更低,只有我们两人能听见,“替我完成了最麻烦的‘救赎’阶段,
真是谢谢了。但现在,正主登场,你这个垫脚石……是不是该识趣点,把男主还回来了?
”“凭什么?”一股无名火猛地窜起,混杂着连我自己都惊讶的不甘。“凭我是付希,
这个世界唯一的女主角。”她笑得越发甜美,却也越发残忍,“凭你再怎么努力,
也只是为他遇见我而存在的磨刀石。你的作用,到此为止了。安心等着退场吧,
看在你把他**得还算省心的份上,我会让你走得体面点。”她说完,
像只胜利的孔雀般翩然离去,留下我站在原地,手心冰凉,那张沉甸甸的黑卡硌得人生疼。
凭什么?就凭那该死的、我醒来第一天就强行塞进我脑子的“情节”吗?告诉我,
我只是徐家收养的、用来暂时安抚那个疯批少年徐锦安的工具人?告诉我,
我存在的意义就是在他最扭曲的时期陪伴他,磨去他过多的戾气,
然后在一个叫付希的真命天女出现时,功成身退,狼狈离场?去他妈的情节!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翻涌的情绪。是的,我在见到徐锦安的前一天“觉醒”了,知晓了这一切。但我林溪,
从来就不是认命的人。即使是一颗棋子,我也要跳出棋盘!最初的徐锦安,
确实如情节描述的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疯批美人。十四岁的少年,
已经有了惊艳众生的轮廓,金丝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遮住了眼底深处的偏执与阴郁。
他表面上谦和有礼,一口一个“姐姐”叫得乖巧,背地里却花样百出。
欢迎我的鲜花里藏着毒蛇;我最常坐的椅子上涂着让人奇痒无比的药剂;甚至我喝的水里,
也曾被下过轻微致幻的药物。他总是用最无辜的表情问:“姐姐,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我一次次按下怒火,告诉自己:这是任务,这是报恩,
徐家给了我孤儿院从未有过的优渥生活,我需要“教化”他。但我用的不是圣母般的包容,
而是更狠的硬碰硬。他把毒蛇放进我房间,
我第二天就能面不改色地拎着那条被炖熟的蛇(当然,是找专业人士处理的)放在早餐桌上,
笑眯眯问他:“锦安弟弟,听说蛇羹大补,尝尝?”他给我下药,
我就能在他常看的书页边缘涂上更刁钻的、只会让他短暂难受却查不出原因的粉末,
在他难受时“关切”地问:“是不是学习太累了?脸色这么差。
”我拆穿他每一个幼稚的阴谋,戳破他每一层虚伪的伪装。“你还小,尾巴藏不住。
”我曾把一枚他用来陷害我的、刻有特殊标记的胸针丢还给他,看着他瞬间僵硬的脸色,
心里莫名生出一丝奇异的成就感。这是一种危险的博弈。我在驯服一头猛兽,
同时也在被猛兽的爪牙磨砺。转折点发生在他高三那年。他连续几天回家都很晚,
身上带着若有似无的瘀伤,问他只说是打球撞的。直到班主任打来电话,
说他差点把同学打死在医院。我赶去学校,看到那个被打得不成人形的学生,
又看到站在办公室角落、面无表情却拳头紧握、眼底翻滚着骇人暴戾的徐锦安。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几乎失控的他。老师怒吼着要他给个说法。我压下心惊,
坚持其中有误会,要求单独和他谈。“为什么?”我第三次问他,
声音是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紧绷。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最终,他别开脸,
声音嘶哑低沉:“他**你……P了那种图,说要散播出去。”那一刻,
我所有准备好的说教和斥责都堵在了喉咙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酸涩难言。
他是因为我?我动用了所有能用的关系,威逼利诱,找到了证据,
逼得对方家长和学校公开道歉。
我替他挡下了来自徐父的狂风暴雨——那次徐父差点把他打死在客厅,
是我冲上去死死拦住了落下的棍棒。从医院陪护他醒来时,他看着我眼下的青黑,
指尖轻轻碰了碰我的眼角,声音虚弱却带着一丝别扭的温柔:“别哭……丑。”谁哭了?
我才没哭。只是眼睛进了沙子。我们的关系从那时起,变得微妙而复杂。
他不再对我使那些小动作,甚至会别别扭扭地给我带早餐,
在我生理期时默不作声地给我准备热水袋。他看我的眼神,
渐渐染上了我自己都不敢深究的依赖和……独占欲。我曾天真地以为,我改变了情节。
我花了那么多心血,
陪伴他从阴戾少年长成逐渐学会收敛爪牙、偶尔甚至能露出真实笑意的青年,
凭什么要拱手让人?但付希的出现,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我。徐父很快找到了我,
语气是惯常的冷漠威严:“林溪,你做得很好,徐家会记得你的功劳。
锦安和付希的婚事已经定下,你准备一下,毕业后出国深造,徐家会负责你所有的费用。
未来的徐氏需要你的能力,但锦安身边,不需要你。”看,情节的力量无处不在,
它用最现实的方式碾压我的妄想。那之后,我刻意疏远徐锦安。他却像察觉到了什么,
越发焦躁,黏我黏得更紧。高考结束那天,他冲出考场,抱着我转圈,
眼睛亮得惊人:“林溪!我们……”“我去给你买城北的桂花糕吧!”我打断他,
努力扬起一个最自然的笑,“庆祝你解放!那家很有名,我想吃很久了,也想带给你尝尝。
”他愣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失落,但还是点了点头,叮嘱我早点回来。我转身,
走向街对面停着的、付希的车。后视镜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
手里还傻傻地抱着我送他的那束向日葵。付希一边开车,一边轻笑:“断得干净点,
对谁都好。你放心,你‘养’得这么乖的男主,我会接手的。”我闭上眼,
感觉心脏那块空了一块,冷风呼呼地往里灌。我把驯服的野兽还给了情节,
却好像把自己的某一部分也弄丢了。异国的五年,我试图开始新生活。我拼命学习,打工,
努力把徐锦安,把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抛在脑后。
除了徐父定期打来的巨额生活费提醒着我过去的纠缠,我几乎快要成功了。
直到汇款突然中断。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回国一趟。我需要一个了结,
也需要弄清楚发生了什么。飞机落地,熟悉的空气扑面而来,带着一种令人心慌的潮湿。
我刚打开手机,试图研究国内陌生的打车软件,一辆黑色的轿车就无声无息地停在我面前。
车窗降下,司机帽檐压得很低:“打车吗?**。”晕机带来的不适让我头脑昏沉,
我没多想,报出徐氏集团大厦的地址,就瘫在后座闭目养神。车开了很久,
久到我察觉不对劲。睁眼看向窗外,心脏猛地一沉——这不是去市区的路!
周围景色越来越偏僻,最终停下的地方,是我刻在骨子里的熟悉——徐家郊区的别墅!
我惊恐地想开车门,却早已被锁死。驾驶座上的人缓缓摘下了帽子和口罩,转过头来。
时间仿佛在他身上精心雕琢过。十九岁的少年彻底褪去了青涩,五官轮廓愈发深邃凌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