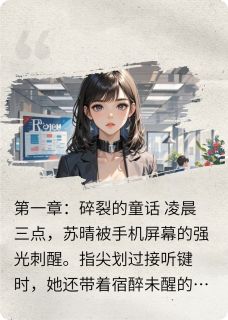
念念十岁那年,迷上了烘焙。每个周末都要霸占厨房,戴着小小的围裙,把面粉弄得满身都是。苏晴从不干涉,只在她烤糊了饼干时,笑着说:“没关系,下次调小十分钟火候试试。”
顾衍总说她太纵容孩子,苏晴却不以为然:“我十岁的时候,偷偷把家里的缝纫机拆了,想做条新裙子,结果被我妈追着打。现在想想,那股子折腾劲儿,不就是创业的雏形?”
话虽如此,当念念说想参加全市少儿烘焙大赛时,苏晴还是认真帮她研究食谱。她们在厨房试了二十多次,终于做出了一款玫瑰慕斯,用的是院子里新鲜采摘的玫瑰花瓣。
比赛那天,顾衍特意推掉会议,一家三口穿着亲子装坐在观众席。念念站在台上,个子还没料理台高,却像个小大人一样,有条不紊地打发奶油、铺蛋糕胚。
“她像你。”顾衍低声说,“上台从不怯场。”
苏晴摇摇头:“不像我,像她自己。”
她看着女儿专注的侧脸,突然想起自己第一次参加行业峰会的样子,紧张得手心冒汗,发言稿背了十遍还是忘词。而念念不一样,她眼里没有“输赢”,只有“我想做好”。这种松弛感,是苏晴四十岁才学会的功课,女儿十岁就懂了。
念念最终拿了二等奖,颁奖时主持人问她:“为什么想做玫瑰慕斯?”
小姑娘歪着头说:“因为妈妈说,玫瑰不仅好看,还能吃,就像人一样,能坚强也能温柔。”
台下的苏晴突然红了眼眶。原来那些不经意说的话,都在孩子心里发了芽。
那天晚上,苏晴收到陆哲远的短信。他出狱后开了家小超市,日子过得平淡,听说念念参加比赛,特意发来祝贺:“孩子很优秀,像你。”
苏晴回了句“谢谢”,没有多余的话。有些关系,就该停留在“知道你过得好”的距离里,不远不近,各自安好。
转年春天,苏晴的父亲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手术室外,苏晴看着母亲通红的眼睛,突然发现她的背已经驼了,走路需要人搀扶。
“别怕,有我呢。”苏晴握住母亲的手,像小时候母亲牵着她那样。
那半个月,苏晴几乎住在医院。白天处理公司事务,晚上在病床前守着,给父亲擦身、翻身。顾衍承担了所有家务,每天变着花样给她做营养餐,还要辅导念念功课。
有天深夜,苏晴趴在床边睡着了,梦里回到小时候,父亲把她架在脖子上,去镇上买糖葫芦。醒来时,发现身上盖着顾衍的西装,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靠着墙睡着了,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
苏晴轻轻给他盖上毯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年轻时总觉得爱情是轰轰烈烈的告白,是昂贵的礼物,现在才明白,是他在你累的时候,默默递上一杯温水;是他在你撑不住的时候,说“我来”。
父亲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葬礼那天,下着小雨,王梅带着村民们来了,林晓也从外地赶回来,站在队伍里,手里捧着一束白菊。
母亲握着苏晴的手,没有哭,只是说:“你爸这辈子,就盼着你平安。现在他看见了,该放心了。”
苏晴想起父亲临终前,意识模糊时还念叨着“晴晴的公司……要好好做……”,突然明白,所谓传承,从来不是血脉的延续,而是精神的接力——父亲把“踏实做事”的道理传给她,她把“永不言弃”的信念传给念念,就像院子里的玫瑰,老根发新芽,年年岁岁,芬芳不息。
父亲走后,苏晴把母亲接到身边住。老太太闲不住,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菜地,种上了辣椒、茄子,说要给念念做她最爱吃的茄盒。
有天傍晚,苏晴下班回家,看到母亲和顾衍蹲在菜地里,研究怎么给茄子搭架子。母亲说:“得用竹竿,结实。”顾衍说:“用不锈钢管吧,能用好几年。”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像两个孩子。
苏晴站在门口,看着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突然觉得,幸福就是这样具体的画面——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而是有人陪你争“竹竿好还是钢管好”,有人等你回家吃一碗热乎的茄盒。
五十岁生日那天,苏晴收到了两份特别的礼物。
一份来自公司的年轻团队,是一本手账,里面贴满了员工们的便签:“苏总说‘错误是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帮我度过了最难的项目”“记得那次加班到凌晨,苏总给我们煮了姜汤”“谢谢苏总让我知道,女性可以既温柔又强大”。
另一份来自念念,是一个亲手缝制的布偶,穿着小小的西装,胸前别着一朵布做的玫瑰。“这是妈妈。”念念笑着说,“我学了半年缝纫才做好的。”
苏晴把布偶放在床头,看着它,突然想起自己锁骨处的玫瑰纹身,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但她知道,它一直都在,像刻在年轮里的印记,记录着所有的风雨和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