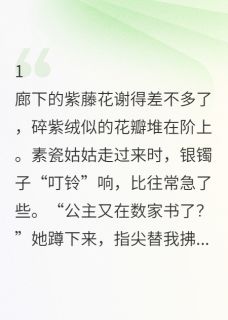
1廊下的紫藤花谢得差不多了,碎紫绒似的花瓣堆在阶上。素瓷姑姑走过来时,
银镯子“叮铃”响,比往常急了些。“公主又在数家书了?”她蹲下来,
指尖替我拂去锦书上的花瓣。我才发现,她袖口的茉莉香里混着点铁锈味,像刚摸过刀。
我把七封锦书在青石板上排开,最末那封的火漆印已经裂了细纹:“姑姑,
母亲说三月初带北漠雪莲回来,今天都六月了。”素瓷的膝盖突然砸在冰凉的地砖上,
裙摆扫过我的手背,寒得我一缩。“公主,”她声音发颤,银镯子抵着地砖响,
“独孤贵妃在殿外求见。”独孤岚进来时,满室宫花都像失了颜色。
她玄色劲装的衣摆绣着银线鹰纹,手里攥着柄木剑,扔给我时,
剑柄的薄茧蹭过我的掌心:“今日教‘挽月式’,学会了有奖。
”我抓着剑柄的手顿了顿——她的指尖还沾着雪霜气,像是刚从宫外回来。“什么奖?
”她突然俯身,温热的气息扫过我耳畔,混着剑鞘的冷香:“比如,告诉你,
你母亲真正去了哪里。”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得家书翻卷,最后那封“北漠雪莲”的信,
正好落在她脚边。父皇带我去水榭那日,柳絮飘得像场碎雪,沾在我月白裙角上,
拍都拍不掉。他坐在临水的栏杆边,手里白玉酒杯盛着琥珀色的酒,
声音里裹着我听不懂的疲惫:“明玥看,李才人新学的胡旋舞,好不好?
”水榭下的舞姬穿着粉白舞衣,旋转时像朵炸开的花。我盯着水面倒影里晃动的影子,
突然问:“父皇,母亲也会穿这么多颜色的衣服吗?”“咚”的一声,他的酒杯撞在栏杆上,
酒洒出来,溅在我手背上,凉得刺骨。“你母亲只爱穿月白。”他说这话时,目光飘向北方,
那里是北漠的方向。当晚我偷溜进父皇的书房。书架第三层有块活动的木板,
我踮着脚推开——藏在里面的画还在。画中少女站在长坡上,月白裙角被风掀起,
腰间悬着的玉佩,竟和独孤岚的那块,连凤凰尾纹的弧度都分毫不差。我指尖碰了碰画轴,
宣纸上落着层薄灰,像是很久没人动过,又像是……总有人偷偷来看。
素瓷姑姑按住我翻箱倒柜的手时,我正扒着母亲的妆奁找另一块暖玉。她袖口的茉莉香里,
血腥味更重了。我抓着她的手腕,摸到她袖口藏着的短刀,
刀鞘上还沾着暗红的血渍:“你流血了?”她猛地甩开我,力道大得我撞在妆奁上,
鎏金镜“哐当”倒在地上。“公主不要再查了。”她声音发颤,银镯子在镜面上划出道痕,
“当年若不是皇后执意要去边关……”“皇后?”我刚要追问,殿外传来脚步声,轻得像猫。
独孤岚倚着门框笑,玄色衣摆扫过门槛,
腰间玉佩在烛火下闪着冷光:“素瓷姑姑这是在给公主讲睡前故事?”她走进来,
靴尖踢到我掉在地上的家书,“正好,我也有个故事——三个月前,有人在边关长坡,
发现了具穿月白裙的尸骨。”素瓷突然站起来,挡在我身前,
我看见她手背上的青筋都绷起来了。烛火晃了晃,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道护着我的墙。
父皇再带我去长坡时,秋草已经没过我的膝盖。风卷着草叶打在脸上,疼得像小虫子咬。
他站在坡顶,望着北漠的方向,背影佝偻得像株枯槐。龙袍月白的底色上,
绣线都有些发旧了——我记起来,这是母亲当年亲手为他绣的。“明玥,
知道为什么总带你来这吗?”他声音哑得像砂纸磨木头,
我攥着袖中那半块从画轴里掉出的玉佩碎片,没敢说话。那碎片边缘很锋利,
硌得我掌心发疼。“你母亲当年就是从这里出发去的边关。”他转身时,我看见他眼角的泪,
混着风里的草屑,“她说要去查军粮贪腐案,带了三个侍卫,
走的时候……还摘了朵坡上的小蓝花,说要给你做书签。
”我终于忍不住问出口:“那独孤贵妃的玉佩,怎么回事?”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咳得弯下腰,指缝里渗出血,滴在月白的龙袍上,像开了朵红梅。“因为……”他喘着气,
声音轻得快被风吹走,“她是你母亲的孪生妹妹啊。”袖中的玉佩碎片突然发烫,
我抬头望向北漠的天,那里的云压得很低,像要落雨。2独孤岚被押进天牢那日,
我偷拿了素瓷姑姑的腰牌,顺着石阶往下走。天牢里的霉味混着血腥味,呛得我直咳嗽。
她卸了钗环,素面朝天坐在草堆上,头发用根麻绳束着。我隔着铁栏看她,
突然发现她眼角的泪痣,和画中母亲的位置一模一样——只是母亲的泪痣是淡褐色,
她的是墨黑。“想知道真相吗?”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从怀里摸出个锦囊,
隔着铁栏递过来,“你母亲没死,当年是我替她死的。”我打开锦囊,
里面的半块玉佩掉在掌心——边缘的弧度,正好和我袖中那半块拼合。
完整的凤凰形状在昏暗的光里,泛着温吞的光。“皇后发现皇弟(当今摄政王)私通敌国,
被他推下悬崖。”她突然笑起来,笑声在天牢里撞得发响,“我换了她的衣服引开追兵,
她现在在北漠养伤。”我攥着拼合的玉佩,指尖都在抖。她又说:“而你父皇,
早就知道这一切。”风从牢窗灌进来,吹得她的头发飘起来,我突然觉得,她的眼神里,
藏着和母亲一样的疲惫。我站在长坡上时,风卷着我的月白裙角,像母亲画里的样子。
素瓷姑姑捧着明黄色的圣旨跪在我身后,银镯子抵着圣旨,发出细碎的响:“公主,
陛下传位给您的诏书……”远处传来马蹄声,嗒嗒地踩在草叶上。我回头,
看见个穿月白骑装的女子勒马停在坡下,
腰间的玉佩在阳光下亮得刺眼——和我手里的凤凰佩一模一样。“明玥。”她开口,
声音清润得像家书里描述的那样,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可突然,
独孤岚在天牢里的话钻进耳朵:“小心你父皇,他留着你,只是为了引你母亲回来。
”我后背一僵,转头就看见父皇带着禁军站在坡顶。他龙袍的下摆扫过草叶,
手里的剑**半截,寒光刺得我眼睛疼。母亲朝我伸出手,我刚要跑过去,
却看见她袖口露出的刺青——墨色的鹰图腾,和摄政王密信上的那个,
连鹰爪的纹路都分毫不差。风突然停了,草叶上的露珠“嗒”地坠在地上,
像谁在暗处落下的棋子。那鹰图腾像淬了毒的针,扎得我眼仁发疼。“明玥,过来。
”母亲的手僵在半空,月白骑装下的肩膀微微颤抖,可她的指尖,
却没有我记忆里的薄茧——母亲当年教我握笔时,指尖总带着磨出来的茧子。
坡顶传来父皇的冷笑,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散:“沈清辞,你果然舍得回来。”我猛地回头,
看见禁军的刀光在日头下晃,素瓷姑姑不知何时挡在我身前,银镯子叮当作响,
像在护着什么:“陛下,公主是无辜的。”“无辜?”母亲突然笑了,那笑声尖细,
和独孤岚竟有几分像,“当年若不是她哭着要北漠的糖葫芦,我怎会在边关多停留半日?
”我的指甲掐进掌心,疼得发麻。母亲的家书里分明写着,
是军中急报让她耽搁了行程——她从来不会提“糖葫芦”,我七岁生辰时,
她还说过“公主不该嗜甜”。“皇嫂这是在怪明玥?”摄政王楚昭彦的声音从斜后方传来,
他玄色蟒袍上的金线鹰图腾,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还是在怪陛下当年默许我把你推下悬崖?
”父皇突然拔剑指向他,剑尖抖得厉害:“朕没默许!”他的喉结动了动,
“朕只是……只是没想到你真敢动手!”母亲翻身下马,腰间玉佩撞上马鞍,发出清脆的响。
她一步步走上坡,月白裙角扫过带露的野草:“楚昭帝,你以为把明玥养在深宫,
我就会束手就擒?”“束手就擒?”我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手里的凤凰佩烫得像火,
“你根本不是我母亲!”所有人都静了。风卷着草叶打在脸上,疼得像又挨了一巴掌。
母亲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你怎么会……”“因为她知道那半块玉佩里的字。
”天牢方向传来锁链拖地的声响,独孤岚被两个禁军押着上来,脖颈间还带着刑具的红痕,
“姐姐,你总说我不如你懂陛下,可你连他在玉佩里刻‘护明’二字都不知道。
”我赶紧摸袖中的玉佩,指尖蹭过碎片背面——果然有模糊的“护”字,
是昨夜素瓷姑姑塞给我的,她说“公主带着,能保命”。“皇后私通敌国,罪证确凿!
”摄政王突然高喊,声音震得草叶晃,“来人,拿下叛党!”禁军的脚步声从四面八方涌来。
素瓷姑姑把我往母亲身后一推,银簪从发髻上拔下来,尖端正对着靠近的士兵:“公主快走,
去北漠找苏将军!”她冲上去时,我看见她袖口的茉莉香混着血雾散开,银镯子掉在地上,
滚到我脚边。3风在耳边呼啸,母亲拽着我的手腕往密林里钻。她的手劲极大,
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掌心的温度烫得吓人——和独孤岚当年教我握剑时的温度,一模一样。
“放开我!”我挣扎着,袖中的凤凰佩硌得胸口发疼,“你到底是谁?”她猛地停步,
转身时眼里闪着诡异的光,像淬了毒的蛇:“明玥,连母亲都不认了?”“我母亲的家书里,
从不会提糖葫芦这种琐碎事!”我甩开她的手,后退半步,鞋底踩在枯枝上,
“咔嚓”一声响,“你是故意说错的,对不对?”她突然笑出声,笑声在林间荡开,
惊起一片飞鸟。羽毛落在我肩头,带着点凉意:“不愧是楚昭的女儿,够聪明。
”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枯枝被踩得噼啪响。我回头,
看见独孤岚追了上来——她玄色衣袍上沾着血迹,左臂缠着布条,
渗出来的血把布条染成了黑红色,手里还提着把带血的剑。“沈清婉,别装了!”她喘着气,
剑尖指向那女人。“沈清婉?”我愣住了,这个名字,我从来没听过。
那女人脸上的温柔瞬间崩塌,恶狠狠地盯着独孤岚:“你怎么逃出来的?
天牢的守卫……”“拜陛下所赐。”独孤岚把一把匕首塞到我手里,刀柄上还带着她的体温,
“他终究还是不忍心看着你母亲的亲妹妹,被你这个冒牌货骗得团团转。
”我握着匕首的手微微颤抖,冰凉的金属贴着掌心。“那我母亲呢?”我盯着沈清婉,
“她到底在哪里?”沈清婉突然从怀里掏出封信,扔到我面前的泥地上。
信纸被风吹得卷起来,我赶紧蹲下去捡,指尖沾了泥:“自己看!这是你母亲亲笔写的,
她早就和北漠王勾结,要打败大楚!”我展开信纸,
上面的字迹确实和家书上的一模一样——连母亲写“玥”字时,竖钩总带点弯的习惯,
都分毫不差。可当我看到信末的日期时,心猛地一沉——那日期,正是母亲说要回来的日子。
“不可能!”我摇着头,眼泪滴在信纸上,晕开了墨迹,“我母亲不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你去问北漠王就知道了。”沈清婉说着,突然从腰间抽出一把短刀,
刀光在林间闪了下,直朝我胸口刺来。独孤岚眼疾手快,一把将我推开。
短刀划在她的胳膊上,布条瞬间被血浸透。“快走!”她对我喊,声音里带着急,“去北漠,
找到苏将军,他会告诉你一切!”我看着她和沈清婉打在一起,刀光剑影里,
突然听见素瓷姑姑的声音——很轻,像是从远处飘来。“……一定要保护好公主,
不能让她落入摄政王手里……”我循着声音找过去,拨开灌木丛,看见素瓷姑姑倒在地上。
她胸口插着一支羽箭,箭羽还在颤,嘴角溢着血。她的手紧紧攥着块令牌,
上面刻着个“苏”字,令牌边缘被她的血浸得发红。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蹲下去捡令牌,
指尖碰着她的手——已经凉了。身后传来沈清婉的惨叫声,我不知道独孤岚有没有打赢,
只知道必须跑。脚下突然一软,我掉进了个深不见底的陷阱。下落时,我看见头顶的树叶间,
有个穿月白裙的影子一闪而过,像母亲,又不像。黑暗像潮水般将我淹没,
坠落的惯性让我撞在松软的落叶堆上,脚踝传来一阵剧痛,像是骨头裂了。
“咳咳……”我呛了几口土,伸手摸向腰间——匕首还在,苏字令牌也在,
只是凤凰佩的碎片好像又裂了道缝。就在这时,黑暗中亮起一点微光,橘黄色的,
像远处的星。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带着点沙哑:“是谁掉进老身的陷阱里了?
”我警惕地缩了缩脚,握紧匕首:“你是谁?”微光渐渐靠近,
我才看清是个穿粗布衣裳的老婆婆。她手里提着盏油灯,灯芯跳着小火花,
脸上的皱纹堆在一起,像老树皮。“小姑娘,别怕。”她笑了笑,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
“我是这附近的猎户,这陷阱是用来捕野猪的。”“猎户?
”我盯着她的手——那双手很粗糙,指关节很大,却没有猎户该有的厚茧,“这荒山野岭的,
怎么会有猎户?”老婆婆叹了口气,油灯的光晃在她脸上:“唉,世道不太平,
城里待不下去,只能躲到山里讨口饭吃。看你的穿着,是宫里来的吧?怎么会跑到这里?
”我犹豫了一下,把匕首藏到袖中:“我……我迷路了。”她没再追问,
只是把油灯放在陷阱边的石头上,扔下来一根粗绳:“这陷阱深,我拉你上来。
你的脚踝好像伤了,前面有间小屋,去歇歇吧。”我抓住绳子,忍着脚踝的疼往上爬。
她的力气很大,拉着我毫不费力,不像个普通老人。到了小屋,她给我倒了碗热水。
水汽氤氲着,我却看见水里飘着点淡绿色的粉末——像极了素瓷姑姑说过的“迷魂散”。
我假装喝水,趁她转身收拾东西,悄悄把水泼在了灶台下的灰里。她坐回来,
开始东拉西扯问我话:“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人?”我敷衍着,
目光却落在她腰间——那里挂着块玉佩,形状竟和我手里的凤凰佩一模一样!我猛地站起来,
指着她的腰:“你这玉佩是哪里来的?”老婆婆脸色一变,
下意识地捂住玉佩:“你……你问这个干什么?”“这玉佩对我很重要!”我往前走了一步,
脚踝的疼让我晃了晃,“你快告诉我!”她沉默了片刻,突然叹了口气,
从怀里掏出封信:“罢了,既然你看到了,我也不瞒你。这玉佩是苏将军托我保管的,他说,
要是遇到个拿着半块凤凰佩的小姑娘,就把这个交给她,再把这封信给你。”我接过信,
指尖碰着信纸——是北漠特有的桑皮纸,和母亲家书的纸一样。信上的字迹苍劲有力,
写着:“明玥公主亲启,吾奉皇后之命,在此等候。速随婆婆来北漠王庭附近的破庙,
吾将告知一切真相。苏凛字。”“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我抬头问,心里又惊又喜。
“天亮就走,晚上不安全。”老婆婆把玉佩解下来,递给我——这是第三块碎片,
背面刻着个“玥”字。当晚我睡在小屋的角落,油灯灭了,黑暗里,
我摸着三块拼合的凤凰佩,突然想起母亲的话:“明玥,暖玉能护人,就像母亲在你身边。
”天刚蒙蒙亮,我就跟着老婆婆往山林外走。她走得很快,脚程比我这个没受伤的人还快,
粗布衣裳的下摆扫过草叶,没沾一点露水。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前方突然传来马蹄声。
老婆婆脸色一变,把我往树后一推:“躲好!是摄政王的人!”我刚藏好,
就看见一群黑衣人骑着马过来,为首的人身穿玄甲,腰间挂着摄政王的令牌。
他们在不远处停下,为首的人勒住马:“仔细搜!公主肯定在这附近!
”老婆婆突然将我往东边推:“快跑!往东边的破庙走,苏将军在那等你!”她说着,
从腰间抽出把短刀,迎了上去,“老身来会会你们!”短刀在晨光里划出冷弧,
她的动作快得不像个老人,一刀就划中了为首黑衣人的胳膊。我咬着牙,
忍着脚踝的疼往东边跑,身后传来兵器碰撞的脆响和惨叫声。跑了约莫一炷香的时间,
身后的声响渐渐消失。我扶着棵老槐树喘气,刚想歇会儿,
却见一个黑衣人从树后绕出来——他胳膊上缠着绷带,正是刚才被老婆婆划伤的人。
“公主殿下,别躲了。”他声音嘶哑,手里的剑指着我,“摄政王有令,要活的。
”我握紧独孤岚给的匕首,后背抵着树干:“你们是摄政王的人?”“是又如何?
”他步步逼近,剑刃的寒光落在我脸上,“皇后通敌,你这公主本就不该存在。
”就在他的剑要刺到我胸口时,一支羽箭突然破空而来,“咻”地钉在他的手腕上。
黑衣人痛呼一声,剑掉在了地上。“谁?”他惊恐地环顾四周。
一个穿着玄甲的青年从林中走出来,手里还握着弓。他腰间挂着的令牌,
和素瓷姑姑手里的“苏”字令牌一模一样:“苏某在此,谁敢动公主?”“苏将军!
”我又惊又喜,差点哭出来。苏凛收起弓,对我拱手:“公主受惊了。老婆婆让我在此接应,
她……”他顿了顿,眼神暗了暗,“她为了引开其他黑衣人,恐怕已经遇难了。
”我心里一沉,说不出话来。老婆婆腰间的玉佩还在我手里,温热的,像她的体温。
苏凛突然从怀里掏出个锦盒:“公主,这是皇后娘娘留给你的。”我打开锦盒,
里面是半块凤凰佩——正好能和我手里的三块拼合成完整的凤凰形状。玉佩下面压着张字条,
是母亲的字迹:“明玥,母并非通敌,实乃发现摄政王与北漠太子勾结,欲夺你父皇江山。
母假意顺从,实为收集证据。若母未能回来,找苏凛,他会助你揭露真相。
”“那父皇知道吗?”我抬头问,指尖还捏着字条。苏凛摇头:“陛下被摄政王蒙蔽,
还以为皇后真的叛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马蹄声,越来越近。苏凛脸色一变:“不好,
是摄政王的人追来了!公主,我带你从密道走,去北漠找皇后娘娘!
”我跟着他往密林深处跑,脚踝的疼越来越厉害。跑着跑着,
突然看见前面有个熟悉的身影——是独孤岚!她身上的伤口还在流血,
玄色衣袍被扯破了好几处,看到我们,她大喊:“别信苏凛!他才是叛徒!”苏凛脸色骤变,
突然拔出剑指向我:“公主,别怪我,我也是身不由己。”我愣住了,看着他剑上的寒光,
又看着跑来的独孤岚,手里的凤凰佩突然烫得厉害。4苏凛的剑刃离我只有三尺远,
我能看见他瞳孔里我的影子——渺小又慌乱。我下意识后退半步,后腰撞到凸起的树根,
疼得倒抽口气。“为什么?”我盯着他腰间的苏字令牌,那曾是我在陷阱里唯一的希望,
“母亲的字条上说,你会帮我。”他嘴角抽搐着,剑却又往前递了半寸:“那字条是仿的!
”他的声音有些发颤,“皇后当年查到的军粮贪腐案,我父亲也牵涉其中,
是皇后亲手判了他死刑!”“你说谎!”我攥紧手中的凤凰佩,
完整的凤凰在阳光下泛着绿光,“这玉佩能验毒,你刚才给我的水囊——”我话没说完,
苏凛突然转身想跑。可独孤岚的剑更快,“噗嗤”一声刺穿了他的肩膀。
鲜血溅在我月白裙角上,像朵绽开的红梅。“说!我姐姐到底在哪?
”独孤岚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剑刃又往里送了半分。苏凛痛得蜷缩在地,
北漠王庭的地牢里……摄政王用她的性命要挟北漠太子……要军防图……”“你怎么不早说!
”我踢开他掉在地上的剑,心里又急又恨。“公主快走!
”独孤岚突然将我往旁边的密道入口推,“这是去北漠王庭的近路,我引开追兵!拿着这个!
”她塞给我一块虎符,上面刻着北漠的狼图腾,“北漠铁骑只认这个,能保你安全。
”我钻进密道时,听见她高声喊:“苏凛在此,快来人啊!”声音越来越远,
混着兵器的碰撞声。密道里伸手不见五指,我摸着潮湿的墙壁往前走,
凤凰佩的绿光成了唯一的光源。墙壁上沾着些青苔,滑溜溜的,像某种动物的皮肤。
走了约莫半个时辰,前方突然传来滴水声,还有人说话的声音——是摄政王的声音!
“……皇后还没松口?”他的声音带着不耐烦。“回王爷,她骨头硬得很,
怎么打都不说军防图在哪。”另一个声音陌生又熟悉,像极了宫里的李才人。我屏住呼吸,
慢慢往前挪,从石壁的缝隙里看出去——摄政王正坐在石桌旁喝茶,
手里的茶杯是父皇赏的白玉杯。而站在他对面的,果然是李才人!她穿着粉色宫装,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等拿到楚明玥,就不信她不交出军防图。”摄政王冷笑,
手指敲着石桌,“那丫头手里的凤凰佩,可是开启国库的钥匙,也是护国军的兵符。
”李才人突然笑了,声音尖细:“王爷别忘了答应我的事,等事成之后,我要做皇后。
”我捂住嘴才没叫出声来,后腰的凤凰佩突然灼热难忍,像是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钻出来。
就在这时,密道的另一头传来脚步声,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明玥,是你吗?”是母亲!
我激动地想冲出去,却被李才人接下来的话钉在原地。
“皇后的声音倒是越来越像当年的沈清婉了,若不是王爷提醒,
臣妾差点以为……”母亲的声音突然变得冰冷,像淬了冰:“楚昭彦,
你以为用假声带就能骗得过我?”石壁外传来兵器交锋的声响,我握紧虎符,
突然明白——原来这三年来,一直和我通信的“母亲”,根本不是她本人。
石壁外的兵器碰撞声越来越急,“叮叮当当”的,像砸在我心上。我死死攥着虎符,
指节泛白,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那熟悉的“母亲”声音突然拔高,
带着破风般的锐响:“楚昭彦,你以为割了我的声带,就能让沈清婉顶替我一辈子?
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和北漠太子的那些勾当?
”摄政王的怒喝混着金器碎裂的脆响:“闭嘴!若不是你当年撞破我和北漠太子的密谈,
何至于此!若不是你非要查军粮案,我怎会对你动手!”我贴着石壁滑坐到地上,
后腰的凤凰佩烫得像团火。
那些家书里的温柔笔触、北漠雪莲的承诺、“母亲”说要给我做蓝花书签的话,
原来全是假的。是谁模仿了母亲的笔迹?是沈清婉,还是……“王爷小心!
”李才人的惊叫声刺破空气。紧接着是重物倒地的闷响,随后传来独孤岚的声音,
带着喘息的沙哑:“姐姐,我来晚了!”我心头一颤,
扒着石壁缝隙往外看——那个曾被我唤作“母亲”的人,正拄着剑半跪在地上,
脖颈处缠着渗血的白布,布料上还沾着些发黑的血渍。独孤岚正用剑格挡李才人的攻击,
玄色衣袍的袖子被划破了,露出里面的绷带。摄政王倒在石桌旁,
胸口插着半块玉佩——竟是沈清婉之前持有的那半块!“是你!”李才人被逼得连连后退,
指着突然站起的“母亲”,脸色惨白,“你根本不是皇后!你是沈清婉!”“眼力不错。
”那人扯掉脖颈间的白布,露出一道狰狞的疤痕,从下巴一直延伸到锁骨,“我是沈清婉,
被你们扔进悬崖还没死的沈清婉!”独孤岚的剑顿了顿,
眼里满是震惊:“你……你不是被我亲手推下悬崖的吗?
当年我明明看到你……”“看到我掉下去,却没看到我被北漠牧民救了。”沈清婉突然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