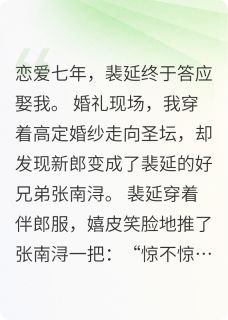
恋爱七年,裴延终于答应娶我。婚礼现场,我穿着高定婚纱走向圣坛,
却发现新郎变成了裴延的好兄弟张南浔。裴延穿着伴郎服,
嬉皮笑脸地推了张南浔一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我面不改色地接过张南浔颤抖递来的戒指,直接套上无名指。婚后裴延却疯了,
他冲进我的新家,跪在昂贵的手工地毯上痛哭流涕。“我只是想开个玩笑,
逼你当众说只爱我!”我晃着红酒杯,俯视他狼狈的模样:“张太太现在很满意她的丈夫。
”“尤其是他名下,刚转给我的那百分之十五集团股份。
”---聚光灯像一道滚烫的熔金,毫不留情地浇在我身上。
空气里弥漫着铃兰的甜香和昂贵香槟的清冽气泡,混合成一种近乎奢侈的晕眩感。
脚下这条长长的、铺着厚厚象牙白地毯的通道,似乎没有尽头,
尽头处那个挺拔的、穿着黑色礼服的身影,
是我用七年青春、无数个妥协与等待换来的终点——裴延。七年。这个词在我舌尖滚过,
带着一点铁锈般的苦涩,更多的却是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和……终于要赢了的麻木。
镶满碎钻的曳地裙摆扫过地毯,发出细微的沙沙声。每一步,都踩在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上。
我甚至能感觉到脸上肌肉因为维持得体的微笑而微微发僵。宾客席里投来无数目光,
艳羡的、祝福的、探究的。我挺直脊背,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演员,走向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走向那个承诺给我未来的男人。距离圣坛越来越近。裴延侧身的轮廓在强光下有些模糊。
他旁边站着的伴郎,是他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张南浔。张南浔似乎比平时站得更直,
像一根绷紧的弦。我的心跳莫名漏跳了一拍,一丝极其微弱的不安,像投入深海的石子,
还没来得及激起涟漪,就被我强行按了下去。胡思乱想什么。我暗自吸了口气,调整步伐,
终于,稳稳地站在了圣坛前,站在了……我未来的丈夫面前。我抬起头,
嘴角扬起的弧度完美无瑕,目光精准地投向裴延。然后,世界在我眼前裂开了一道缝。
站在圣坛中央,穿着和我婚纱配套的新郎礼服的,不是裴延。是张南浔。
那个总是沉默地跟在裴延身边,戴着金丝边眼镜,气质清冷疏离的张南浔。此刻,
他穿着剪裁完美的黑色礼服,胸口的白色玫瑰娇艳欲滴,那张一向没什么表情的脸,
在强光下显得异常苍白,嘴唇抿成一条僵硬的直线。金丝眼镜后的眼神,
是纯粹的惊愕和无措,甚至带着一丝来不及掩饰的狼狈。他像一尊被强行推上展台的石膏像,
手脚都不知该往哪里放。
而我那恋爱七年、刚刚在休息室还深情款款说“终于等到今天”的准新郎裴延,
正穿着笔挺的伴郎服,站在张南浔旁边。时间凝固了。宾客席里死一般的寂静,针落可闻。
连背景里那舒缓的婚礼进行曲,都仿佛卡了带,变成一阵阵尖锐的耳鸣,
刺得我太阳穴突突直跳。裴延咧开嘴,露出一口白得晃眼的牙齿。他伸出手,
极其随意地、带着一种恶作剧得逞般的兴奋,用力推了张南浔的肩膀一把。“哈!
”裴延的声音在死寂的大厅里炸开,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欢快,“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他甚至还夸张地张开手臂,环顾了一下四周鸦雀无声的宾客,
仿佛在期待一场雷鸣般的掌声和爆笑。“怎么样,哥们儿我这创意绝不绝?
七年长跑终成眷属,临门一脚换个新郎!**不**?哈哈哈!”张南浔被他推得一个趔趄,
眼镜都滑到了鼻梁中间。他手忙脚乱地扶住眼镜,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着,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看向我,那眼神复杂得如同打翻的调色盘——有极致的尴尬,
有被当众羞辱的难堪,有对我反应的巨大恐惧,
甚至……还有一丝极其微弱的、连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的恳求?
裴延的笑声还在空旷的穹顶下回荡,像砂纸一样摩擦着我的神经末梢。惊喜?意外?**?
七年。我看着他脸上那毫不掩饰的、等着看我崩溃或暴怒的期待表情,
看着张南浔僵直的身体和苍白的脸,看着台下无数张惊愕、茫然、看好戏的脸孔。
一股冰冷的气流从脚底瞬间窜遍全身,奇异地浇熄了所有翻腾的怒火和屈辱。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死寂的平静。七年,原来在他眼里,
不过是一场可以随时拿来开涮、博人眼球的廉价表演。我脸上那点僵硬的、职业性的笑意,
在裴延刺耳的笑声中,一点点、一点点地加深了。嘴角上扬的弧度变得异常清晰,
甚至带上了一丝冰冷的、玩味的意味。司仪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手,此刻也完全懵了,
拿着麦克风的手僵在半空,活像一座造型滑稽的雕塑。我直接忽略了他。我的目光,
平静无波地,落在了张南浔脸上。他猛地一震,像是被我的视线烫到,
扶眼镜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站在圣坛旁,穿着庄重牧师袍的老先生,此刻也完全懵了。
他花白的眉毛纠结在一起,看看穿着新郎礼服的张南浔,
又看看旁边笑得像个二流子似的伴郎裴延,最后,
求助般地将目光投向了我——这个穿着婚纱、本该是唯一女主角的新娘。老先生清了清嗓子,
试图找回一点职业的威严,
但声音明显带着抖:“呃……这位先生……”他犹豫地看向张南浔,
“还有这位……新娘……”他又转向我,眼神里充满了“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的困惑。
裴延的笑声终于歇了,他抱着手臂,好整以暇地看着牧师,又看看我,
眼神里充满了那种等着看戏的、令人作呕的兴奋。他似乎笃定了我会尖叫,会崩溃,
会哭着质问他,然后他就可以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以一种“开个玩笑而已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的姿态,重新走上来,完成这场他主导的闹剧。
牧师深吸一口气,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按流程走下去,哪怕这流程诡异得像恐怖片。
他转向张南浔,语气带着十二万分的试探和不确定:“张南浔先生,
你是否愿意娶苏晚女士为妻,按照圣经的教训与她同住,在神面前和她结为一体,
爱她、安慰她、尊重她、保护她,像你爱自己一样。不论她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贫穷,
始终忠于她,直到离开世界?”“我……”张南浔张了张嘴,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摩擦。
他下意识地又想去扶眼镜,目光飞快地扫过我平静得过分的脸,
又扫过旁边裴延那张看好戏的脸,最后定格在牧师脸上,眼神里是巨大的混乱和挣扎。
那句“我愿意”像是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怎么也吐不出来。额角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在聚光灯下闪着微光。牧师的眼神更绝望了。裴延脸上的笑容更深了,
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得意,他甚至用手肘轻轻捅了捅张南浔僵硬的胳膊,压低声音,
用那种自以为幽默的语调催促:“嘿,兄弟,台词!说啊!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尴尬和裴延自以为是的催促达到顶峰时,我动了。没有崩溃,没有质问,
甚至没有再看裴延一眼。我微微侧过身,面向张南浔。
镶满碎钻的裙摆随着我的动作划出一道冰冷的弧光。我的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穿透了这片死寂,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直接盖过了牧师的结巴和裴延的聒噪。
“戒指呢?”我朝他伸出手。那只手,白皙、稳定,没有一丝颤抖。整个婚礼现场,
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连背景音乐都彻底消失了,只剩下空调系统沉闷的嗡嗡声。
张南浔猛地抬起头,金丝眼镜后的瞳孔骤然收缩,像是被强光刺到。
他死死地盯着我伸出的手,仿佛那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凶器。几秒钟的石化之后,
他像是被无形的线扯动,手忙脚乱地开始在口袋里摸索。昂贵的西装口袋被他翻得一团糟,
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带着一种近乎滑稽的笨拙。终于,
他从裤袋深处掏出一个深蓝色的丝绒小盒子。他打开盒子的动作带着一种豁出去的笨重。
盒子里,一枚璀璨夺目的钻戒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裴延家祖传的鸽子蛋,今天早上,
裴延还亲手把它交给伴郎张南浔保管,戏谑地说“替我拿好我的下半辈子”。
戒指的光芒折射在张南浔苍白的脸上,映出他额角细密的汗珠和微微颤抖的下颌线。
他捏起那枚沉甸甸的戒指,指尖冰凉。他迟疑地、极其缓慢地伸出手,试图托起我的左手。
他的手指带着明显的凉意和无法抑制的轻颤,触碰到我的指尖时,
像被微弱电流击中般猛地一缩。“我……”他试图开口,声音却破碎不堪。“我自己来。
”我截断了他所有可能的犹豫和退缩,声音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湖面。
在他惊愕的目光和裴延骤然凝固的笑容中,我极其自然地、甚至是带着点优雅地,
用右手拇指和食指,轻轻拈起了他指尖那枚冰凉的戒指。钻石的棱角硌着我的指腹,
冰冷坚硬。然后,在全场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
在裴延那副“老子等着看你哭”的表情彻底僵化、碎裂的瞬间,我没有任何犹豫,
没有任何停顿,稳稳地、决绝地将那枚象征着裴家传承和裴延“下半辈子”的硕大钻戒,
推进了自己左手的无名指根部。金属的冰凉感瞬间缠绕住指根,
带着一种奇异的、沉甸甸的踏实。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甚至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优雅,
仿佛只是在试戴一件普通的首饰。戒指完美契合,尺寸精准得像是为我量身定做——毕竟,
裴延的指围,和张南浔几乎一样。做完这一切,我抬起手,对着头顶炫目的聚光灯,
欣赏了一下无名指上那过分璀璨的光芒。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在疯狂反射着光,
刺得人眼睛发疼。然后,我才慢悠悠地转向旁边彻底石化的牧师,
脸上甚至带上了一丝恰到好处的、仿佛刚从某个小插曲中回过神来的微笑。“牧师先生,
”我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大厅里,“该我的词了。”老牧师像是被雷劈中,
猛地一哆嗦,手里的圣经差点掉在地上。他慌忙翻开书页,手指颤抖地划过一行行烫金的字,
嘴唇哆嗦着,
南浔失魂落魄的惨白、以及裴延那副仿佛被施了定身咒、笑容彻底碎裂扭曲的脸上来回扫视。
“苏……苏晚女士……”牧师的声音像是破旧的风箱,嘶哑得不成样子,
“你是否愿意嫁给张南浔先生为妻,按照圣经的教训与他同住,在神面前和他结为一体,
爱他、安慰他、尊重他、保护他,像你爱自己一样。不论他生病或是健康、富有或贫穷,
始终忠于他,直到离开世界?”几百道目光,像几百根烧红的针,密密麻麻地扎在我身上。
空气粘稠得如同凝固的沥青。我缓缓地、极其清晰地开口,目光没有看向身边的张南浔,
也没有瞥向一旁雕塑般僵硬的裴延,而是平静地越过牧师花白的头顶,
投向远处穹顶下巨大的水晶吊灯。那璀璨的光芒,像无数冰冷的眼睛。
“我——”裴延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他像是从一场荒诞的噩梦中惊醒,
瞳孔骤然放大,里面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骇和一种被彻底愚弄的暴怒。他猛地向前冲了一步,
嘴唇哆嗦着,似乎想要咆哮,想要阻止这彻底失控的局面。“——愿意。
”我的声音平稳地落下,盖过了他喉咙里即将冲出的嘶吼,像一块冰冷的巨石投入死水,
激起无声的巨浪。“砰!”一声闷响,裴延像是被无形的巨锤当胸击中,
踉跄着狠狠撞在了旁边的花艺拱门上。精心布置的玫瑰和铃兰簌簌落下,
鲜红的花瓣砸在他昂贵的伴郎服肩头,又狼狈地滚落在地毯上。他死死地盯着我,
眼白瞬间爬满了猩红的血丝,那眼神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张南浔在我身边,
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我甚至能听到他细微的、倒抽冷气的声音。
在我吐出“愿意”两个字时,他的肩膀几不可察地剧烈颤抖了一下,
仿佛承受了某种巨大的冲击。牧师长长地、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那声音在麦克风的扩音下显得格外粗重,像是劫后余生。
他飞快地、几乎是抢着念完了剩下的流程,声音带着一种逃出生天的急促。
“……我宣布你们正式结为夫妻!新郎,现在你可以亲吻你的新娘了!”最后几个字,
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带着一种甩掉烫手山芋的解脱。亲吻?张南浔的身体彻底僵成了冰雕。
他猛地转向我,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充满了巨大的、无处安放的恐慌,
像一只被逼到悬崖边的鹿。他的喉结剧烈地上下滚动,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汗水沿着他鬓角滑落,在强光下亮晶晶的。裴延扶着拱门,勉强站稳,他死死地盯着张南浔,
眼神阴鸷得能滴出水来,那是一种无声的、带着血腥味的警告和威胁。
整个大厅的空气再次凝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张南浔身上,
等着看他如何应对这致命一击。时间被拉得无限长。就在张南浔的呼吸都快要停滞,
连裴延嘴角都开始勾起一丝残忍的、看好戏的弧度时——我动了。
没有给张南浔任何犹豫和崩溃的时间,我微微侧过身,正对着他。
在他惊愕放大的瞳孔注视下,我踮起脚尖——镶钻的鞋跟在地毯上压出一个小小的凹痕。
同时,我伸出手,坚定地、甚至带着点不容抗拒的力道,
捧住了他那张过分僵硬、冰冷的脸颊。然后,在几百双眼睛的注视下,
在裴延瞬间扭曲狰狞的面容前,我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
目标精准——他紧抿的、毫无血色的薄唇。触感冰凉、干燥,
带着他身体无法抑制的细微颤抖。没有任何技巧,没有任何情欲,纯粹得像一个盖章,
一个宣告。一触即分。我松开手,退后半步,重新站定。脸上依旧平静无波,
仿佛刚才那个惊世骇俗的吻,只是拂去了一片落在肩头的花瓣。“礼成。
”我对着彻底石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的牧师,轻轻吐出两个字。声音不大,
却像是一记重锤,砸碎了这场荒诞剧最后的幕布。---“砰!
”厚重的雕花实木门在身后关上,将门外那个歇斯底里的世界彻底隔绝。
裴延那变了调的、混杂着暴怒和某种崩溃的吼声,像被掐断了电源,瞬间消失。门内,
是另一个世界。巨大而空旷的玄关,挑高近六米的穹顶,
一盏冷感十足的现代艺术吊灯洒下柔和却缺乏温度的光。
空气里弥漫着新家具的皮革味、某种高级雪松香薰的清冽,以及……一丝空旷的冷寂。
脚下是触感绵密厚实的深灰色手工羊毛地毯,踩上去悄无声息,仿佛能吸走一切喧嚣。
**在冰凉的门板上,闭上眼。无名指上那枚巨大的钻戒硌着掌心,冰冷坚硬。
婚纱沉重的裙摆像铅块一样拖拽着我。
刚才在礼堂里支撑着我的那股冰冷的、近乎狂暴的平静,此刻如同退潮般迅速消散,
留下的是被抽空般的虚脱和一种迟来的、深入骨髓的寒意。身体顺着光滑的门板,
一点点滑坐下去。昂贵的蕾丝和缎面摩擦着冰冷的地板,发出细微的声响。我蜷起腿,
将脸深深埋进膝盖里。那顶价值不菲的钻石小王冠歪斜地挂在发间,冰凉地贴着额角。
太安静了。安静得能听到自己血液冲刷耳膜的声音。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有几分钟,
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直到一阵极其轻微、带着犹豫的脚步声,打破了这片死寂。
我抬起头。张南浔站在几步开外。他已经脱掉了那身荒谬的新郎礼服外套,
只穿着里面的白衬衫,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露出清晰的喉结。
金丝眼镜后的眼神复杂得难以解读,有浓重的疲惫,有未散的惊魂未定,有深切的歉意,
还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近乎无措的观察。他手里端着一杯水,
透明玻璃杯壁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喝点水?”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带着试探。他走近几步,
保持着一点距离,弯下腰,将那杯水轻轻放在我脚边的地毯上。动作很轻,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冰凉的杯壁碰到我的指尖。我没有动,只是看着他。他迟疑了一下,
没有起身,只是维持着半蹲的姿势,视线与我齐平。镜片后的目光很沉,
没有了礼堂里的惊惶,却沉淀着更深的东西。“对不起。”他开口,声音低沉而清晰,
每一个字都像斟酌过,“今天的事……我完全不知情。裴延他……”他顿了顿,
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词,“……疯了。”他的道歉很直接,没有推诿,没有辩解裴延的行为,
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他也是被推入火坑的受害者,并且为此感到抱歉。我扯了扯嘴角,
一个毫无笑意的弧度。端起那杯水,冰冷的液体滑过干涩灼痛的喉咙,带来一丝短暂的清明。
“我知道。”我的声音嘶哑得厉害,“你不是他。
”张南浔似乎因为我这句话而微微震动了一下。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站起身,
动作带着一种刻意的缓慢,似乎在给我空间。“楼上……主卧我收拾好了。
新的洗漱用品在浴室。衣帽间……右边一半是空的。”他语速不快,条理却异常清晰,
像是在交代工作,“你需要什么,直接告诉管家,或者……告诉我。
”他没有说“我们的房间”,而是清晰地划分了界限——主卧他收拾好了(给我),
衣帽间一半是空的(属于我)。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没有一丝一毫的暧昧或越界,
只有一种基于当前混乱局面下最务实的安排。我撑着门板,有些吃力地站起来。
婚纱的束缚感让人窒息。“谢谢。”我低声说,没有看他,
径直朝着他刚才示意的楼梯方向走去。高跟鞋踩在厚厚的地毯上,依旧无声无息。身后,
张南浔没有跟上来。我走到楼梯转角,停下脚步,微微侧头。他还站在原地,
玄关顶灯的光线勾勒出他挺拔却显得有些孤寂的身影。他微微垂着头,
看着地上那杯我喝过的水,镜片反着光,看不清表情。只有那只垂在身侧的手,
无意识地、用力地蜷了一下。---三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一场轰动全城的荒诞闹剧,
从茶余饭后的谈资,变成偶尔才会被提及的旧闻。张太太的生活,平静得像一汪深潭。
张南浔名下的这栋顶层复式公寓,成了我隔绝外界风暴的堡垒。
三百六十度的落地玻璃幕墙外是繁华都市流动不息的光河,
里面却是恒温恒湿、一尘不染的寂静。巨大的衣帽间被迅速填满,一半是我的当季新款,
另一半属于张南浔的昂贵西装和衬衫,界限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他履行着一个“丈夫”所能提供的最高规格的物质保障,却更像一个存在感稀薄的室友。
他通常在书房工作到深夜,脚步轻得像猫。偶尔在巨大的开放式厨房倒水遇见,
也只是点点头,问一句“还没睡?”或者“需要什么?”,
语气平淡得像在询问下属项目进度。那份婚前协议,被我们心照不宣地执行得滴水不漏。
直到那天深夜。我在影音室看完一部冗长的文艺片,出来找水喝。经过书房虚掩的门缝时,
里面透出的灯光和一种……过于安静的压抑感,让我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门没有关严。
透过那道缝隙,我看到张南浔背对着门,坐在宽大的书桌前。他没有开主灯,
只有桌上一盏老式的绿色玻璃罩台灯亮着,昏黄的光晕将他笼罩其中。
他面前摊开着一个厚重的皮质相册,指尖停留在其中一页上,久久没有移动。他微微低着头,
平时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有几缕垂落在额前,遮住了部分镜片。
台灯的光将他侧脸的线条勾勒得异常清晰,下颌绷紧,嘴唇抿成一条没有弧度的直线。
那是一种沉浸在久远时光里才会有的专注和……一种沉重的、难以言说的寂静。
空气里仿佛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我正想悄然离开,
目光却无意间扫过他指尖停留的那页。一张明显是**角度的照片。照片上的我,
穿着大学时洗得发白的蓝色连衣裙,抱着一摞厚厚的书,走在初夏的林荫道上。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我身上洒下斑驳的光点。我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侧着脸,
似乎在和旁边的人说着什么,嘴角带着一点轻松的笑意。那笑容,
是我自己都快要忘记的、属于七年前的苏晚的样子。照片的右下角,
用极细的黑色钢笔写着一个小小的日期,
以及一行更小的、几乎难以辨认的字迹:“她今天穿了蓝色。像雨后的天空。”我的心跳,
毫无预兆地漏跳了一拍。指尖按在冰凉的门框上,留下一点湿痕。就在这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