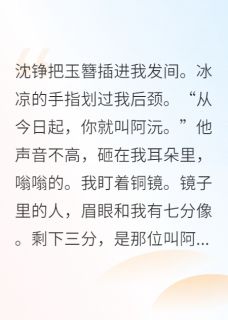
但也不再靠近我。只是偶尔。远远地看我一眼。眼神空洞。像透过我在看一个虚无的幻影。
府里的下人开始窃窃私语。看我的眼神带着怜悯和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我知道。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失宠的。连替身都做不好的可怜虫。也好。清净。我重新拿起针线。
绣些帕子荷包。托人悄悄拿到外面卖。攒点私房钱。爹娘身体还行。弟弟读书用功。
知道我在将军府“做事”。总写信来。让我多为自己打算。“姐,别太委屈自己,
等我考取了功名,接你回家。”我看着信。鼻子发酸。回家。多好的词。可我的家在哪里?
将军府这个精致的牢笼?还是那个早已物是人非的小村庄?我不知道。直到那个清晨。
剧烈的恶心感把我从睡梦中攫醒。我趴在床边。吐得天昏地暗。胆汁都呕了出来。一连几天。
都是如此。吃什么都吐。浑身乏力。月信也迟了快两个月。一个可怕的念头。像冰冷的毒蛇。
缠住了我的心脏。我避开府里的人。悄悄去了城西的医馆。老大夫搭着我的脉。闭着眼。
半晌。睁开。“恭喜夫人。”他脸上带着笑。“是喜脉,快两个月了。
”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手脚冰凉。喜脉?两个月?就是…就是那个混乱的夜晚?
“夫人?夫人?”老大夫看我脸色不对,“您…还好吗?”我回过神。勉强扯出一个笑。
“好…好…谢谢大夫。”我浑浑噩噩地走出医馆。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发冷。
手不自觉地抚上小腹。那里还很平坦。却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在生长。沈铮的孩子。这个认知。
让我恐惧得几乎站不稳。怎么办?他会怎么想?会要我生下来吗?
还是会…像丢弃一件垃圾一样,处理掉?我不敢想。我躲在房里。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食不下咽。夜不能寐。肚子里的孩子却不管这些。它顽强地生长着。我的孕吐越来越厉害。
人也迅速消瘦下去。纸包不住火。终于。伺候我的小丫鬟发现了端倪。
她惊恐地看着我吐得昏天暗地。“姑…姑娘…您这是…”“没事。”我擦着嘴,脸色苍白,
“吃坏了东西。”她眼神闪烁。没再问。但我知道。瞒不住了。果然。第二天傍晚。
沈铮来了。他脸色铁青。像笼罩着一层寒霜。屏退了所有人。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
空气凝固得能冻死人。他盯着我。目光像刀子。刮过我的脸。最后落在我依旧平坦的小腹上。
“谁的?”他问。声音冰冷。没有一丝温度。我的心沉了下去。“什么谁的?”“孩子。
”他吐出两个字,像淬了冰渣,“谁的野种?”野种。这两个字。像两把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我的心上。我猛地抬起头。看着他。看着他眼中毫不掩饰的厌恶和暴怒。
一股血气直冲头顶。“你说是谁的?”我反问,声音抖得厉害。他一步上前。
狠狠捏住我的下巴。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姜忘忧!”他咬牙切齿,“别跟我耍花样!
说!是不是趁我不在府里,勾搭了哪个不长眼的东西?”剧烈的疼痛从下巴传来。
却比不上心口的万分之一。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那道疤显得格外狰狞。
这就是我爱了那么多年的竹马。这就是我放在心尖上等了许多年的少年郎。多可笑。多可悲。
泪水毫无预兆地涌上来。模糊了视线。我用力掰他的手。“放开我!”他非但没放。
反而捏得更紧。“说!”“是你的!”我崩溃地哭喊出来,“是你的!沈铮!那天晚上!
你忘了?!”他像是被雷劈中。猛地僵住。捏着我下巴的手。触电般松开。
他踉跄着后退一步。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看看我的肚子。眼神混乱。惊愕。
然后是更深的恐惧和…厌恶?“不…不可能…”他摇头,喃喃自语,
“怎么会…”他像是想起了那个混乱的夜晚。想起了他失控的吻。
想起了他后来的暴怒和驱逐。脸色瞬间惨白如纸。“不可能…”他重复着,眼神狂乱,
“一定是弄错了…对!弄错了!”他猛地看向我。眼神像抓住救命稻草的溺水者。“去落掉!
”三个字。像三把冰锥。狠狠扎进我的心脏。我听见自己血液凝固的声音。“你说什么?
”“去落掉这个孩子!”他低吼,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疯狂,“现在!立刻!
我让嬷嬷去准备药!”他转身就要去叫人。“沈铮!”我用尽全身力气喊住他。
声音嘶哑得像破锣。他停住脚步。没回头。背影僵硬。“这是我的孩子。”我捂着小腹,
一字一句地说。他猛地转过身。眼神猩红。“你的孩子?姜忘忧!你搞清楚!这是个孽种!
一个错误!”他指着我的肚子。手指颤抖。“他根本不该存在!
他的存在只会提醒我那天晚上有多荒唐!提醒我…”他顿住。后面的话没说出口。但我知道。
提醒他什么。提醒他背叛了死去的阿沅。提醒他碰了一个低贱的替身。
提醒他失控的欲望和混乱的内心。“听着!”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语气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残忍,“我会给你一笔钱,足够你和你家人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找个地方,安顿下来。这个孩子,必须处理掉。”他看着我。眼神冰冷。毫无转圜余地。
“这是命令。”命令。多熟悉的词。就像当初命令我穿上阿沅的衣服。梳起阿沅的发髻。
扮演一个死人的影子。现在。他又要命令我杀死腹中的骨肉。只因为这个生命的存在。
玷污了他对阿沅“神圣”的思念。多讽刺。我看着他那张英俊却冷酷的脸。
看着他那双曾经盛满少年星光的眼睛。如今只剩下寒冰和厌恶。心里最后一点火星。
彻底熄灭了。连灰烬都不剩。我忽然不哭了。也不抖了。一种奇异的平静笼罩了我。
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好。”我说。声音出乎意料地平稳。他愣了一下。
似乎没料到我这么干脆。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像是松了口气。
又像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你…想通了就好。”他语气缓和了一些,
“我会安排好一切。”“不用了。”我打断他。他皱眉。“什么?”“我说,不用你安排。
”我看着他,清清楚楚地说,“钱,我不要。”“你的地方,我也不去。”“孩子,是我的。
”“我会走。”“离开这里。”“永远。”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像是没听懂我的话。
“你说什么?”“我说。”我深吸一口气,每一个字都咬得极重,“我走。带着我的孩子,
离开将军府。从此以后,你我两不相欠。生死,各安天命。”他死死盯着我。
眼神像要穿透我的皮肉。“姜忘忧,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很清楚。”“离开这里,
你拿什么活?你爹娘怎么办?你弟弟怎么办?”他试图用现实压垮我。我笑了。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沈大将军。”我抹掉眼角的泪,“不劳您费心。”“我姜忘忧,
当年能在债主手里保住自己。”“如今,就能带着我的孩子活下去。
”“至于我家人…”我看着他,“这些年,承蒙将军‘照拂’,欠您的,
我用这些年做替身的工钱抵了。不够的,下辈子还。”“从今往后,他们是生是死,
是贫是富,都与你沈大将军无关。”“你!”他气结,额角青筋暴跳,“你简直不识好歹!
”“是啊。”我点头,“我是不识好歹。所以,不碍您的眼了。”我转身。开始收拾东西。
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的旧衣服。一些零碎的铜钱。
还有…角落里那个落满灰的小瓷瓶。我把它捡起来。擦干净。放进包袱。他站在原地。
看着我利落的动作。像一尊石化的雕像。“你真要走?”他声音发涩。“是。
”“为了…这个孽种?”我收拾东西的手一顿。慢慢直起身。看着他。“他不是孽种。
”“他是我姜忘忧的骨肉。”“是我的命。”他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
一个字也没说出来。眼神里翻涌着我看不懂的情绪。愤怒。挣扎。痛苦。还有一丝…茫然。
我背起小小的包袱。最后看了一眼这个住了几年的精致牢笼。“将军。”“保重。
”我挺直脊背。从他身边走过。没有回头。一步一步。走出了这座富丽堂皇的将军府。
阳光有些刺眼。我抬手挡了一下。手放在小腹上。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在顽强地跳动。
“别怕。”我轻声说。“娘带你回家。”身后。沉重的大门。缓缓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隔绝了里面那个冰冷的世界。也隔绝了我荒唐的过去。三年后。江南。临安城。
我的小绣坊刚刚开门。“忘忧姐!快!新到的苏缎!花样可好看了!
”隔壁布庄的周娘子风风火火地跑进来。“就来!”我笑着应道,把手里的绣绷放下。
小院阳光正好。葡萄藤架下。一个小小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跑过来。一把抱住我的腿。
奶声奶气地喊:“娘!抱!”我弯腰。把她抱起来。亲了亲她软乎乎的小脸蛋。“小满乖,
娘去隔壁看看布,回来给你带糖糕。”“糖糕!甜甜!”小丫头眼睛立刻亮了,拍着小手。
眉眼弯弯。笑起来。左边脸颊有个小小的梨涡。像极了她爹。“忘忧!快点!
”周娘子在门口催。“来了!”我把小满交给帮忙看店的吴婆婆,“婆婆,
辛苦您看会儿小满。”“去吧去吧,小满跟婆婆玩。”吴婆婆笑眯眯地接过孩子。
我快步走出绣坊。和周娘子一起往码头那边去。三年前。我带着身孕离开京城。一路南下。
身上的盘缠不多。靠给人缝补、绣花,勉强糊口。后来在临安城落脚。用最后一点钱,
租了这个小铺面。前面开店,后面住人。取名“忘忧绣坊”。小满是在一个春夜出生的。
生她的时候。疼得死去活来。接生的稳婆直叹气。“你这身子骨…以前怕是亏得厉害,
又是头胎…遭罪啊…”我咬着布巾。汗水和泪水糊了满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
我和孩子都要活下去。当那声微弱的啼哭响起时。我浑身脱力。
看着稳婆手里那个红彤彤、皱巴巴的小东西。眼泪止不住地流。“是个丫头!瞧这眉眼,
俊着呢!”稳婆把孩子抱给我看。小小的。软软的。闭着眼。像只小猫。
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她。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小满。”我轻声叫她,“娘的小满。
”小满。我的女儿。我的命。从此。我在这个陌生的江南小城扎下了根。白天开店。
晚上哄睡了小满。就坐在灯下赶绣活。手指被针扎破无数次。眼睛熬得通红。
但看着小满一天天长大。会笑。会爬。会咿咿呀呀地叫娘。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
我断绝了和京城的所有联系。爹娘和弟弟那里。只托人悄悄带过两次钱和信。
说我在江南安好。勿念。没有提小满。不想让他们担心。更不想…节外生枝。日子清贫。
但安心。小满是我生命里唯一的光。码头上。新到的苏杭绸缎果然漂亮。水一样滑。
花样时新。“这个!还有这个淡青的!都给我扯些!”我挑了几匹。“忘忧姐眼光就是好!
”周娘子帮我抱着布,“你家小满,**岁了吧?该做几身漂亮小裙子了!”“是啊。
”我笑着付钱。抱着布往回走。心里盘算着给小满做什么样式。刚走到巷子口。
就看见吴婆婆抱着小满。站在绣坊门口。神色有点慌张。“忘忧!你可回来了!
”“怎么了婆婆?”“小满…小满刚才玩着玩着,突然说热,
我摸着头有点烫…”吴婆婆急道。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放下布。伸手去摸小满的额头。
滚烫!小脸也烧得通红。蔫蔫地趴在我肩上。“娘…难受…”她小声哼哼。“不怕不怕,
娘在。”我强作镇定,心却揪紧了,“婆婆,麻烦您帮我看下店!”“快去快去!孩子要紧!
”吴婆婆连声说。我抱着小满就往医馆跑。心里慌得像擂鼓。小满身体一直不错。很少生病。
这次烧得这么突然。医馆里。老大夫仔细诊了脉。又看了看小满的舌苔。眉头紧锁。“大夫,
怎么样?”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邪风入体,来势汹汹啊。”老大夫叹气,“孩子太小,
底子又弱…怕是…”他欲言又止。我更慌了。“大夫!您一定要救救她!多少钱我都给!
”“不是钱的事。”老大夫摇头,“这病…凶险。我开个方子,先吃着。
能不能熬过去…看孩子的造化了。”造化?这两个字像千斤重锤。砸得我眼前发黑。
我抱着滚烫的小满。跌跌撞撞回到绣坊。煎药。喂药。小满烧得迷迷糊糊。药喂进去就吐。
小脸烧得通红。呼吸急促。小小的身子在我怀里颤抖。“娘…疼…”她闭着眼,
无意识地呢喃。我的心像被刀绞。“小满乖…吃了药就不疼了…”我一遍遍哄。一遍遍喂。
药汁洒了大半。她的小脸越来越红。气息越来越弱。“小满…小满你别吓娘…”我抱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