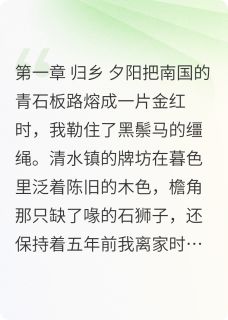
第一章归乡夕阳把南国的青石板路熔成一片金红时,我勒住了黑鬃马的缰绳。
清水镇的牌坊在暮色里泛着陈旧的木色,檐角那只缺了喙的石狮子,
还保持着五年前我离家时的姿态。马蹄踏过石板的脆响惊飞了檐下的麻雀,
它们扑棱棱掠过酒旗,带起一阵陈年酒气——这气息让我喉头发紧,
恍惚间竟分不清是故乡的味道,还是边关风沙里淬着的血腥气。路人纷纷驻足,
指尖戳戳点点。有人认出了我背后那杆长枪,枪缨上的红绸虽已褪色,
却仍能看出浸过血的深暗;有人盯着我这身明光铠,
护心镜上北狄弯刀的刻痕在夕阳下像道狰狞的疤。他们的眼神从最初的惊疑,慢慢变成敬畏,
最后染上几分刻意的谄媚。我挺直脊背,感受着这些目光在铠甲上流淌,
胸腔里五年积攒的戾气与野心,像被风吹燃的火星,噼啪作响。"是陈铁山!
陈家小子从边关回来了!"有人扯着嗓子喊,声音里带着咋舌的惊叹。
"听说杀了十七个敌兵呢,圣上都赏了军功!"这些话像热油浇在炭火上,
让我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想起雁门关的雪夜,想起被我刺穿喉咙的北狄首领,
想起将军拍着我肩膀说"你小子以后前程无量"——是啊,
我陈铁山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会为半袋杂粮跟人争得头破血流的穷小子了。穿过镇口的石桥时,
黑鬃马突然放慢了脚步。桥洞下的石缝里,还留着我当年刻下的歪扭名字,
旁边是个模糊的"春"字。记忆像被马蹄踏起的尘土,
猛地呛进鼻腔——赵春娘总爱在这儿等我,手里攥着块用布包好的杂粮饼,
见我来了就往我怀里塞,左颊那块暗红的胎记在日头下泛着光,像朵长错了地方的花。
我勒紧缰绳,黑鬃马打了个响鼻,蹄子在石板上刨出浅坑。前面就是A2首层那间老屋,
木门上的裂痕比五年前更深了,像道永远合不上的伤口。推开门的瞬间,
霉味混着灯油的气息扑面而来,像盆掺了冰碴的冷水,兜头浇灭了我浑身的热意。
灶间昏黄的油灯晃得人眼晕,灯芯爆出的火星落在地上,照亮了满地的稻草。
赵春娘猛地从灶台前站起,粗布围裙上沾着黑灰,手里攥着的抹布"啪嗒"掉在地上。
她瘦了,颧骨尖得像山石,眼窝陷下去,唯有那双眼睛,在看到我时突然亮起来,
像暗夜里点起的火把。可那点光亮很快就变成了卑微的狂喜,她的嘴唇哆嗦着,
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铁山哥......你、你真回来了?"她扑过来想替我解甲,
粗糙的手指刚碰到护心镜的冰凉,我下意识侧身躲开。护心镜上的刻痕还带着北狄人的血气,
那是军功的勋章,怎么能被这双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玷污?我皱眉扫过屋里:灶台是冷的,
铁锅沿结着黑垢;桌上那碗腌菜泛着死气,
几片蔫黄的菜叶漂在浑浊的盐水里;旁边的杂粮饼硬得能硌掉牙,上面还沾着点灰。
这就是我守了五年边关、杀了十七个敌兵换来的"家"?
记忆里那个模糊的身影突然清晰起来:她会在我出征前连夜纳鞋底,
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株倔强的芦苇;她会把省下来的米磨成粉,蒸成小小的米糕,
藏在我行囊最深处......可眼前这个女人,憔悴、丑陋,浑身散发着穷酸气,
右眉那道疤尤其刺眼——那是当年为了护我,被张屠户家的恶犬咬伤的,可此刻看在眼里,
只觉得碍眼。"嗯。"我从喉咙里挤出个单音节,把缰绳扔在门后,军靴碾过地上的稻草,
发出窸窣的声响。她慌忙去拾缰绳,手指被我的靴底压住,指节瞬间泛白。可她没作声,
只是咬着唇,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像被风吹灭的灯芯。第二章金钗在老屋住了三日,
我终于忍无可忍。赵春娘总是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端茶时手会抖,说话时声音像蚊子哼。
她做的饭永远是杂粮饼配腌菜,说要给我攒钱置地,
可我陈铁山需要的是良田千亩、华屋百间,不是她这点可怜的积攒。第三日清晨,
我借口置办军功文书,翻身上了黑鬃马。马蹄踏过青石板路时,
我听见身后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回头看见赵春娘站在巷口,手里攥着个布包,
风掀起她的粗布衣角,露出里面磨得发亮的补丁。"铁山哥,
带上这个......"她想追上来,却又不敢,只是站在原地,把布包往我这边递。
我没回头,夹了夹马腹,黑鬃马扬起前蹄,很快就把那道单薄的身影甩在了身后。
入城后的街市热闹得晃眼,绸缎庄的幌子在风里招摇,酒肆飘出的肉香勾得人喉头发紧。
我勒住马在"玲珑阁"前驻足,这是城里最气派的首饰铺,
柜台里的金钗银镯闪得人睁不开眼。就在这时,黑鬃马突然人立而起,
前蹄刨向一辆停在路边的马车。那是辆翠盖珠缨的马车,车帘绣着金线牡丹,车轮包着铜皮,
碾过石板路时悄无声息。我猛地拽紧缰绳,马嚼子勒得黑鬃马嘶鸣不止,
车帘却被一只戴着赤金镶玉镯子的手轻轻掀开了。露出的那张脸,像刚剥壳的荔枝,
肤光胜雪,眉梢眼角都带着钩子。她的发髻梳得一丝不苟,
鬓边那支点翠步摇随着马车的晃动轻轻摇曳,垂下的珠串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军爷好身手。"她的声音娇得能滴出水来,纤纤玉指捏着一方锦帕递过来,
苏合香的气息顺着风飘过来,瞬间盖过了我身上的硝烟味,"擦擦汗吧。
"我接过帕子的瞬间,指尖触到她的温软,心里像有团火猛地烧起来。那帕子绣着并蒂莲,
丝线细密得像蛛网,边角还缀着颗小小的珍珠。
的雕花栏杆、车帘上的金线牡丹、她腕上镯子的莹光......这才是我该配得上的生活!
"多谢姑娘。"我故意扯开衣襟,露出胸前那道最深的刀疤。疤痕像条暗红色的蛇,
从锁骨蔓延到心口,"这是在雁门关拼杀时留下的,北狄人的弯刀划的,差一点就刺穿了心。
"她的眼波在刀疤上流转,突然亮起来,像发现了稀世珍宝。"军爷真是少年英雄。
"她的指尖在帕子上轻轻打着转,语气里的兴味更浓了,"不知......成家了吗?
"那一刻,赵春娘的脸在我脑海里闪了一下——她左颊的胎记,右眉的疤痕,
还有那双永远带着怯懦的眼睛。可这影像很快就被眼前的笑靥彻底碾碎。
我扯出个得意的笑:"尚未。大丈夫当以功业为重,儿女情长不过是累赘。"她掩唇轻笑,
步摇上的珠串又响起来:"军爷说的是。小女子柳金凤,家父是这玲珑阁的东家。
若军爷不嫌弃,不如移步阁中喝杯清茶?"我几乎是立刻翻身下马,连黑鬃马都忘了拴。
柳金凤的马车在前面引路,车轮碾过石板的声音,在我听来像胜利的鼓点。回到那间破屋时,
已是深夜。赵春娘还在灶台前忙碌,锅里飘出肉香,是那种久违的、带着油脂的醇厚香气。
她见我进来,慌忙用围裙擦着手,端出个粗瓷碗——里面是炖得酥烂的肥肉,油花浮在上面,
映着她讨好的笑:"铁山哥,我攒了三个月的钱,割了斤肉,
你尝尝......"我没看那碗肉,从怀里掏出张纸拍在桌上。休书是托城里账房写的,
墨迹还没干透,"休书"两个字像淬了毒的钉子,钉在粗糙的木桌上。"签了。
"我的声音比边关的寒风还冷,"你我夫妻情分,到此为止。
"她手里的碗"哐当"摔在地上,热油溅在她裤脚,烫出几个黑印。可她像没知觉,
只是死死盯着那张纸,嘴唇哆嗦着,眼里的光一点点熄灭:"为、为什么?""无子。
"我别过脸,不敢看她的眼睛,怕那里面的东西动摇我。可话一出口,又觉得不够狠,
便补了句,"有恶疾——你这脸,谁看了不晦气?"我顿了顿,把最狠的话砸出去,
像挥出最锋利的刀:"再说,你配不上我了。柳家**......玲珑阁的柳金凤,
你见过吗?她穿的衣裳,比你这破屋还值钱;她一根头发,都比你金贵。"她突然笑了,
笑声嘶哑得像破锣,眼泪却顺着脸颊往下淌,冲开了脸上的灰,露出那片暗红的胎记。
她的手指抖得厉害,却还是拿起休书,用那双被冻疮裂开口子的手紧紧攥着,指节泛白,
仿佛要把纸嵌进肉里。"好。"她只说一个字,声音轻得像叹息,却带着种说不出的决绝。
她转身进屋,很快拎出个小包袱。包袱皮是我当年穿旧的军衣改的,边角都磨破了。
我瞥见里面除了几件打满补丁的旧衣,
还有那块她没带走的杂粮饼——就是她总往我怀里塞的那种,硬邦邦的,却带着麦香。
她走出门口时,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恨,也没有怨,只有一片死寂,
像被大雪压过的荒原。我心里莫名一紧,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
可那点异样很快就被对柳家富贵的向往盖了过去。门"吱呀"关上的瞬间,
我仿佛听见杂粮饼掉在地上的声音。第三章枷锁入赘柳府那天,红绸从门口铺到街口,
吹鼓手敲得震天响,连街对面的药铺都歇了业,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我穿着绣金的喜服,
站在柳金凤身边,看着她头上那支累丝嵌宝的凤钗——钗头的珍珠有鸽子蛋那么大,
在阳光下闪着莹光,据说能买下半条街的铺子。柳金凤的手搭在我腕上,
涂着蔻丹的指甲轻轻掐着我的皮肉,带着种炫耀的亲昵。宾客们的贺词像潮水般涌来,
"天作之合""金玉良缘"......这些话让我晕头转向,觉得前半生吃的所有苦,
都在这一刻得到了补偿。可第一晚,我就被她踹下了锦榻。她嫌恶地用帕子捂着脸,
苏合香的气息裹着冰冷的嘲讽:"一身汗味,粗鄙不堪。去沐浴,用那瓶波斯进贡的香露,
洗三遍再来。"我忍着气照做了。香露的味道甜得发腻,洗到第二遍时,皮肤已经发紧,
可我不敢违逆。柳府的丫鬟们站在屏风外,压抑的嗤笑声像针一样扎进耳朵。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身锦衣华服越来越像枷锁。管家递账本时,永远先看柳金凤的脸色,
我说话时,他甚至敢转头跟旁边的仆妇使眼色。有次我想添置一把称手的宝刀,
柳金凤正在逗她的狸猫,闻言嗤笑一声:"府里护院的刀剑比你当年在边关用的好十倍,
你一个享福的爷们儿,舞刀弄枪作甚?难不成还想回那吃沙喝风的鬼地方?
"她的狸猫"喵"地叫了一声,爪子搭在她的膝头,享受着比我还金贵的待遇。
宴席上的羞辱更是家常便饭。有次州官来访,我多看了两眼献舞的姬妾,
柳金凤突然端起茶杯,滚烫的茶水泼在我手上,她却笑吟吟地对众人说:"夫君看迷了眼,
喝口茶醒醒神。"宾客们都噤了声,州官的嘴角却撇了撇。我古铜色的手背瞬间起了燎泡,
钻心地疼,可只能强扯着笑容,说"夫人说的是"。那燎泡后来烂了半个月,
柳金凤只让丫鬟送了瓶最便宜的药膏,还嘟囔着"这点小伤也值得大惊小怪"。
我试图重拾武艺,在花园练拳时,柳金凤总爱倚着栏杆嗑瓜子。她的瓜子皮故意往我头上扔,
壳子落在我发间,她就咯咯地笑:"哟,陈大将军好威风,
莫不是还想回那穷酸地方当你的兵痞?安生待着吧,柳家养得起你这闲人!
"昔日在边关的悍勇,在日复一日的羞辱中被消磨得干干净净。我开始懒得反驳,懒得争辩,
甚至在她当着下人的面骂我"废物"时,都能低下头,假装没听见。脊梁不知从何时起,
就慢慢弯了。有次喝多了酒,想起雁门关的兄弟——王二狗总爱偷藏半块饼给我,
李老栓教我怎么用草药止血,还有死去的赵校尉,最后一口气还在喊"守住关口"。
我忍不住跟柳金凤念叨:"当年在雁门关......"话没说完就被她打断。
她正用银签挑着燕窝,闻言把签子一扔,燕窝溅在描金的碗沿上。"又提你那穷酸过去?
"她的声音尖利得像刀子,"若不是看在你那点军功还有用,
能让我爹在州官面前多说两句话,你以为柳家会要你这莽夫?"我攥紧了拳头,
指甲嵌进掌心,血腥味在嘴里散开。可看着她身后那些仆妇鄙夷的眼神,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提过想生个孩子,延续香火。柳金凤正给她的狸猫梳毛,
漫不经心地说:"生孩子?疼得很,又损颜色。有这猫儿解闷就够了。你呀,
当好你的柳家姑爷便是,别想那些有的没的。"那只狸猫突然朝我龇牙,露出尖尖的爪子。
第四章寒夜被我弃如敝履的赵春娘,那时正在富户的后巷浆洗。她离开清水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