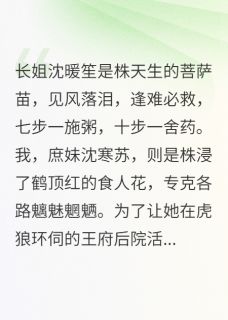
长姐沈暖笙是株天生的菩萨苗,见风落泪,逢难必救,七步一施粥,十步一舍药。我,
庶妹沈寒苏,则是株浸了鹤顶红的食人花,专克各路魑魅魍魉。
为了让她在虎狼环伺的王府后院活下去,我陪嫁进了镇北王府。
她嫁给了体弱多病的王府世子萧墨轩。而我,嫁给了世子的祖父,
年逾古稀的老王爷……他爹!王府真正的定海神针——镇北王太尊萧擎苍。婚后不久,
世子从北疆带回个“孤苦无依”的牧羊女,长姐心疼得直绞帕子:“妹妹,我想认她做义妹!
”我眼皮都没抬:“行,你认我也认。”谁知,认亲茶还没奉上,
就听说世子被太尊罚去跪寒玉祠堂三日。萧太尊拄着玄铁蟠龙杖,
敲得青石板火星四溅:“孽障!想让你太爷爷我晚节不保,背上个苛待弱女的名声就直说!
”1我是镇北王世子妃沈暖笙的庶妹,沈寒苏。整个北境都知道,沈家这对异母姐妹,
情分深得令人咋舌。无他,只因我那长姐,是株罕见的圣光灵芝,心肠软得能当云片糕,
路过的雀儿打喷嚏她都得诵段平安经。而我,自幼被扔在药王谷与毒虫为伍,
看多了人心鬼蜮,生死无常,心窍早淬炼得比孔雀胆还毒。赏花宴上,
都督家的千金“失手”要将滚沸的参汤泼向长姐裙摆,我指尖微弹,
一枚淬了麻痒散的银针悄无声息刺入她膝弯。那千金腿一软,
整碗汤全扣在了自己精心养护的牡丹髻上。“啊——!”尖叫穿云裂石。都督千金钗环散乱,
怒指我:“沈寒苏!你敢使阴招?!”我慢条斯理捻着袖口金线,眼皮都懒得掀:“阴?
我姐是菩提转世,普度众生,你动她?问过我这个负责清扫业障的修罗夜叉了吗?”我凑近,
用气声在她耳边低语:“下次再‘手滑’,泼你脸上的可就是化骨水了。
”长姐沈暖笙这才回神,慌忙去搀扶那千金,满面忧急:“哎呀,妹妹可烫着了?
都怪这路不平……”转头又对我蹙眉:“二妹,你怎如此莽撞!”我:“……”得,白费劲。
对这种浑身冒圣光的,欺负她像欺负棉花,护着她像护着琉璃盏,憋屈。
可偏偏看着她被人当肥羊宰,我这“夜叉”就忍不住挥叉。久而久之,
倒成了她的专属“净坛使者”。2长姐能全须全尾地活到出阁,
全靠我这“夜叉”一路劈荆斩棘。然而。她归宁那日,我才离府半旬,
她就又踩进了天坑——她的夫婿,镇北王世子萧墨轩,是个出了名的药罐子兼耳根软。
长姐怜惜夫君缠绵病榻,拿出压箱底的银票替他打点外院庶务,结果被府中老油子联手做局,
账面上生生被挪空了五万两。消息传开,她成了北境最大的笑柄。“我苦命的儿啊!
”继母王氏只会搂着女儿哭天抢地。我那戍边多年的爹,对着敌酋能挽三石弓,
对着家宅事却只会搓手叹气:“忍忍吧,王府势大,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我听得额角青筋直蹦。这窝囊气,真是祖传的!“这也能忍?”我嗤笑一声,
眼风扫过屋里愁云惨雾的三人。哭声骤停。继母和长姐怯生生望着我,父亲也缩了缩脖子。
我这个自幼离家、行事诡谲的庶女,对他们而言,威慑力堪比活阎罗。“我给我姐陪嫁。
”我言简意赅。继母和父亲瞪大眼:“你要给世子做妾?”“不。”我唇角勾起一丝冷弧,
语惊四座,“我要给世子当太祖母。”3当世子妃?没兴趣。但当世子的太祖母,
这辈分听着就解气。镇北王府的老祖宗,萧太尊萧擎苍,年逾古稀,
筋骨却硬朗得似百年玄铁,曾掌天下兵马,门生故吏遍朝野。老王爷是他儿子,
世子是他重孙。他老人家鳏居多年,在府中是说一不二的擎天玉柱。嫁给他,
我就是萧墨轩板上钉钉的太祖母!管教他,名正言顺。……我是深谙世情的毒花。
只用了半炷香的功夫,就让萧太尊点头,三媒六聘、八抬大轿娶我过门——萧太尊的军机堂。
我开门见山:“萧擎苍。”他抬眸,苍老却锐利如鹰隼的目光锁住我。“您鳏居多年,
外面都传您清心寡欲,早断了红尘念想,一心向道。”他盘着乌木佛珠的手顿住。
我逼近一步,压低声音,带着点蛊惑:“娶我。我能让全北境都知道,您老人家,宝刀未老,
雄风尚存。”权倾朝野又高寿的老家伙,最忌讳什么?一是后继无人,
二是被人说清心寡欲是假,实则……不行。萧太尊:“……”他沉默片刻,眼中精光爆闪,
忽然抚掌大笑,声震屋瓦,“好个胆大包天的小妖女!成!这笔买卖,老夫做了!婚后,
有劳沈二姑娘替老夫‘正名’了。”成了!4萧太尊续弦,
娶的还是个能当他曾孙女的小姑娘,这桩婚事震得北境抖了三抖。闹洞房?无人敢。
但看笑话的,挤满了王府角门。自然也包括我那便宜重孙,萧墨轩。
他被挡在“砺锋堂”太尊居所外时,我正倚着雕花窗棂嗑瓜子。“太爷爷,孙儿给您道喜!
祝您和……呃,太祖母,日月同辉,琴瑟和谐!”萧墨轩的声音带着谄媚,
又透着十二万分的别扭。都说礼多人不怪。可萧太尊听完,那张刀刻斧凿的脸更沉了,
玄铁蟠龙杖在地上重重一顿,声如闷雷:“谐?谐个屁!
”“老夫能不能和你太祖母琴瑟和谐,全看你小子懂不懂事!再敢让你媳妇掉一滴眼泪,
仔细你的骨头!”萧墨轩:“???”他彻底懵圈。萧太尊为啥火大?
因为我天天在他耳边“布道”。不分时辰,不分场合。比如洞房花烛夜。龙凤喜烛高燃,
萧太尊身着暗金蟒袍,虽年迈,身姿却挺拔如松,周身久掌杀伐的威势迫人。而我,
正毫无形象地啃着桌上的合卺酥:“太尊,您这样不行。”萧太尊也不恼,
慢悠悠倒了杯温酒推过来:“哦?如何不行?”我接过抿了一口:“您这威慑,太含蓄。
您那重孙,脑子跟榆木疙瘩灌了浆糊似的,不把话凿穿了塞他脑仁里,他听不懂。
您得说得再狠点,比如,再亏空银子,就送他去北疆牧马十年。”萧太尊睨我一眼,
哼道:“张口闭口那孽障。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冲着他才跳我这老坑的。”我:“?
”不然呢?我姐不嫁你重孙,我能跳你这坑?看着他银发如雪但气势不减的样子,
我把话咽回去,扯出个假笑:“当然不止,您老骥伏枥,威风八面,也是原因之一。
”另一部分,
自然是图他年纪大——好糊弄、地位高——能压阵、据说也“清心寡欲”——省心。
“所以还是有一部分为了那孽障。”萧太尊显然没信后半句,花白的剑眉一挑,
抄起手边的拐杖作势要敲,“小妖女,就不能多惦记点老头子我?”我狸猫般往后一缩,
翻身滚上宽大的紫檀拔步床,裹紧锦被滚到最里侧:“多惦记您?我怕您老人家道心不稳!
睡了睡了,太尊安寝!”烛火摇曳,映着他哭笑不得又隐含纵容的脸,最终化作一声轻叹。
5因着萧太尊对我“言听计从”,加上我精准拿捏了萧墨轩的死穴——他畏他太爷爷如虎。
“太祖母,您发发慈悲,别让太爷爷再逼我练那劳什子枪法了!我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
”萧墨轩苦着脸哀嚎。我慈祥地拍拍他肩膀:“乖重孙,太祖母是为你好。你看你,
身子骨弱,再不练点武艺强身,以后怎么镇守这偌大的北境?太爷爷也是望孙成龙啊。
”转头我就去砺锋堂:“太尊,墨轩说最近练武太轻松,筋骨都没活动开,
我看得请军中那位‘鬼见愁’罗教头来亲自操练。”萧墨轩:“!!!”他想告状,
太尊眼皮一掀:“你太祖母殚精竭虑为你筹谋,你还敢抱怨?自己没二两力气,
倒嫌操练太轻?明日开始,负重加倍!”萧墨轩:“……”他只能憋着满腹委屈,
每天拖着酸软身子去给长姐请安,顺便汇报“武艺进展”,夫妻俩虽谈不上蜜里调油,
倒也风平浪静。直到前些日子,萧墨轩奉父命去北疆巡视军屯。长姐和我品茶时,神思不属,
连茶都喝到了鼻子里。“担心他?”我放下茶盏,“北疆太平,无甚险情。专心。
”长姐摇头,秀眉紧锁:“不是担心。是……他来信说,返程途中,
救了个被马贼劫掠的可怜孤女,那女子家破人亡,无依无靠,想带回府中给个安身立命之所。
”我捏着茶盖的手一滞,眼神锐起:“孤女?什么底细?姓甚名谁?
”长姐茫然:“信上未提,只说身世凄苦……”我心中警铃大作。王府世子,体弱心软,
路上“偶遇”家破人亡的孤女?这戏码老掉牙了!十成十是冲着长姐这世子妃之位来的!
我敛了笑意,盯着长姐:“那你打算如何?收留她?认她做义妹?还是给她寻个好人家?
”长姐咬唇,她知道我能让这“孤女”无声无息“病逝”。以我“太祖母”的身份,
易如反掌。她挣扎良久,眼中竟闪过一丝罕见的决绝:“二妹,我想……收她做义妹!
好好待她,给她寻个好归宿!”我差点被茶水呛死。好家伙,不愧是我姐!
人家都要来刨你墙角根了,你还想着给人当红娘!我深吸一口气,面无表情:“行,
你收我也收。”当不成她的太祖母,我还不能当她的“太祖母”吗?分居!必须分居!
这破王府待腻了!6当晚,萧太尊从城外军营回府,刚踏进砺锋堂,
就瞥见我书案上墨迹淋漓的“分居书”。萧太尊脚步微顿,捻着佛珠的手紧了紧,
状似随意问:“丫头,写什么呢?这般用功?”“分居书。”我头也不抬。“分居书?
”他声线陡然拔高,几步抢到案前,看清是长姐的笔迹,紧绷的肩线微松,“暖笙的?
为何要分居?墨轩那小子又犯浑了?”隔着几步,我都能感受到他骤然加重的呼吸。“嗯,
”我搁下笔,吹了吹墨迹,“您那宝贝疙瘩重孙,从北疆给您捡回个‘义重孙女’。
我姐菩萨心肠泛滥,想认个妹妹。”萧太尊眉头瞬间拧成死结:“荒唐!”他明显松了口气,
却又为萧墨轩的愚蠢而震怒:“这事老夫知晓了,定会处置。”他以为这就完了?
我在心里冷笑:老狐狸,我那份,早就塞进你常看的兵书夹页里了!……长姐沈暖笙,
生平头一遭做了个离经叛道的决定,整个人处于一种亢奋的晕眩中。
翌日天蒙蒙亮就冲进砺锋堂问安,眼睛亮得灼人:“二妹!我们何时动身?
细软我都收拾妥当了!”我顶着俩黑眼圈,有气无力:“姐,寅时刚过……您老行行好,
让我再眯会儿。”“你怎么了?”她关切道。
我磨着后槽牙:“昨夜被一只老狐狸念了大半宿的‘王府体面’。”长姐恍然,
随即又和我兴致勃勃地讨论起“潜逃”路线。计划不如变化快。萧墨轩回府了。
他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个身着粗布麻衣、弱柳扶风的女子下了马车。那女子身形单薄,
面色苍白,眉宇间凝着化不开的愁绪,真似一朵遭了霜打的铃兰。萧墨轩目光扫过众人,
落在长姐身上,带着讨好和心虚:“夫人,这位是柳絮儿姑娘,身世甚是凄楚……我想着,
能否让她在府中暂住些时日?”柳絮儿怯生生向长姐福身:“絮儿见过世子妃,
给夫人添麻烦了……”那姿态,柔弱堪怜。下人们的目光在柳絮儿和长姐之间来回扫射,
窃窃私语如蚊蚋:“啧,世子爷真是菩萨心肠……”“这姑娘瞧着比咱们王妃……嗯,
更惹人怜呢……”“可怜?我看是祸水还差不多!”长姐的脸色瞬间褪尽血色,身体微颤,
眼泪说来就来,扑簌簌滚落,真真是梨花带雨,我见犹怜(这次是真伤心+真被膈应到了)。
她猛地转身,以帕掩面,肩头耸动。我立刻上前扶住她,压低声音:“对,就这么演!
伤心欲绝!回房就说你想去城外庵堂清修,我陪你。分居书放妆奁最显眼处!
”长姐含泪点头,演得情真意切。就在我们准备抽身退场,执行计划时。
砺锋堂方向传来一声穿云裂石般的暴喝,如九天惊雷:“萧墨轩!给老夫滚过来!
”7再糊涂的世子,在积威深重的太爷爷面前,也成了筛糠的鹌鹑。萧墨轩腿一软,想溜,
却被两名铁塔般的亲卫“请”到了砺锋堂外的“思过厅”。我和长姐隐在回廊朱柱后,
听着心腹丫鬟飞快来报:“世子爷被太尊罚跪在思过厅寒玉砖上了!”“太尊让人请了军棍!
”思过厅内,气氛肃杀如战场。军棍破风声响起,伴随着萧墨轩压抑的痛哼。
萧太尊的声音冰冷如北疆寒铁:“蠢货!去趟北疆,脑子被马踢了?”砰!
“什么来历不明的腌臜东西都敢往府里带!王府的规矩是儿戏吗?”砰!
“老夫看你就是皮子松了!想让你太爷爷我背上个欺凌弱女、晚节不保的污名是吧?
”……长姐站在廊下阴影里,光影切割着她苍白的面容。我心里咯噔一下,问她:“还走吗?
”以她圣光普照的性子,看到萧墨轩挨打,听到太尊那句“晚节不保”,难保不会心软退缩。
她沉默片刻,反问我:“你呢?”我挑眉:“随你。你分,我立刻走;你不分,
我勉为其难再当几天太祖母。”出乎意料,她眼神异常坚定:“我想走。”很好!
毒花护持多年,圣光灵芝终于硬气了一回!而且行动力惊人,转身就要撤。
我一把扣住她手腕:“急什么?”长姐不解。我露出一个标准的妖女微笑:“银票带足了吗?
外面打点处处需钱。“值钱的东西都带上。太尊在教训孙子,一时半刻顾不上。“机不可失。
走,搬家去!”我拽着她风风火火往回冲。库房钥匙?我有!捅开!银票、田契、矿契,
整匣端走!长姐嫁妆里那套前朝御赐的羊脂玉雕件?值钱!打包!
太尊书房里那几柄镶金嵌玉的匕首?顺走!……所过之处,雁过拔毛。
连太尊珍藏的几坛子御赐百年陈酿都被我顺手拎进了包袱。长姐目瞪口呆,被我感染,
也冲进了小厨房,把那个会烤一手绝妙胡饼的西域厨子拽了出来:“带上他!路上吃!
”……“潜逃”异常顺利。萧太尊在思过厅“沉浸式”教孙,
压根不知他的砺锋堂和王府库房正经历一场扫荡。直到他打累了,将军棍一扔。回到砺锋堂,
看着空了大半的多宝格,翻开兵书,
再看看库房管事抖着递上的失物清单……萧太尊捻着佛珠的手,
指节捏得发白:“……”8萧太尊与萧墨轩的反应?我与长姐无暇他顾。马车奔出城三十里,
我叫停了车夫。“怎么了?”长姐抱着胡饼盒子,茫然问。我敲着车壁:“不能回沈家。
”以我爹和王氏那怂样,萧太尊派人递个话,他俩就能把我俩捆了送回去,
还得附赠一句“好好伺候太尊/世子”。我俩一拍即合,掉头直奔渡口,包了艘大船东行。
从烟雨江南,到繁华东海,最后在四季如春的南疆大城“碧榕”落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