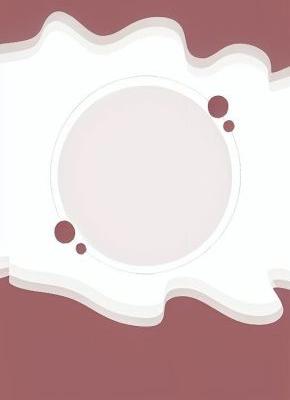
火苗舔舐着红色的封皮,很快将其点燃。
刺鼻的焦糊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沈衾面无表情地看着,看着那张她和顾厉声的合照在火焰中扭曲、变形,最后化为灰烬。
三十年的婚姻,也如同这本假的结婚证一样。
烧了,就什么都没了。
天亮了。
沈衾一夜未睡,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
但她的神情却异常平静。
她像往常一样,为顾厉声准备好早餐,熨烫好他今天要穿的衬衫。
顾厉声起床后,看到她憔悴的脸色,心疼地皱起眉。
“还是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不用。”沈衾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沙哑,“老毛病了,休息一下就好。”
顾厉声没有怀疑。
他坐在餐桌前,喝着沈衾为他盛的粥,习惯性地称赞道:“还是你煮的粥最好喝。”
沈衾垂下眼眸,没有接话。
搁在以前,她会笑着说,“喜欢就多喝点。”
但今天,她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怕自己一开口,就会歇斯底里地质问他。
质问他徐婉清是谁。
质问他为什么要骗她三十年。
但她不能。
她还没有想好该怎么做。
离婚?
这两个字像一把刀,狠狠地扎进她的心脏。
他们有儿子,有共同经营了半生的家。
离婚,就意味着这一切都将分崩离析。
更何况,她连法律上的妻子都不是,又有什么资格提离婚?
她只是一个“同居者”。
想到这里,沈衾的心又是一阵绞痛。
“我今天要去一趟邻市,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可能要明天下午才回来。”顾厉声放下碗筷,擦了擦嘴。
“嗯。”沈衾淡淡地应了一声。
“你自己在家,要好好吃饭,别又随便对付一口。”顾厉声不放心地叮嘱道。
“知道了。”
顾厉声走到玄关换鞋,沈衾跟了过去,手里拿着他的外套。
他穿上外套,习惯性地想拥抱她一下。
沈衾却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顾厉声的动作僵在半空,眼里闪过一丝诧异。
“怎么了?”
沈衾的心跳得飞快,她强装镇定地笑了笑,“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外套上有灰,想帮你拍拍。”
她说着,伸手在他肩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两下。
一个完美的借口。
顾厉声没有再多想,只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那我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门关上的那一刻,沈衾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
她靠在门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仅仅是十几分钟的相处,就几乎耗尽了她所有的心力。
她不敢想象,未来的日子,她该如何面对这个枕边人。
顾厉声走了。
偌大的房子里,只剩下沈衾一个人。
空气里还残留着他身上淡淡的须后水味道。
熟悉又陌生。
沈衾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直到阳光照进客厅,她才缓缓起身。
她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她要知道真相。
徐婉清到底是谁?
她和顾厉声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他要娶一个不爱的人,还要用一本假证来欺骗她?
沈衾回到书房,再次打开那个暗格。
铁盒里,那本属于徐婉清的结婚证静静地躺着。
沈衾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拿起它,仔细地检查着。
除了这本结婚证,盒子里空无一物。
没有任何其他的线索。
沈衾有些失望。
她将结婚证放回原处,目光在书房里逡巡。
顾厉声是个很念旧的人。
如果这个徐婉清对他很重要,他不可能只留下一本结婚证。
一定还有别的东西。
沈衾开始在书房里翻找起来。
她拉开一个个抽屉,翻过一本本书。
书房很大,藏东西的地方也很多。
一个小时过去了,她一无所获。
就在她快要放弃的时候,她的目光落在了书桌上的一个旧笔筒上。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木质笔筒,是他们儿子顾Zechen上小学时,在手工课上做的。
顾厉声一直很宝贝,用了二十多年。
沈衾拿起笔筒,倒出里面的笔。
她晃了晃笔筒,里面发出一声轻微的异响。
有夹层。
沈衾的心又提了起来。
她用发夹小心地撬开笔筒的底部,一块薄薄的木板应声而落。
里面藏着一把小小的,已经泛黑的铜钥匙。
这把钥匙的样式很老旧,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是开什么锁的?
肯定不是那个铁盒的锁,那个她已经撬开了。
沈衾握着那把冰凉的钥匙,脑海中闪过一个地方。
城南,有一家老旧的银行。
顾厉声在那里,有一个保管箱。
这件事,顾厉声从未告诉过她。
是多年前,她无意中看到过一张保管箱的租赁合同。
当时她问起,顾厉声只说是存放一些公司的重要文件。
她也就没有再多问。
现在想来,或许,那里藏着他真正的秘密。
沈衾没有丝毫犹豫。
她换上衣服,拿着那把钥匙,打车直奔城南。
那家银行果然还在,只是比记忆中更加破败了。
来这里办理业务的,大多是些老年人。
沈衾走到柜台前,深吸一口气,报出了顾厉声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您好,我想取一下保管箱里的东西。”
银行职员是个年轻的女孩,她看了一眼沈衾,又看了一眼电脑。
“请出示您的身份证和钥匙。”
沈衾递上自己的身份证和那把铜钥匙。
女孩核对了一下信息,脸上露出一丝为难的神色。
“抱歉,女士,这个保管箱是顾厉声先生用他的个人名义租赁的,按规定,只能由他本人来取。”
沈衾的心一沉。
她早该想到的。
“我是他妻子,”沈衾急切地解释道,“他出差了,让我来帮他取一份急用的文件。”
“那您有他的委托书吗?”
“……没有。”
“那就没办法了,这是规定。”女孩的态度很坚决。
沈衾的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
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不。
她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
“小姑娘,”沈衾的语气忽然软了下来,眼眶也红了,“你就帮帮忙吧。我先生他……他住院了,情况很不好,特意交代我一定要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她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沓钱,悄悄地塞到柜台下面。
“这里面的文件,关系到他的性命,求求你了。”
沈-衾的声音带着哭腔,情真意切。
女孩有些动容,也有些犹豫。
她看了看周围,见没人注意,才低声说:“您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我们主任。”
沈衾的心又悬了起来。
几分钟后,女孩回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男人。
男人打量了沈衾几眼,又看了看她手里的钥匙。
“你真是顾厉声的妻子?”
“是,千真万确。”
“他真住院了?”
“是,急性心梗,还在抢救。”沈衾的谎话张口就来,脸上满是悲痛和焦急。
男人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权衡利弊。
最后,他叹了口气。
“好吧,下不为例。”
他接过钥匙,带着沈衾走进了银行的地下保管库。
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一股陈旧的霉味扑面而来。
男人在一个编号为“520”的保管箱前停下,用两把钥匙打开了箱门。
一个和书房暗格里一模一样的铁盒,出现在沈衾面前。
沈衾的心跳得厉害。
她颤抖着手,打开了盒子。
里面没有文件。
只有一叠厚厚的信,和一张泛黄的旧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笑靥如花的年轻女孩。
她依偎在一个英俊的青年怀里。
那个青年,正是二十多岁的顾厉声。
而那个女孩……
虽然素未谋面,但沈衾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一定就是徐婉清。
因为她的眉眼,和那本结婚证上的黑白照片,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