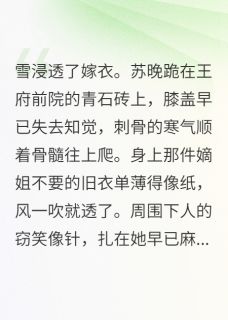
雪浸透了嫁衣。苏晚跪在王府前院的青石砖上,膝盖早已失去知觉,
刺骨的寒气顺着骨髓往上爬。身上那件嫡姐不要的旧衣单薄得像纸,风一吹就透了。
周围下人的窃笑像针,扎在她早已麻木的皮肤上。那半块贴身藏了七年的残玉,
此刻被柳如烟的侍女狠狠踩在脚下碾磨,玉屑混着污雪,成了烂泥。心口那点微弱的火苗,
噗地一声,彻底熄了。她闭上眼,滚烫的泪砸在冰面上,瞬间冻结。
-----------1花轿摇摇晃晃,像一口移动的棺材。苏晚攥着袖口,
指甲深陷掌心,试图压住那阵要把她骨头都冻透的寒意。大红盖头隔绝了视线,
只听见王府门前震天的鞭炮声,还有宾客们压低的、幸灾乐祸的议论。“一个庶出的孤女,
也配顶替嫡**?”“啧,战神王爷那脾气,怕是活不过今晚……”轿帘猛地被掀开,
刺骨寒风裹着雪粒子灌进来。一只骨节分明、戴着玄铁护腕的手,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道,
粗暴地扯掉了她的盖头。光刺得苏晚眯起眼。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刀削斧凿般的脸。
剑眉斜飞入鬓,鼻梁高挺,薄唇紧抿成一条冰冷的直线。最慑人的是那双眼睛,
深不见底的寒潭,翻涌着毫不掩饰的戾气和……厌恶。他穿着玄色蟒袍,身量极高,
站在轿门前投下的阴影,沉沉地笼罩着她。萧绝的目光在她脸上逡巡,像冰冷的刀锋刮过。
片刻,他唇角勾起一丝讥诮的弧度,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穿透寒风,砸进每个人耳中。
“赝品,”他冷笑,目光扫过她身上同样刺目的正红嫁衣,“也配穿这个颜色?”话音未落,
他猛地抬手。嗤啦——裂帛声尖锐刺耳!苏晚只觉得肩头一凉,半边嫁衣被硬生生撕裂,
露出里面素白的中衣。寒风瞬间舔舐上**的肌肤,激起一片战栗。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萧绝将那半片撕裂的、绣着金凤的红绸随手扔在雪地上,如同丢弃一件肮脏的垃圾。
“滚去西偏院。”他转身,背影决绝,只留下冰冷无情的命令,“别污了本王的眼。
”王府的管家,一个面团似的中年人,脸上堆着虚假的恭敬,眼底却全是鄙夷。“王妃,
请吧。”他侧身,指向一条幽暗、积满冰雪的小径。苏晚挺直脊背,
忽略周围无数道或怜悯、或嘲讽、或好奇的目光。她拢紧破碎的嫁衣,遮住那片刺目的白,
赤着脚踩上冰冷的雪地。每一步,都像踏在刀尖上。寒气从脚底直窜心口。经过萧绝身侧时,
他腰间垂挂的物件,猝不及防地撞入她低垂的视线。那是一枚玉佩。青白玉质,
雕着半只狰狞的虎头。断口处参差不齐,显然是硬生生掰开的。苏晚的呼吸猛地一窒!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她眼前发黑。七年前那个风雪肆虐的破庙,
少年将军浑身是血,气息奄奄,剧毒侵蚀着他的神智。是她,
一个同样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小女孩,用冻僵的手,
从怀里掏出唯一值钱的东西——娘亲留下的双鱼玉镯,塞给路过的货郎,换来了救命的药。
少年昏迷前,艰难地掰开随身携带的虎符玉佩,将一半塞进她手里。
“小丫头……拿着……日后……报……”风雪吞没了他的承诺。后来,
为了给病重的弟弟换药,她流着泪把那半块残玉当掉了。当票被她小心地藏在弟弟的襁褓里。
此刻,那失落的半块虎符,就悬在萧绝腰间。他就是当年那个濒死的少年将军!
一股酸涩的热流猛地冲上眼眶,又被她死死压回去。不能认。弟弟还在继母手里。
她只是尚书府一个无人在意的棋子,是顶替嫡姐的“赝品”。暴露身份,
只会让弟弟陷入更危险的境地。她攥紧了袖中仅存的另半块残玉,冰凉的玉硌着掌心,
带来一丝微不足道的清醒。她垂下眼,更深地埋下头,赤足踏着积雪,
一步步走向王府最偏僻、最荒凉的角落。西偏院。名字好听罢了。
推开吱呀作响、快要散架的院门,一股浓重的霉味和灰尘气息扑面而来。所谓的院子,
不过是一圈破败的矮墙围着几间摇摇欲坠的厢房。积雪覆盖着枯草,
寒风在空荡的院子里打着旋,发出呜呜的悲鸣。
领路的婆子不耐烦地一指最角落那间堆满杂物的屋子:“喏,就这儿。王妃今晚将就着吧。
”语气里的敷衍和轻慢,毫不掩饰。婆子走了。留下苏晚一个人,站在死寂的院子里。
寒意无孔不入。破碎的嫁衣根本挡不住风。她推开那扇歪斜的木门。里面更糟。
一股浓重的柴草和尘土混合的气味。蛛网挂在房梁角落,
地上散落着劈了一半的木柴和一些破烂农具。窗户纸破了大洞,冷风呼呼地往里灌。
角落里堆着些潮湿发霉的稻草,大概就是“床”了。没有炭盆,没有热水,
甚至没有一盏油灯。这就是她的“洞房”。苏晚走到那堆稻草边,慢慢坐下。
身体早已冻得麻木,只有心口那半块残玉贴着皮肤的地方,
还残留着一丝微弱的、属于过去的暖意。她蜷缩起来,把脸埋在膝盖里。忍了一路的泪水,
终于无声地滚落,砸在冰冷的稻草上,瞬间凝结成冰珠。弟弟……娘亲……她死死咬住下唇,
直到尝到一丝血腥味。“阿姐会活下去……”她在心底无声地嘶喊,
“带着你……一起活下去……”夜色,像浓稠的墨汁,彻底淹没了这方被遗弃的角落。
2寒意如同跗骨之蛆,从四面八方钻进骨头缝里。苏晚蜷缩在冰冷潮湿的稻草堆上,
单薄的素衣根本抵挡不住柴房里刺骨的阴冷。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白雾,
肺腑里像塞满了冰碴子。意识在寒冷和高热的拉锯中渐渐模糊。额头滚烫,脸颊却冰凉。
身体深处一阵阵地发冷,又一阵阵地燥热。她把自己蜷得更紧,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
迷迷糊糊间,她下意识地摸向胸口。隔着薄薄的衣料,那半块残玉冰冷的棱角硌着掌心,
带来一丝奇异的慰藉。指尖摩挲着那粗糙的断口,七年前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猝不及防地撞进混乱的脑海。也是这么冷。破庙的屋顶漏着风,雪花打着旋飘进来。
她刚埋葬了病饿而死的娘亲,自己也发着高烧,浑身滚烫,却冷得瑟瑟发抖,
缩在神龛下仅剩的一点干草堆里,等着死亡的降临。然后,她听见了沉重的、拖沓的脚步声,
还有浓重的血腥气。一个高大的身影踉跄着扑倒在破庙门口。借着雪地微弱的光,
她看见那人穿着残破染血的盔甲,脸上糊满了血污和冰霜,嘴唇是骇人的青紫色。他蜷缩着,
身体剧烈地抽搐,喉咙里发出嗬嗬的痛苦嘶声,像一头濒死的猛兽。是剧毒发作。
恐惧让她想逃,可脚步却像钉在地上。少年痛苦挣扎的模样,让她想起了自己病逝的娘亲。
那是一种被绝望吞噬的孤寂。她不知哪来的力气,跌跌撞撞爬过去。靠近了,
才发现他腰间挂着一块奇特的玉佩,半只虎头,狰狞又威严。他滚烫的手死死攥着一把短匕,
眼神涣散,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只剩下野兽般的痛苦和警惕。“别……怕……”她哆嗦着,
声音细弱蚊蚋,伸出冰冷的小手,试图去碰他滚烫的额头,
“我……我帮你……”他猛地一颤,涣散的目光骤然聚焦在她脸上,带着凌厉的杀意。
短匕无意识地抬起。苏晚吓得闭紧了眼,却没有后退。也许是她的颤抖,
也许是她眼底纯粹的恐惧和一丝笨拙的善意,少年紧绷的身体微微松懈下来,
那骇人的杀意如潮水般退去。他痛苦地闷哼一声,彻底失去了意识,但那只握着断玉的手,
却下意识地伸向她,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浮木。她看到了他手臂上狰狞的伤口,
黑紫色的毒血正汩汩渗出,散发着不祥的气息。破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药,没有食物,
只有刺骨的寒风。她急得团团转。
目光落在自己唯一还算值钱的东西上——手腕上那只娘亲留下的、成色普通的双鱼玉镯。
那是娘亲临终前塞给她的,让她“换条活路”。她看看地上气息微弱的少年将军,
又看看手腕上的镯子。小小的脸上满是挣扎。最终,她猛地一咬牙,用力将镯子褪了下来。
“等我!”她对着昏迷的少年喊了一声,也不知他能否听见。然后攥紧冰凉的玉镯,
一头冲进了漫天风雪里。寒风像刀子割在脸上。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厚厚的积雪里跋涉,
小小的身体被风吹得摇摇欲坠。不知摔了多少跤,浑身湿透冰冷,
终于看到远处有微弱的灯火——一个在风雪中艰难前行的货郎担子。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跑过去,将玉镯塞给惊愕的货郎,
语无伦次地哀求:“药……救命的药……求求你……”货郎看了看玉镯,
又看了看冻得嘴唇发紫、浑身狼狈的小女孩,终究叹了口气,
从担子里翻出几个粗瓷瓶和一小包药粉塞给她。“快回去吧,小丫头,这风雪要人命!
”她紧紧抱着那些药,像抱着稀世珍宝,跌跌撞撞地往回跑。回到破庙,
少年将军的气息更微弱了,浑身滚烫得吓人。她手忙脚乱地照着货郎说的法子,
笨拙地给他清洗伤口,敷上药粉。又把仅有的几颗药丸,费力地撬开他紧咬的牙关,
一点点喂进去。做完这一切,她已经累得虚脱,靠着冰冷的墙壁滑坐在地,冷得蜷成一团。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觉自己的手腕被一只滚烫的大手抓住。她惊惶地睁开眼。
少年将军不知何时醒了,虽然依旧虚弱,但眼神已恢复了几分清明。他看着她,
又看看自己手臂上被简单包扎过的伤口,再看看她空空的手腕。他沉默着,
眼底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最终,他艰难地抬手,解下腰间那枚雕刻着半只虎头的玉佩。
然后用尽力气,猛地将玉佩掰成两半!清脆的玉碎声在寂静的破庙里格外清晰。
他把其中一半,带着温热体温的断玉,塞进她冻僵的小手里。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重。“小丫头……拿着这个……”他喘了口气,
深邃的眼睛紧紧锁着她,
……我萧绝……必报此恩……”“萧绝……”苏晚在混沌的高热中无意识地呢喃着这个名字,
滚烫的泪水滑落眼角,瞬间变得冰凉。就在这时,柴房那扇破败的门被哐当一声踹开!
凛冽的寒风裹着雪粒子猛地灌进来,瞬间冲散了苏晚脑海中那点残存的温暖幻象,
让她狠狠打了个寒颤,神智被强行拽回冰冷刺骨的现实。
一个穿着王府侍卫服色的高大身影堵在门口,满脸的不耐烦和轻蔑。
他手里抱着一团灰扑扑的、明显是旧衣物的东西。
侍卫的目光像打量垃圾一样扫过蜷缩在稻草堆上、瑟瑟发抖的苏晚,嘴角撇了撇,
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他手臂一扬,那团旧衣物像丢垃圾一样,
劈头盖脸地朝着苏晚砸了过去!粗糙的麻布衣料带着冰冷的寒气,
重重砸在苏晚的脸上、身上。
一股淡淡的、属于另一个女子的脂粉香气混杂着樟脑味儿弥漫开来。“王爷吩咐了,
”侍卫的声音冰冷生硬,如同这柴房里的空气,“王妃身份‘尊贵’,
府中暂时没有新裁的冬衣。这是大**——哦不,是原先那位准王妃留在府里的旧衣,
还没穿过几次。王爷说……”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嘴角勾起一个恶劣的弧度,一字一句,
清晰地钉入苏晚的耳中:“您这样的,只配用别人不要的东西!”说完,
侍卫看也不看她的反应,像完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差事,转身就走。哐当一声,
破门再次被关上,隔绝了外面微弱的光线,也隔绝了最后一点虚假的体面。
柴房里重新陷入昏暗和死寂。只有那团被丢弃的、属于“准王妃”苏玉瑶的旧衣,
像一块肮脏的破布,散落在冰冷的稻草上,散发着无声的、极致的羞辱。苏晚僵硬地坐着,
脸上被衣料砸过的地方一片冰凉。高烧让她的视线有些模糊,但侍卫那充满恶意的话语,
却像淬了毒的冰锥,狠狠扎进她的心脏。她慢慢地、慢慢地伸出手,
指尖触碰到那件灰扑扑的旧衣。麻布的质感粗糙冰冷,上面残留的、属于另一个女子的气息,
让她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只配……用别人不要的东西……是啊,在所有人眼里,
她苏晚,就是一个顶替了别人位置的赝品,
一个可以被随意践踏、用别人丢弃的垃圾打发的物件。滚烫的泪水在眼眶里疯狂打转,
却被她死死咬住嘴唇,硬生生逼了回去。不能哭。眼泪在这里是最无用的东西,
只会让看笑话的人更得意。她颤抖着手,没有去碰那件衣服,
而是再次紧紧攥住了胸口衣襟下的那半块残玉。冰凉的玉硌着掌心,带来一阵尖锐的痛楚,
却也奇异地让她混乱灼热的头脑清醒了一瞬。
萧绝……当年那个承诺必报此恩的少年将军……如今,
却成了将这份羞辱亲手砸在她脸上的人。心底某个角落,传来细微的、碎裂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东西,彻底凉透了。她闭上眼,将脸深深埋进冰冷的膝盖,
蜷缩的身体在稻草堆里微微颤抖,像一片在寒风中即将凋零的枯叶。
柴房里只剩下她压抑的、带着病痛灼热的喘息,和窗外永无止境的、呜咽的风雪声。
3寒风卷着碎雪扑进窗棂。苏晚搓了搓冻得发紫的手,哈出一口微弱白气。
偏院的炭盆早熄了,只剩死灰。她刚把弟弟的药小心包好藏进枕下,院门就被粗暴地推开。
柳如烟裹着雪狐裘,像一团柔暖的云飘进来。身后跟着的侍女趾高气扬,
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药。“王妃姐姐,”柳如烟声音甜得发腻,眼底却冰凉,
“王爷说这参汤最是滋补,特意让我送来,给姐姐暖暖身子。”她莲步轻移,
裙裾扫过冰冷的地面。苏晚垂眼,起身行礼:“多谢柳姑娘,不敢劳烦。”话音未落,
柳如烟脚下一个“不稳”,惊呼着朝苏晚倒来。那碗滚烫的药汁,
直直泼向苏晚伸出欲扶的手背和半边脸颊!“啊!”皮肉灼烧的剧痛让苏晚瞬间白了脸,
踉跄后退。手背上立刻燎起一片骇人的红泡。滚烫的药汁顺着她的下颌滴落,
洇湿了单薄的旧衣。柳如烟被侍女稳稳扶住,毫发无伤。她掩着唇,
泫然欲泣:“姐姐怎么如此不小心?这汤药可珍贵了……”眼底却闪过一丝快意的恶毒。
就在这时,沉重的脚步声踏碎了偏院的死寂。萧绝高大的身影堵在门口,
玄色大氅上还沾着未化的雪。他一眼就看见柳如烟“受惊”的模样和苏晚狼狈的烫伤。
“怎么回事?”他的声音比屋外的寒风更冷。柳如烟立刻倚靠过去,声音带了哭腔:“王爷,
都怪我不好……想给王妃姐姐送碗热汤,谁知姐姐像是嫌弃,
竟失手打翻了……”萧绝的目光像淬了冰的刀子,狠狠剐在苏晚身上。
那目光里没有丝毫温度,只有全然的厌弃和怀疑。他几步上前,
铁钳般的手猛地攫住苏晚的下巴,迫使她抬起头。剧痛让苏晚眼前发黑,
被迫迎上他暴戾的视线。“烟儿一片好心,你这贱婢也敢糟践?”他手指用力,
几乎要捏碎她的骨头。苏晚能清晰地看到他眼中翻涌的怒火,那怒火只为另一个女人燃烧。
“本王警告你,”他每一个字都像冰锥,狠狠凿进她耳中,“烟儿若少一根头发,
本王就剥了你的皮!”下巴上的剧痛远不及心口的万分之一。苏晚疼得浑身发颤,
却死死咬住下唇,不让一丝呜咽溢出。就在这屈辱的瞬间,
她被迫抬起的视线无意间扫过柳如烟抬起抚鬓的手腕。一只莹润剔透的白玉双鱼镯,
松松地套在那截皓腕上。苏晚的瞳孔骤然紧缩!那镯子的纹路,
那鱼儿衔尾的弧度……与她七年前为了给弟弟抓药,
咬牙典当掉的那只娘亲唯一的遗物——一模一样!寒意瞬间爬满脊背,比烫伤更刺骨。
她如坠冰窟。萧绝嫌恶地甩开她,仿佛扔掉什么脏东西。苏晚重重跌倒在地,
手背的烫伤蹭在冰冷粗粝的地面上,又是一阵钻心的疼。“把这院子看好,
别让她再冲撞了烟儿!”萧绝丢下冰冷的命令,拥着泫然欲泣的柳如烟,头也不回地离去。
侍女们鄙夷的目光像针,密密地扎在苏晚身上。沉重的院门再次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一切。
苏晚蜷缩在冰冷的地上,很久很久。直到手背的灼痛变得麻木,
直到冻僵的身体找回一丝知觉。脸颊上被烫到的地方**辣地疼,寒风一吹,
像无数小刀在割。她挣扎着爬起来,一步一步挪到破旧的铜盆边。里面结着一层薄冰。
她咬紧牙关,颤抖着将剧痛的手浸入刺骨的冰水里。激痛让她眼前阵阵发黑,
冷汗浸透了里衣。她需要这冰冷来清醒。水波晃动,映出她苍白狼狈的脸,
也映出方才柳如烟腕间那只刺目的玉镯。娘亲临死前塞给她的镯子。
“晚儿……收好……将来……”娘亲虚弱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为了救弟弟的命,
她把它当给了城南那家挂着“恒”字招牌的老当铺。当票上,
掌柜亲手写下的日期是——癸酉年冬月初七。那一天,也是她在破庙雪地里,
用自己单薄的身体暖着一个濒死少年,割开手腕喂他鲜血的日子。
镯子怎么会到了柳如烟手上?寒意从浸在冰水里的手,一直蔓延到心底最深处,
冻得她五脏六腑都缩紧。她猛地抽回手,带起一片冰凉的水花。踉跄着扑到墙角,
颤抖着从墙砖的缝隙里,抠出那半块温热的残玉。紧紧攥在掌心。那粗糙的断口硌着皮肉,
带来一丝微弱却真实的痛感。她看着玉,又仿佛透过玉,看到那个雪夜少年模糊的眉眼。
再想到方才萧绝那恨不得生啖她血肉的暴怒眼神。指尖深深掐进残玉的边缘,
几乎要嵌进肉里。不能说。她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了铁锈般的血腥味。
眼底翻涌的巨浪被硬生生压回一片死寂的深潭。寒风呜咽着,卷起地上的残雪,
拍打着破败的窗纸。4雪是半夜下疯的。狂风卷着冰粒子砸在窗棂上。苏晚缩在柴房草堆里,
裹紧那床薄得透光的旧棉被。寒气顺着骨头缝往里钻,冻得她牙齿打颤。
弟弟阿瑜的脸在黑暗里浮起来,惨白,嘴唇泛着青紫。药,得尽快凑够买药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