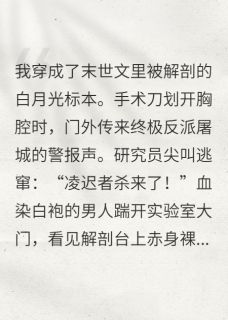
基地最高层,曾经象征着权力的将军套房,如今更像一个功能混乱的缝合怪。客厅的残骸尚未清理干净,断壁残垣间弥漫着尘埃和淡淡的硝烟味。而在套房西翼,一扇厚重的防辐射合金门隔绝了外界的混乱。门上,用略显生涩的笔触挂着一块崭新的木牌,上面刻着几个字:**安宁诊疗中心**。
门内,是另一个世界。
光线是经过特殊过滤的、柔和的暖白色,均匀地洒落。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消毒水味,但更浓郁的是各种草药混合的、令人心安的清香。墙壁被粉刷成柔和的米白色,上面甚至挂着几幅色彩宁静的风景画复制品——绿意盎然的森林,波光粼粼的湖泊,与窗外的末世废土形成刺眼对比。
几排简易但整洁的病床排列着,上面躺着形形**的伤患。有缺胳膊断腿、伤口狰狞的战士,有因为辐射病而皮肤溃烂、痛苦**的老人,也有只是受了惊吓、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孩子。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细条纹病号服(和某人同款)的“护士”和“护工”们安静地穿梭其间。他们的动作或许不够专业,眼神也带着末世生存者特有的警惕,但动作都尽可能地轻柔,传递药品、更换绷带、低声安抚。一个角落里,甚至用废弃集装箱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药房,里面飘出熬煮草药的苦涩香气。
这里没有高科技的医疗设备,只有最基础的药品、绷带、草药和一双双带着笨拙却真挚关怀的手。
诊疗中心的“院长”,此刻正站在一张病床前。
阿夜。
他依旧穿着那身标志性的、略大的蓝色病号服,外面罩了一件干净的白色医生袍,袖口挽起,露出一截清瘦的手腕。湿漉漉的黑发被仔细地梳理过,服帖地垂在额前,遮住了一部分过于苍白的肤色。几天前那场精神争夺战消耗巨大,让他看起来有些单薄,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像被泉水洗过的黑曜石,里面盛满了专注和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
他微微弯着腰,正小心翼翼地为一个断了腿的年轻战士拆解腿上脏污的旧绷带。那战士腿上血肉模糊的伤口深可见骨,边缘已经有些发炎肿胀,散发着不太好闻的气味。阿夜的动作却异常稳定和轻柔,仿佛在对待一件稀世珍宝。他先用沾着温和消毒药水的棉球,一点点软化粘连在皮肉上的绷带纤维,再用精巧的小镊子,一丝丝地剥离。每当战士因为疼痛而肌肉紧绷、闷哼出声时,阿夜的动作就会立刻停下,抬起眼,用那双清澈温和的眼睛看着对方,低声说:“忍一忍,马上就好。”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
拆掉旧绷带,露出下面红肿流脓的伤口。阿夜仔细地用生理盐水冲洗掉脓血,动作轻柔得如同羽毛拂过。然后他打开旁边一个散发着清凉草药气息的小陶罐,用干净的竹片挑起里面碧绿色的药膏,均匀地涂抹在伤口周围。药膏接触皮肤,带来一阵舒适的凉意,战士紧皱的眉头明显舒展了一些。
“这个药膏每天换一次,”阿夜一边仔细地缠上干净的新绷带,一边轻声嘱咐,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战士耳中,“伤口不能碰水,也别用力。过两天肿消了,我帮你把碎骨复位。”
“谢…谢谢您,陆医生。”年轻的战士声音有些哽咽,看着自己腿上被处理得干净清爽的伤处,又看看眼前这个气质干净温和得不似末世中人的年轻“医生”,眼神里充满了感激和一种难以言喻的信赖。
阿夜只是微微弯了弯嘴角,算是回应。他直起身,目光扫过诊疗室内一张张或痛苦、或麻木、或带着微弱希冀的脸。当他看到角落里那个因为辐射病而痛苦蜷缩的老人时,眉头几不可查地蹙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清晰的痛楚和不忍。他快步走过去,蹲下身,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小包用干净油纸包着的药粉,低声和旁边一个护工交代着什么,又亲自喂老人喝了几口水。
整个诊疗室安静而有序,只有低低的交谈声、偶尔的**和药瓶碰撞的轻响。一种久违的、属于“秩序”和“希望”的微光,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艰难地维系着。
突然!
诊疗中心那扇厚重的合金大门,被人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从外面猛地推开!
“哐当——!”
巨大的声响瞬间打破了室内的宁静!门板重重撞在墙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回音!
所有病床上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一哆嗦!孩子们惊恐地缩进被子里,伤患们下意识地绷紧了身体,护工们警惕地握紧了手边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扫帚、药瓶、甚至是板凳。
一股浓烈的、如同刚从尸山血海中跋涉而出的血腥味、硝烟味和浓重的铁锈气息,如同实质的潮水般汹涌而入!瞬间冲淡了室内草药的清香,带来一种冰冷刺骨的杀伐之气。
一个高大的身影,踏着门口涌入的、带着黑土尘埃的光线,堵在了门口。
是陆烬。主人格。凌迟者。
他依旧穿着那身标志性的破烂染血白袍,袍角甚至还在往下滴落着粘稠的、颜色暗沉的液体。黑发凌乱,几缕被汗水或血污黏在棱角分明的脸颊上。脸上、脖颈、**的手臂上,溅满了新鲜的、甚至有些还冒着热气的血点,如同刚完成一场血腥的祭祀。他周身散发着一种刚刚高强度杀戮过后的余热,像一座行走的熔炉,混合着硝烟和血腥的蒸汽几乎扭曲了周围的空气。一双眼睛,不再是之前那种燃烧的赤红,而是一种沉凝的、如同万年寒冰般的深黑,里面沉淀着化不开的暴戾和一种近乎虚无的冰冷。
他右手,随意地拎着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人头。
一个须发虬结、面目狰狞、双眼圆瞪、充满了惊骇和凝固痛苦的男人头颅。脖颈的断口参差不齐,显然是被硬生生撕扯下来的,此刻还在缓慢地滴落着粘稠的血液和某种组织液,在地板上汇聚成一小滩令人作呕的暗红。头颅的额头上,有一个清晰的、被某种高温武器灼烧出的狼头烙印——正是之前另一个敌对势力的首领!
陆烬像是丢垃圾一样,随手将那颗还在滴血的头颅扔在诊疗室门口光洁的地板上。
“咚。”
沉闷的声响如同丧钟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头颅咕噜噜滚了几圈,沾满了灰尘和血污,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正好对着诊疗室内一张张惊恐万状的脸。
“啊——!!!”尖叫声瞬间撕裂了室内的平静!一个离门口最近的、正在接受包扎的小女孩吓得魂飞魄散,爆发出凄厉至极的哭嚎!
整个诊疗室瞬间乱成一团!惊恐的尖叫、痛苦的**、慌乱的碰撞声交织在一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那点安宁和秩序,在这颗滴血的头颅和门口那尊煞神带来的恐怖冲击下,如同脆弱的肥皂泡,瞬间破灭!
阿夜猛地转过身!
当他看清门口景象的刹那,脸上那种专注、温和的神情瞬间冻结、碎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愤怒和冰冷的痛楚!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如同被投入了寒冰,瞬间冻结,随即燃起两簇足以焚毁一切的怒火!
“你!”阿夜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微微颤抖,带着少年特有的尖利,他指着门口那颗狰狞的头颅,又指向如同杀戮化身般的陆烬,“滚出去!”
他小小的身体因为愤怒而绷紧,像一张拉满的弓。一股冰冷而尖锐的精神力量不受控制地在他周身凝聚,诊疗室里的温度似乎都骤然降低了几度。他挡在病床前,如同护崽的母兽,将那些惊恐的伤患护在身后,毫不退缩地瞪着门口那个满身血腥的“自己”。
陆烬那双沉淀着无边暴戾和冰冷的深黑色眼眸,缓缓抬起,落在了阿夜身上。他的目光扫过阿夜身上那件刺眼的白色医生袍,扫过诊疗室里那些惊惶无助的面孔,最后,定格在阿夜因为愤怒而微微涨红的脸上。
一丝极其细微的、近乎讥诮的弧度,在他染血的嘴角缓缓勾起。那笑容冰冷刺骨,没有任何温度。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微微侧开身体,让开了堵住的大门。然后,他抬起脚——
“啪叽。”
那只沾满泥泞和血污、散发着浓重腥气的军靴,精准地、毫不留情地踩在了那颗滚落脚边、还在微微抽搐的狼头首领的头颅上!
头骨碎裂的沉闷声响,混合着某种粘稠液体被挤压的声音,清晰地传遍了死寂的诊疗室。
“呃……”压抑的呕吐声从几个伤患喉咙里发出。
陆烬仿佛只是碾死了一只碍眼的虫子。他甚至没有再看阿夜一眼,也没有再看诊疗室里地狱般的景象。他拖着那把从不离身的巨大合金砍刀——刀锋上还挂着新鲜的血肉碎末——转过身,高大的身影融入门外的光影和尘埃之中,只留下一个被浓重血腥味和死亡气息笼罩的门口,以及地板上那颗被彻底踩碎、面目全非的头颅。
阿夜死死地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了血腥味。他小小的身体因为极致的愤怒和一种深沉的无力感而剧烈地颤抖着。他猛地闭上眼睛,再睁开时,眼中的怒火被强行压下,只剩下深不见底的冰冷和一片狼藉的诊疗室。
他深吸一口气,不再看门口那颗恐怖的头颅。他蹲下身,从旁边的医疗推车上拿起一卷干净的绷带和消毒水,走向那个被吓得失声痛哭的小女孩。他的动作依旧稳定,声音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和疲惫:
“别怕,没事了。”他一边轻柔地用沾了消毒水的棉球擦拭小女孩脸上被溅到的血点,一边对旁边一个脸色惨白的护工吩咐,声音冷得像冰,“把门口……清理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