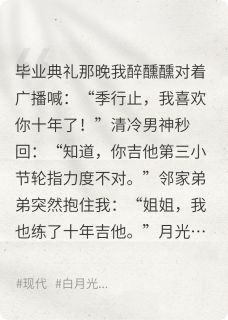
毕业典礼那晚我醉醺醺对着广播喊:“季行止,我喜欢你十年了!”
清冷男神秒回:“知道,你吉他第三小节轮指力度不对。”
邻家弟弟突然抱住我:“姐姐,我也练了十年吉他。”
月光下两人同时掏出拨片——季行止那块刻着“小哭包”,李方昭的刻着“胆小鬼”。
便利店的冷光灯里,季行止像座冰雕:“债清了,路你自己走。”
可当我转身时,他攥住我手腕的力道几乎捏碎骨头:“陈温郁,十年利息…你打算怎么付?”
当代女大学生三大美德:清醒,自律,不碰爱情。
我,陈温郁,自认前两项修炼得炉火纯青,偏偏在最后一项上,栽了个结结实实的大跟头,一栽就是十年。栽在了一个叫季行止的人身上,摔得粉身碎骨,还甘之如饴。
季行止。光是默念这个名字,舌尖都像含了一颗微凉的薄荷糖,清冽又带着一丝隐秘的回甘。
他是我们这届公认的神话。不是那种咋咋呼呼、光芒万丈的神,更像图书馆深处最安静角落里,被时光打磨得温润又疏离的一尊玉像。年少时便以“别人家孩子”的终极形态闻名遐迩,成绩单漂亮得如同精心伪造的艺术品,一张脸更是造物主偏心眼的铁证。后来不知为何,他像投入深潭的石子,从喧嚣的中心沉了下去,敛尽光华,只在每次年级大榜的顶端,用那种令人绝望的分数昭示着他的存在。
我认识他,或者说,单方面地、隐秘地关注他,也正好十年。从我初一那个懵懂又自卑、淹没在人群里毫不起眼的“陈小郁”,到现在勉强混了个“校园女神”虚名、走在路上也能收获几道回头率的“陈温郁”。十年时光,足够把一只丑小鸭的羽毛染上些许光华,却没能磨平我看向他时,心底那份扎根太深的怯懦。
他太远了。远得像挂在天边的一轮冷月,清辉洒落,却触手冰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