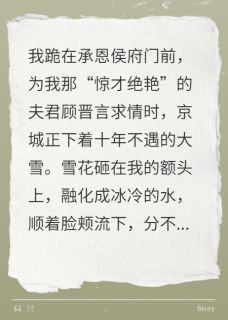
我跪在承恩侯府门前,为我那“惊才绝艳”的夫君顾晋言求情时,
京城正下着十年不遇的大雪。雪花砸在我的额头上,融化成冰冷的水,顺着脸颊流下,
分不清是雪水还是泪水,我磕了九百九十九个头,额头一片血肉模糊,
只为求承恩侯高抬贵手,放因言获罪的顾晋言一条生路。三天三夜,我水米未进,
直到最后彻底晕厥过去。1醒来时,我躺在冰冷的偏院卧房里,只有一个老婆子守着我。
我哑着嗓子问:“夫君呢?夫君回来了吗?
”老婆子眼神躲闪:“老爷……回来了”我心中一喜,挣扎着要起来,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我的苦,没白受。“姑娘,
您别动”老婆子按住我“老爷……正在前厅陪客”我愣住了,陪客?
他刚从大理寺的牢里出来,九死一生,不先来见我这个为他奔走的妻子,而去陪客?这时,
我的贴身丫鬟小桃哭着跑了进来:“**!您别管了!姑爷他……他根本没心!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小桃哽咽着说:“姑爷是回来了,
可不是承恩侯放的,是……是二**,她去求了太子殿下,姑爷一出狱,
连看都没看雪地里晕倒的您一眼,就直接奔去了咱们府上,抱着二**说,‘画儿,
我便知道,这世上只有你懂我,只有你肯为我不顾一切’”轰的一声,
我脑子里最后一根紧绷的弦,断了。我叫温书,是丞相府的大女儿,我妹妹叫温画,
是丞相府最受宠的二女儿。顾晋言原本的婚约对象,是温画。可那时顾家家道中落,
顾晋言只是个空有才名的穷书生,温画当着爹娘的面哭闹,说她才不要嫁过去吃苦。
母亲抱着她,心疼得直掉眼泪,然后,她转身对我说:“书儿,你向来懂事,
**妹金枝玉叶,受不得委屈,这门亲事,你替了吧”父亲也说:“温书,
顾晋言此子非池中之物,你嫁过去,好生辅佐他,将来有你的好日子”我自小就不受宠,
因为我性子沉闷,不如妹妹活泼讨喜,我默默地点了头,其实我心里,是有一丝窃喜的,
我读过顾晋言的诗,敬佩他的才华,我想,只要我真心待他,总能捂热他的心。于是,
我带着我娘留下的丰厚嫁妆,嫁入了顾家。我为他操持家务,为他洗手作羹汤,
他要银钱打点同僚,我便拿出我的嫁妆铺子,他要举办文会,结交名士,
我便拿出我的私房钱为他操办。三年,我将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只为换他一点点的温情。
可他的眼里,从来没有我,他叫我“夫人”却从不叫我的名字,他对我永远是客气而疏离的。
而我的好妹妹温画,却时常来我们府上,她和顾晋言谈诗词歌赋,谈风花雪月,他们是知己,
是知音,而我,只是一个操持后宅,浑身沾满油烟味的俗气妇人。我一直以为,
只要我做得够好,他总会看到的。直到我跪在雪地里,用我的命去换他的命,而他出来后,
却奔向了另一个女人。那一刻,我彻底明白了。不是我做得不够好,而是他心里,
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我所有的付出,不过是一场自我感动的笑话。高烧退去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小桃把我的嫁妆单子拿来。我看着那厚厚的一沓纸,
上面记录着我娘留给我的每一个铺子、每一亩良田,这些年,为了顾晋言,
已经变卖了近三成。我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温书啊温书,你真是天底下第一号的傻子。
从那天起,我不再去前院嘘寒问暖,不再为顾晋言的饮食起居费心,
我让管家把所有账本都送到顾晋言的书房。“告诉老爷,我病了,中馈之事,
暂由他自己打理”我对管家说。顾晋言起初没在意,只当我在闹脾气,
他每日依旧和温画诗酒唱和,流连于各种文会,风光无限。可没过多久,府里就乱了套,
采买的以次充好,下人偷懒耍滑,账目一塌糊涂,顾晋言是个读书人,哪里懂这些,
他焦头烂额,终于忍不住来我院里找我。他站在门口,皱着眉,
语气带着一丝不耐:“你闹够了没有?一个妇道人家,不好好管家,像什么样子?
”我正坐在窗边看书,头也没抬:“顾大人,我只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管家,中馈之事,
本就是当家主君的责任”他愣住了,似乎没料到我会这样说话,他第一次正眼看我,
发现我穿着一身素净的衣裳,脸上未施粉黛,神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温书,
你到底想怎么样?”他语气软了些。我终于抬起眼,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顾晋言,
我们和离吧”他如遭雷击,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你疯了?我如今是朝中新贵,
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你提和离?传出去我们顾家的脸面何存?你温家的脸面又何存?
”“脸面?”我轻轻笑了一声“顾大人,你抱着我妹妹说她是你的知己时,
可曾想过我的脸面?你对我三年来的付出视而不见时,可曾想过我的脸面?
”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最后拂袖而去,撂下一句:“我绝不答应!”我不在乎。
2我开始暗中变卖剩下的嫁妆,但这一次,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
我将银钱换成金条,又托了可靠的人,在京城外买了一处清静的庄子。我的父母听闻此事,
气冲冲地赶来。母亲指着我的鼻子骂:“温书!你是不是昏了头!晋言如今前途无量,
你当上了官夫人,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妹是去求了太子,那是为了救他,
也是为了救你们整个顾家!你怎么如此不知好歹,善妒至此!
”父亲也沉着脸:“赶紧给晋言认个错,安分守己地当你的顾夫人,别再闹了,丢人现眼!
”我看着他们,只觉得无比可笑。“母亲,当初是您让我替嫁的,
您说我懂事”我平静地说“现在,我不想再懂事了,我为他付出所有,换来的是什么?
是他在雪地里对我视而不见,是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我应该大度”“我没错,所以我不认错,
和离书,他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他们被我的决绝惊呆了。顾晋言也开始慌了,他发现,
没有我打理后宅,他根本无法专心于朝堂之事,他开始尝试讨好我,给我买名贵的首饰,
稀有的字画。可这些东西,都被我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他开始频繁地来我的院子,
笨拙地想与我说话,回忆我们刚成婚时的点滴。可他不知道,他回忆里的那些事,
主角都是他自己和我妹妹,他甚至记不清,为他熬夜缝制官服的人是我,而不是温画。那天,
温画又来了,她梨花带雨地站在我面前:“姐姐,你不要怪晋言哥哥,都是我的错,
如果你实在容不下我,我以后再也不见他了”换做以前,我或许会心软。但现在,
我只觉得恶心。我看着她,冷冷地说:“第一,我不是你一母同胞的姐姐,别叫我姐姐,
我担不起。第二,你们见不见面,与我无关。第三,
请你立刻离开我的院子”顾晋言终于意识到,我是铁了心要走。
他开始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眼神看我,他说:“书儿,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前是我不好,
是我忽略了你,以后我改,我一定好好待你”他甚至为了留住我,主动疏远了温画,
拒绝了我父母的探望。可太迟了。心死过一次的人,是暖不回来的。
我拿出了我早就准备好的东西——一本账册。那上面,详细记录了这些年,他为了往上爬,
收受的每一笔“炭敬”、“冰敬”还有各种由头的银钱,证据确凿。
我把它放在他面前:“顾大人,签了这份和离书,这本账册,我会烧掉,从此我们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若是不签……”我没有说下去,但他懂了。他看着我,
眼睛里满是震惊、痛苦和不可置信,他大概从未想过,那个一直默默无闻,
被他视为摆设的妻子,竟有如此手段。他颤抖着手,拿起了笔。签下名字的那一刻,
他双眼通红,声音嘶哑:“温书,你……可曾爱过我?”我看着他,
想起了三年前那个满心欢喜,以为能用真心换真情的自己。我摇了摇头,平静地说:“不曾,
嫁给你,只是父母之命”我看到他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我知道我撒了谎,可那又如何?
爱过,然后呢?不过是让他多一个伤害我的理由,多一份自以为是的筹码。
我带着小桃和我的金条,离开了顾家,我没有回丞相府,那个地方,
从我娘去世的那天早已不是我的家。3我住进了城外的庄子。庄子很美,有山有水,
有花有田,我用手里的钱,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坊,专门印一些女子也能读懂的杂记和话本,
生意不好不坏,但足够我衣食无忧。我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
再也不用为了讨好谁而委屈自己。后来,我听说顾晋言因为后宅不宁,又被人抓住了把柄,
在朝堂上屡屡受挫,最终被外放到了一个偏远的苦寒之地。我的妹妹温画,终究没有嫁给他,
太子殿下不知从何处听说了她的“痴情”故事,觉得她水性杨花,丞相府家风不正,
便取消了原本属意她做侧妃的念头。我的父母来庄子上找过我几次,
话里话外都是让我回去帮帮顾晋言,帮帮家里。我让庄头把他们客客气气地“请”了出去。
一个春日的午后,我坐在院子里的梨花树下,看着自己新写的话本,小桃端来了刚沏好的茶。
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微风拂过,带来阵阵花香。我忽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好日子”。
不依附于任何人,不执着于任何情,我的喜怒哀乐,都由我自己决定。日子一晃,便是两年。
我的书坊,从最初只印些我自己写着解闷的话本,慢慢地也开始收一些落魄书生的稿子,
我给的价钱公道,从不克扣,渐渐地竟也闯出了些名气,
庄子上的妇人闲时会来书坊帮我装订,我按件计酬,她们有了私房钱,脸上的笑也多了。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静地过下去,直到一个男人的出现。他第一次来书坊时,
穿着一身半旧的青布长衫,身形高大,眉眼间却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惫,
他不像别的客人那样挑拣畅销的话本,而是在书架前站了很久,
最后拿起一本我写的《女医手记》。那是我写得最用心、也卖得最差的一本。
“这本书记述的药理,颇有见地,只是这几处,似乎与古法相悖”他走到柜台前,声音低沉,
指着书中的几页。我有些意外,便与他探讨了几句,我发现他见识广博,不仅懂医理,
对行军布阵、农桑水利也颇有了解,我们聊了半个时辰,他才付钱告辞。后来,
他便成了书坊的常客,我渐渐知道,他叫沈七,是邻庄的一个佃户,曾在外当过几年兵,
受了伤才退下来,他话不多,但每次来,都会和我聊上几句,我们聊书,聊庄稼,聊天气,
就是不聊过去。和他相处,很轻松,我不用揣摩他的心意,也不用担心说错话。这天,
小桃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不好了!县衙的张主簿带人来了,说我们印的书伤风败俗,
要查封书坊!”我心里一沉,张主簿是县丞的小舅子,早就眼红我书坊的生意,
几次三番派人来暗示,想入股分红,都被我拒绝了,没想到他竟用了这么个下作的由头。
我走到前头,张主簿正一脸横肉地让人搬我的书。“张主簿,我的书都在官府备过案,
何来伤风败俗一说?”我冷着脸问。“哼,有没有,得我们查过才知道!
”他色厉内荏地嚷嚷。正在这时,沈七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乱糟糟的场面,
走到张主簿面前,什么也没说,只从怀里掏出了一块不起眼的木牌,在他眼前晃了一下。
张主簿的脸瞬间就白了,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
他结结巴巴地说:“原……原来是沈……沈爷,误会,都是误会”说完,
便带着他的人屁滚尿流地跑了。我愣住了,小桃也愣住了。沈七收起木牌,
对我平静地说:“那是我以前在军中时,一位将军赠的信物,他说在京畿地界,遇上麻烦,
或可一用”他顿了顿,又说:“温掌柜,你是个有本事的女人,但世道对女子苛刻,
你若不嫌弃,日后若有小人叨扰,可遣人去邻庄寻我”我看着他坦荡的眼神,
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我郑重地对他福了一福:“多谢沈先生”他笑了笑,
露出一口白牙:“我不是什么先生,叫我沈七就好”自那以后,再没人敢来书坊找麻烦,
我和沈七的来往也多了些,他会帮我修葺漏雨的屋顶,我也会在他下工时,请他喝一碗热茶,
吃一碟点心。庄子上的人开始传闲话,小桃也旁敲侧击地问我:“**,我看那沈七人不错,
老实本分,又会疼人……”我只是笑笑,不说话。我的心早已是一片废墟,
不想再建什么楼阁了,如今这样,有书为伴,有友可交,便已足够。直到那天,
一个我以为永不会再见的人,出现在了我的庄子门口。4是外放结束,返回的顾晋言。
他比两年前憔悴了许多,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官袍,风尘仆仆,鬓角竟有了白霜,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悔恨,有痛苦,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祈求。
“书儿”他哑着嗓子叫我。我平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陌生人“顾大人,
别来无恙”我的冷淡刺痛了他,他上前一步,急切地说:“书儿,我知道错了,这两年,
我在瘴疠之地,日日夜夜都在想你,我想着你为我跪在雪地里,想着你为**持家务,
想着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是我混账,是我有眼无珠,是我负了你!
”他从怀里掏出一沓厚厚的纸:“你看,这是我为你写的诗,我为你画的像,书儿,
你跟我回去,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我发誓,这辈子我只对你一个人好,再也不见温画,
再也不理会那些俗事,我只守着你”我看着那些纸,上面确实是他的笔迹,字字句句,
情真意切,若是两年前,我看到这些,怕是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可现在,我只觉得讽刺。
“顾大人”我开口,声音没有一丝波澜“你知道吗?我庄子里的梨花,开了两次了,
书坊的账本,换了四本,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话不多,但会帮我修屋顶”我抬眼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我的生活里,早就没有你了,你的悔恨,你的深情,
都和我无关了”“不……不是的!”他激动地抓住我的手腕“书儿,你是在气我,我知道的,
你心里还有我,不然你不会跟我说这些!”他的力气很大,捏得我生疼。
“放手”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沈七不知何时站在了那里,他没穿那身佃户的衣服,
而是一身挺括的武将常服,虽然没有品阶纹样,但那股沉稳的气势,
却让顾晋言下意识地松了手。沈七走到我身边,自然地将我护在身后,
对顾晋言说:“这位大人,温掌柜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你离开”顾晋言看着沈七,
又看看我,脸上血色尽失,他惨然一笑:“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不是心如死灰,
你只是……另觅新欢了”他这话,说得极其刻薄。换做以前,我或许会为了名声而辩解。
但现在,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然后,我做了一件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的事。
我主动牵住了沈七的手。他的手掌很宽大,很粗糙,却很温暖,他似乎也愣了一下,
但很快就反握住了我的手。我看向顾晋言,清晰地说道:“是,所以,顾大人,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顾晋言踉跄着后退了两步,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
他死死地盯着我们交握的手,眼里的光,一点一点地,彻底熄灭了,最终,他转身,
失魂落魄地走了。他走后,我才松开沈七的手,有些不好意思:“抱歉,沈先生,
方才借你一用”沈七看着我,眼神深邃,他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温书,我不是佃户,
也不是普通的退伍兵,我本名沈岐,曾是羽林卫左将军,因得罪权贵,
才解甲归田”他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我方才说的,并非全是假的,我确实心悦你,
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怜悯,我喜欢看你打理书坊的样子,喜欢听你谈论书里故事的见解,
我所求的,不是让你为**持家务,而是想与你并肩,看这四季风光”他停顿了一下,
语气带着一丝紧张:“我知你受过伤,不愿再轻易信人,没关系,我可以等,
等到你庄子里的梨花再开十次,等到你的书坊开遍大江南北,温书,
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的肩上,我看着他真诚的眼眸,
那片早已荒芜的心田,仿佛有春风吹过,竟悄悄地,生出了一点绿意。我笑了,
发自内心地笑了。我没有立刻回答他。但我知道,我的结局,或许可以比想象中,
更完美一些,顾晋言的身影消失在小路的尽头,我才慢慢松开了紧绷的肩膀,
院子里一时间静得只剩下风吹过梨花树叶的沙沙声。我低头看着自己还牵着沈岐的手,
掌心的温度真实得有些烫人,我像是被惊到一般,迅速抽回了手,脸上有些发热。
“沈……将军”我下意识地用了敬称,随即又觉得不妥“沈先生,今日之事,
多谢你”他没有在意我的称呼,只是静静地看着我,那双深邃的眼睛里,
情绪比刚才更加分明,他说他心悦我,他说他可以等,这些话,像一颗颗小石子,
投进了我那早已古井无波的心湖。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只能垂下眼帘,
轻声说:“我……我的过往,想必你也听说了一些,我如今只想守着这个庄子和书坊,
过几天安生日子,情爱之事,早已不敢奢望”“这不是奢望”沈岐的声音很沉稳,
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安生的日子,和有个人在身边,并不冲突,温书,
我不会像他一样,把你当成攀附的阶梯,或是装点门面的摆设,我只是觉得,你一个人撑着,
太累了,我想帮你分担一些,哪怕只是修修屋顶,搬搬书这样的小事”我心里一颤。
这三年来,所有人都对我说,要我“懂事”要我“大度”要我“辅佐”夫君,只有他,
说我“太累了”。我抬起头,认真地看着他,他穿着一身普通的武将常服,
脸上还有风霜的痕迹,可他的眼神,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哥都要干净、坦荡。
我沉默了许久,久到小桃都有些不安地挪了挪脚步。最后,我指了指院子里的石桌,
那上面还放着我们之前喝的半壶清茶。“茶要凉了”我说“若不嫌弃,再喝一杯吧,
沈岐”我没有叫他沈将军,也没有叫他沈先生,而是叫回了他最初的名字。
沈岐的眼睛亮了一下,他咧开嘴,露出了一个爽朗的笑容,那股属于将军的威严瞬间消散,
又变回了那个会帮我修屋顶的邻庄佃户。“好”他干脆地应道。5那之后,
我们的关系似乎没什么变化,又似乎处处都变了,他还是会时常来书坊,
有时带一些山里的野味,有时只是默默地帮我把新印的书搬到架子上,我们依然聊天,
但话题里,多了一些他过去在军中的趣事,我也渐渐会说一些我写话本时的想法。
我们谁也没再提“在一起”或是“机会”这样的话,但庄子上的人看我们的眼神,
都带上了善意的笑。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里,慢慢地好起来。
直到半个月后,小桃从镇上采买回来,脸色有些不对。“**”她把我拉到内室,
压低了声音“今天镇上的悦来客栈,住进来一拨京城来的人,排场可大了,
我听见客栈的伙计偷偷议论,说是……安国公府的人”我的心猛地一沉。安国公,
当朝太后的亲弟弟,权倾朝野,而我记得,沈七说过,他当初得罪的权贵,
正是安国公的小儿子。“他们来做什么?”我问。“不清楚”小桃摇摇头,
神色担忧“但我听见他们跟掌柜的打听,说是在找一个三年前从羽林卫退下来的故人,
身高八尺,左臂上有一道旧箭伤”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这说的,
分明就是沈岐。我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我好不容易才从一个泥潭里爬出来,
过上了几天清净日子,难道又要被卷进另一个更深、更危险的漩涡里去吗?那一瞬间,
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退缩。是劝沈岐快走,走得越远越好,从此我们再无瓜葛,
我守着我的庄子,他去过他的江湖,这样,我就能保住我这来之不易的安宁。
这个念头是如此诱人,几乎要脱口而出。可紧接着,我脑海里浮现出的,
却是沈岐那双坦荡的眼睛,是他沉稳的声音,他说:“我只是觉得,你一个人撑着,
太累了”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我真的劝他走了,那我又和当初逼我替嫁的母亲,
和那个对我付出视而不见的顾晋言,有什么区别?都是在危难面前,选择牺牲别人,
保全自己。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才活成了今天的温书,我不能再变回去了。
“小桃”我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坚定“你去邻庄,告诉沈七,
就说我书坊里有一批新到的纸,请他过来帮我验验货,切记,
不要让任何人看出异样”小桃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重重地点了点头,
快步走了出去。傍晚时分,沈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我的庄子。我屏退了下人,
将小桃打听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听完后,沉默了片刻,脸上没什么意外的神色,
只是眉头微微皱起:“他们还是找来了”“是安国公的小儿子?”我问。
“嗯”他点了点头“当年在边境,他为抢军功,冒进深入,致使三千弟兄陷入重围,
我带兵将他救回,依军法上报,他被夺了军职,从此便恨上了我”我心中了然,
这确实是那些纨绔子弟做得出来的事。“那你打算怎么办?他们人多势众,
你……”我有些担心。他看着我,忽然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你怕吗?”我愣住了。
怕吗?当然怕,安国公府,那是我连仰望都够不上的存在,动一动手指头,
就能把我的庄子和书坊碾成粉末。但我看着他沉静的目光,却鬼使神差地摇了摇头。
“有你在,我不怕”我说。话说出口,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这确实是我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沈岐笑了,那笑容里,有欣慰,有暖意,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锋芒。“好”他站起身,
高大的身影在夕阳的余晖里,投下长长的影子“既然你不怕,那我们,
就去会会他们”我以为他说的“会会他们”是要提着刀冲进悦来客栈,我甚至想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