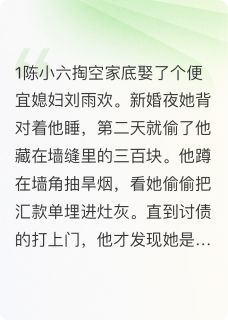
1陈小六掏空家底娶了个便宜媳妇刘雨欢。新婚夜她背对着他睡,
第二天就偷了他藏在墙缝里的三百块。他蹲在墙角抽旱烟,看她偷偷把汇款单埋进灶灰。
直到讨债的打上门,他才发现她是被拐卖的,弟弟被扣在骗子窝里当人质。
“今晚他们就带我走。”她往他手里塞了张纸条,上面写了个地址。陈小六连夜翻山报警,
带着警察端了骗婚组织的老巢。混乱中她扑过来替他挡了一刀,血染红了嫁衣。
病房里他笨拙地喂粥:“那三百块...不用还了。
”她苍白的脸突然红了:“你比我还傻...那钱早被他们收走了。
”2陈小六是被窗棂外透进来的冷光给刺醒的。他睁开眼,陌生的屋梁横在头顶,
糊着旧报纸,边角已经泛黄卷曲。身上盖着的薄被硬邦邦的,
带着一股仓促浆洗过的生涩味道。记忆迟钝地回流,像冻住的溪水一点点化开——昨天,
他成亲了。他下意识地往炕里侧摸去,入手只有一片冰凉、压得平整的空荡。人已经起了。
外间传来细微的、锅铲碰撞的声响。陈小六坐起身,粗糙的土布被面摩擦着皮肤。
他套上那件半新不旧、专门为昨天置办的靛蓝褂子,趿拉着鞋走到门边。灶膛的火光跳跃着,
映在刘雨欢单薄的脊背上。她正搅动着锅里翻滚的稀粥,动作有些生疏僵硬。
灶口堆着几根掰断的柴火,旁边,一个磕破了边的粗瓷碗里,孤零零地躺着半个煮熟的鸡蛋。
陈小六的目光在那半个鸡蛋上停顿了一瞬,
又移到墙角——那里靠墙摆着两口陪嫁过来的、刷着暗红漆的箱子,锁扣簇新。
他心里那块悬了一夜的石头,似乎往下落了落,却又被另一种更沉的东西替代。
他花光了爹娘留下的那点薄产,又向族里几个叔伯东挪西借,
才凑足了那笔对于山里人来说近乎天价的“彩礼”,四千八百块。
媒人王婆子拍着胸脯打包票:“六子,你就把心放肚子里!这姑娘,老实本分,手脚勤快,
家里遭了灾才急着找条活路,便宜!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便宜。陈小六咀嚼着这两个字,
嘴里泛起一股难言的苦味。他搓了搓脸,走到水缸边,拿起葫芦瓢舀了半瓢凉水,
咕咚咕咚灌下去。冰凉刺骨的水流一路冲到胃里,让他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分。“吃饭吧。
”他哑着嗓子说了一句,没看灶台边的人,
自顾自走到那张瘸了一条腿、用石头垫着的饭桌旁坐下。
刘雨欢端着两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过来,一碗放在他面前,一碗放在自己那边。
她始终垂着眼,浓密的睫毛像小扇子,在苍白的脸上投下两片阴影,遮住了所有的情绪。
她坐下,拿起筷子,小心翼翼地只夹面前碟子里一点咸得发苦的萝卜干。陈小六端起碗,
视线却不由自主地扫过墙角。那里有块土坯砖,被他抠松了又仔细嵌回去,
砖缝里藏着他最后的三百块钱,那是预备着开春买种粮的命根子。昨晚,
他趁着刘雨欢背对着他、呼吸似乎变得均匀绵长时,才偷偷爬起来,把钱塞了进去。
那砖缝……似乎比昨晚塞钱时,松动了那么一丝丝?陈小六的心猛地往下一沉,
握着碗沿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饭桌上一片死寂,
只有筷子偶尔碰到碗边的轻响和两人压抑的呼吸声。陈小六喝了几口稀粥,
胃里非但没暖起来,反而更空了。他放下碗,摸出别在腰带上的旱烟杆和烟袋锅。
黄铜的烟锅头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微光。他慢吞吞地捏了一小撮焦黄的烟丝,按进烟锅里,
手指有些发颤。“家里……还好?”他干巴巴地问,声音像是砂纸磨过木头。
刘雨欢的肩膀几不可察地瑟缩了一下,头垂得更低,几乎埋进碗里。过了好半晌,
才从喉咙里挤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嗯。”陈小六不再问了。他划着火柴,凑近烟锅,
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涌入肺腑,呛得他闷咳了两声,
却压不住心口那股不断翻腾、越烧越旺的焦灼和猜疑。那三百块钱的影子,
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上。日子像村口那条浑浊的小河,无声无息地淌过去。
刘雨欢确实手脚勤快,洗衣、做饭、打扫屋子,样样都做,只是沉默得像块石头。
陈小六早出晚归,扛着锄头下地,侍弄那几亩薄田,或是去后山砍柴。每次回家,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装作不经意地,用鞋尖蹭蹭墙角那块土坯砖的边缘。一次,
两次……那块砖缝的松动感,越来越明显了。心里的窟窿,也跟着越来越大。这天傍晚,
陈小六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远远看见自家那间低矮的土坯房顶上,
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又细又淡,还没升多高就被山风吹散了。他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
刘雨欢正蹲在灶膛前添柴火。跳跃的火光映着她半边脸,额角沁着细密的汗珠。
她全神贯注地盯着灶膛里燃烧的火焰,眼神空洞,仿佛灵魂都抽离了。陈小六没出声,
放轻脚步绕到屋后。他蹲在灶屋后墙那个小小的通风口下方,透过砖石的缝隙,
刚好能看到灶膛口那片光亮的区域。他屏住呼吸。灶膛里的火苗正旺,发出噼啪的轻响。
刘雨欢添完最后一把柴,站起身,左右飞快地扫视了一眼。院子里空无一人。
她迅速地从贴身的旧棉袄内兜里摸出一小片折得方方正正的纸,犹豫着,指尖微微颤抖。
她咬着下唇,盯着那跳跃的火焰看了几秒钟,仿佛在与什么无形的力量做最后的挣扎。终于,
她猛地一闭眼,手腕一抖,那片纸被她飞快地扔进了灶膛深处滚烫的余烬里。
火焰贪婪地卷上来,瞬间吞噬了那薄薄的纸片,只留下一点焦黑的边缘,转眼也化为了灰烬。
陈小六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的肉里。那是什么?汇款单?欠条?还是……别的什么?
他猛地站起来,眼前一阵发黑,血液冲上头顶,嗡嗡作响。三百块!
还有那四千八百块的彩礼钱!一个可怕的、冰冷的念头像毒蛇一样缠住了他的心:他陈小六,
怕是真的被王婆子那老虔婆,用个“便宜媳妇”给骗了个底儿掉!就在这时,
院门被人粗暴地一脚踹开!“哐当”一声巨响,腐朽的木门板狠狠撞在土墙上,
震落簌簌的灰尘。三个流里流气的汉子闯了进来,为首的是个刀疤脸,敞着怀,
露出胸口狰狞的刺青,眼神像刀子一样剐在刚惊慌失措站起来的刘雨欢身上。“哟,刘雨欢,
小日子过得挺美啊?”刀疤脸咧着嘴,露出被劣质烟草熏得焦黄的牙齿,声音粗嘎难听,
“哥几个大老远跑来喝喜酒,新娘子连杯茶都不给倒?”他身后两个跟班也嘿嘿怪笑着,
贪婪的目光在刘雨欢身上和简陋的屋子里来回扫荡。刘雨欢的脸瞬间褪尽了最后一丝血色,
身体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脊背死死抵住了冰冷的土灶台。
“你们……你们是谁?想干什么?”陈小六一个箭步从屋后冲出来,挡在刘雨欢身前,
尽管他自己心也跳得像擂鼓,但一股血性还是顶了上来。他握紧了拳头,紧紧盯着刀疤脸。
刀疤脸斜睨了他一眼,满是不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干什么?”他嗤笑一声,
伸手从裤兜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在陈小六眼前晃了晃,“找你媳妇要钱!白纸黑字,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她爹看病借的印子钱,连本带利,五千!拖到今天,利滚利,
现在是一万二了!”那张纸条像烧红的烙铁,烫得陈小六眼睛生疼。
他猛地扭头看向身后的刘雨欢。她嘴唇哆嗦着,眼睛死死盯着地面,
绝望的泪水无声地滚落下来,砸在脚下的泥土里。她整个人都在往下瘫软。“放屁!
”陈小六只觉得一股邪火直冲天灵盖,所有的憋屈、怀疑、愤怒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烧得他理智全无,“什么印子钱!你们就是骗子!合伙骗婚的骗子!”他指着刀疤脸,
手指因为激动而剧烈颤抖,“滚!给我滚出去!不然老子跟你们拼了!”“哟呵?穷横?
”刀疤脸三角眼一翻,凶光毕露,“给脸不要脸是吧?”他朝身后一歪头,“哥几个,
教教这山炮怎么做人!顺便,把这小娘们儿带走!老大说了,
南边有老板就喜欢这嫩生生的调调,能卖个好价钱抵债!”两个跟班狞笑着扑了上来。
陈小六吼了一声,抡起墙边靠着的扁担就砸了过去。混乱瞬间爆发。
扁担砸在一个混混的胳膊上,发出闷响,对方痛叫一声。但双拳难敌四手,
另一个混混从侧面狠狠一脚踹在陈小六腰眼上。剧痛让他眼前一黑,踉跄着倒地,
扁担脱手飞了出去。“小六哥!”刘雨欢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刀疤脸趁机上前,
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粗暴地往外拖。“臭娘们儿,走!”“放开她!
”陈小六挣扎着想爬起来,又被一个混混死死踩住肩膀,动弹不得。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刘雨欢像只待宰的羔羊被拖向院门。她徒劳地踢打着,哭喊着,
泪水糊了满脸。就在被拖过倒在地上的陈小六身边时,混乱中,刘雨欢的手猛地挣脱了一下,
飞快地往陈小六那只被踩住的手里塞了一样东西!动作快如闪电,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
那是一个小小的、硬硬的纸团。刀疤脸毫无察觉,骂骂咧咧地把她拖出了院门,
脚步声和哭喊声迅速远去。另一个混混又狠狠踢了陈小六一脚:“老实点!再敢找事,
弄死你!”啐了一口,也追了出去。破败的院子里只剩下陈小六一个人。
肩膀和腰腹的剧痛让他蜷缩在地上,好半天喘不过气。山风吹过,
带来远处几声模糊的狗吠和那帮**嚣张的哄笑声,越来越远。他死死咬着牙关,
口腔里弥漫开浓重的血腥味。他慢慢摊开那只被踩得生疼的手。手心被汗水浸得濡湿,
一个揉得极小的纸团静静躺在那里,边缘几乎被他攥破。
他用颤抖的、沾着泥土和血污的手指,极其艰难地,一点点将纸团展开。
纸上只有一行歪歪扭扭、用烧焦的炭条写下的字,
显然是在极度恐惧和仓促中完成的:“黑石沟,老砖窑。救救我弟弟!今晚他们带我走!
”3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铁钎,狠狠捅进陈小六的眼睛,烫得他浑身一激灵。
所有的谜团、猜疑、愤怒,在这一刻被这行字瞬间点燃,烧成一片滔天的烈焰!骗婚!拐卖!
人质!刀疤脸最后那句“卖个好价钱”像毒蛇一样噬咬着他的神经。他猛地从地上弹了起来,
顾不得浑身散架般的剧痛。黑石沟!那个废弃了十几年的老砖窑,离这里有三十多里山路,
全是崎岖难行的陡坡和密林!他必须赶在那帮畜生把刘雨欢转移走之前,把消息送出去!
陈小六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冲进屋里,
从炕席底下摸出那把磨得雪亮的柴刀别在腰后,又抓起墙角一个破旧的军用水壶灌满凉水。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神龛旁边那面蒙尘的镜框上,
里面嵌着他爹穿着旧式民兵制服、挎着步枪的照片。爹当年在公社民兵连干过,
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遇着真坏种,别怂!找穿制服的!”对!派出所!
只有穿制服的警察才能对付那帮手里可能有家伙的亡命徒!陈小六不再犹豫,
一头扎进了浓重的夜色里。山路崎岖,夜色如墨,冰冷的山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他深一脚浅一脚地狂奔,树枝抽打在脸上、胳膊上,划出道道血痕,
脚底被尖锐的石子硌得生疼。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呐喊:快!再快一点!黑石沟!
老砖窑!汗水浸透了破旧的褂子,又被夜风吹得冰冷刺骨。肺部火烧火燎,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铁锈般的腥甜。他摔倒了无数次,膝盖和手肘擦破,黏腻的血混着泥土。
但他立刻爬起来,继续跌跌撞撞地向前冲。刘雨欢那双绝望含泪的眼睛,
还有那张写着“救救我弟弟”的纸条,在他眼前交替闪现,
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疲惫不堪的身体。不知跑了多久,双腿早已麻木得失去了知觉,
全凭一股意志在机械地向前挪动。远处,
山坳的轮廓终于出现了点点稀疏的灯火——那是乡里唯一有派出所的地方!凌晨三点多,
陈小六像个从泥潭里捞出来的泥人,一头撞开了乡派出所那扇漆皮斑驳的绿色木门。
值班室里灯光昏暗,一个年轻的民警正伏在桌上打盹,被这巨大的动静惊得差点跳起来。
“救…救人!”陈小六嗓子已经完全嘶哑,扑到桌前,
双手死死抓住桌沿才勉强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身体,他大口喘着粗气,
胸腔里拉风箱似的呼哧作响,
“黑…黑石沟…老砖窑…拐卖…骗婚…人质…我媳妇…还有她弟弟…快…快去!
”他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汗水混着血水泥水从额头淌下,糊住了眼睛。
但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迸射出的恐惧、焦急和近乎疯狂的恳求,
让年轻的民警瞬间睡意全消,神情变得无比凝重。“同志,别急!坐下慢慢说!
”民警赶紧扶他坐下,倒了杯热水塞到他冰冷颤抖的手里,“黑石沟?老砖窑?拐卖?
你确定?”陈小六猛灌了几口水,烫得他直咧嘴,却奇异地让混乱的脑子稍微清醒了一点。
他颤抖着从怀里掏出那张被汗水浸得发软、边缘已经磨毛的纸条,
像捧着救命稻草一样递给民警。“看…这个!
我媳妇…塞给我的…他们今晚就要把她带走卖掉…她弟弟…还在他们手里当人质!
晰地把自己如何娶亲、刘雨欢如何偷藏钱、如何偷烧东西、刀疤脸如何上门要债抢人的经过,
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年轻民警看着纸条上那行炭笔字,听着陈小六的叙述,脸色越来越沉。
他立刻拿起桌上的老式摇把电话,用力摇了几圈:“喂?总机!给我接县局!紧急情况!
要快!”4天色将明未明,一层冰冷的灰蓝色笼罩着黑石沟。
废弃多年的老砖窑像一头蹲伏在荒草荆棘中的巨兽,沉默而阴森。
几堵残破的高大砖墙矗立着,黑洞洞的窑口如同怪兽张开的大嘴。
几辆没有开警灯的吉普车和摩托车悄无声息地停在远处山梁背面的树林里。
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借着地形和荒草的掩护,迅速而无声地向砖窑包抄过去。
陈小六也被允许跟在后面,他手里紧紧攥着一根结实的木棍,指关节捏得发白,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几乎要撞破肋骨。带队的刑警队长压低声音,
用极快的语速做着最后的部署。就在这时,一阵嘈杂的引擎声由远及近!
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卷着尘土,颠簸着从另一条坑洼的山路驶来,
吱嘎一声停在了砖窑前那片空地上。车门拉开,刀疤脸率先跳了下来,
骂骂咧咧地拽着一个被反绑双手、堵着嘴的身影下了车——正是刘雨欢!她头发散乱,
脸上带着泪痕和淤青,那身暗红色的嫁衣在灰暗的晨色中格外刺眼。紧接着,
另外几个打手也推搡着一个瘦弱惊恐、约莫十二三岁的男孩下了车。“妈的,磨蹭什么!
快点!把人弄进去!天亮了不好走!”刀疤脸烦躁地催促着,推了刘雨欢一把。她一个踉跄,
差点摔倒,绝望的目光下意识地扫向四周荒凉的山野。就是现在!“行动!
”刑警队长猛地一挥手!尖锐的警笛声骤然撕裂了山沟的寂静!“警察!不许动!举起手来!
”威严的吼声从四面八方炸响!“操!条子!”刀疤脸瞬间脸色剧变,惊骇欲绝,
反应却快得惊人。他第一反应不是举手,
而是猛地一把将身边离他最近的那个瘦弱男孩狠狠推向扑上来的警察,
同时另一只手闪电般地从后腰拔出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
转身就朝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的刘雨欢刺去!动作狠辣,分明是要灭口!“姐——!
”被推开的男孩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陈小六只觉得全身的血液都冲到了头顶!他看到刀疤脸眼中那疯狂的凶光,
看到那把致命的匕首划向刘雨欢毫无防备的后心!他离得最近,
身体比脑子更快地做出了反应。“雨欢!”一声野兽般的嘶吼从喉咙里迸发出来!
陈小六像一颗出膛的炮弹,不顾一切地猛扑过去,手中的木棍狠狠砸向刀疤脸持刀的手臂!
砰!木棍砸中了!但刀疤脸的手臂只是剧痛地一偏,匕首的去势并未完全阻住!
冰冷的刀锋依旧带着死亡的啸音刺向刘雨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
刘雨欢似乎也感觉到了背后袭来的致命寒意。她没有躲闪,反而在陈小六扑过来的同时,
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拧身,张开双臂,决绝地迎向了那把匕首!她的目标,
赫然是挡在陈小六的身前!噗嗤!一声沉闷得令人心胆俱裂的钝响。时间仿佛凝固了。
陈小六眼睁睁地看着那把锋利的匕首,深深地、毫无阻碍地捅进了刘雨欢的右胸下方!
温热的、带着浓重腥气的液体瞬间喷溅而出,有几滴滚烫地溅在他的脸上、脖子上。
“呃……”刘雨欢的身体猛地一僵,眼睛难以置信地睁大,瞳孔瞬间涣散。
她看着近在咫尺、目眦欲裂的陈小六,张了张嘴,却只涌出一大口鲜红的血沫。
那身暗红色的嫁衣,胸口的位置迅速被染成一片更深、更刺目的黑红,湿漉漉地黏贴在身上。
“雨欢——!!!”陈小六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凄厉嚎叫,巨大的恐惧和绝望瞬间将他淹没。
他丢开木棍,疯了一样扑上去,紧紧抱住刘雨欢软倒的身体。“妈的!
”刀疤脸还想抽刀再刺,旁边一个警察的枪托已经狠狠砸在他后脑勺上,
他哼都没哼一声就栽倒在地。其他几个打手也迅速被扑上来的警察死死按倒制服。
那个瘦弱的男孩挣脱了束缚,哭喊着扑向倒在血泊中的姐姐:“姐!姐——!”“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刑警队长对着步话机狂吼,声音都变了调。现场一片混乱。
陈小六跪在冰冷的地上,紧紧抱着怀里迅速失去温度的身体,
双手徒劳地、颤抖地捂住她胸前那个可怕的伤口,试图堵住那汹涌流出的鲜血。
粘稠温热的液体不断从他指缝间涌出,怎么也止不住。他看着她苍白如纸的脸,
看着她涣散瞳孔里最后一点微弱的光,巨大的恐惧像冰冷的潮水将他彻底吞噬。
“别死…雨欢…求求你…别死…”他语无伦次地哀求着,声音破碎不堪,
滚烫的泪水大颗大颗地砸在她沾满血污的脸上,和血水混在一起,蜿蜒而下。
刘雨欢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却只涌出更多的血沫。
她的眼睛费力地转向旁边被警察紧紧抱着、哭得撕心裂肺的弟弟,
又极其缓慢地、艰难地移回到陈小六那张被泪水和血污模糊的脸上。
那双渐渐失去焦距的眼睛里,最后残留的情绪,不是怨恨,不是恐惧,
而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沉重的悲哀,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释然?她的手,
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极其轻微地、颤抖地抬了一下,指尖似乎想要触碰陈小六的脸颊,
却在半途颓然落下。“姐——!”男孩凄厉的哭喊声在山谷里绝望地回荡。
刺耳的救护车笛声由远及近,划破了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5医院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焦虑与等待的沉闷气息。
惨白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照在光洁的地砖上,反射出冰冷的光。
陈小六像个木头人一样坐在长椅上,后背僵直地贴着冰凉的椅背。
他身上那件沾满血污和泥土的破褂子还没来得及换掉,干涸的血迹变成了深褐色,
紧紧贴在皮肤上,散发出浓重的铁锈味。双手摊在膝盖上,指缝里凝固着暗红的血痂,
怎么洗也洗不掉的痕迹。他脸上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布满了蛛网般的红血丝,
直勾勾地盯着对面墙上那盏“手术中”的红色指示灯。那刺目的红光,
像刘雨欢胸口洇开的血,灼烧着他的神经。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每一次手术室的门轻微响动,他都会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猛地抬头,心脏骤然缩紧,
直到看清出来的是护士或其他家属,才又失魂落魄地垂下头。
“小六哥…”一个怯生生的、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陈小六迟钝地转动了一下眼珠。是刘雨欢的弟弟,刘小川。
男孩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明显不合身的病号服,脸上还残留着泪痕和惊恐过后的苍白,
但那双眼睛,却和刘雨欢有几分相似,此刻正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小川…”陈小六的嗓子沙哑得像砂纸摩擦,“你姐她…会没事的…”这话说出来,
连他自己都觉得空洞无力。刘小川用力吸了吸鼻子,
又红了:“都怪我…要不是我…姐就不会被他们抓走…也不会…不会…”他哽咽着说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