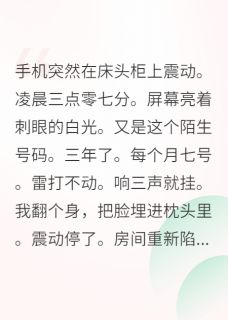
手机突然在床头柜上震动。凌晨三点零七分。屏幕亮着刺眼的白光。又是这个陌生号码。
三年了。每个月七号。雷打不动。响三声就挂。我翻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震动停了。
房间重新陷入黑暗。死寂。我闭上眼,数羊。一只羊,
两只羊...嗡——嗡——手机又震了!还是那个号码!我猛地坐起来,一把抓过手机。
手指悬在红色挂断键上。鬼使神差地,我按了绿色的接通键。没说话。那边也没声音。
只有细微的电流声。还有...很轻,很轻的呼吸。像有人把耳朵紧贴着话筒。“谁?
”我的声音有点哑。那边呼吸顿了一下。“琮琮...”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低沉,
带着点刻意压出来的沙哑,“是我。”我浑身的血,唰地凉了半截。这声音,
烧成灰我都认得。陈墨。我前男友。“陈墨?”我听见自己冷冰冰的声音,“你有病?
”那边沉默了几秒。呼吸声重了些。“琮琮,别这样。”他语气放软,
带着那种我过去很吃的、疲惫又深情的调调,“三年了,每个月我都打,
你一次都没接过...今天,你终于接了。”“我按错了。”我毫不客气。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气。”他自顾自地说下去,像在排练过无数遍的台词,
“当初...是我不对。我压力太大,太想证明自己...说了很多混账话,做了混账事。
琮琮,这三年,我没有一天不在后悔...”后悔?我差点笑出声。
后悔当初没把我这块垫脚石,榨得更干净点?“后悔完了?”我打断他,“说完我挂了。
”“等等!”他急急地喊,“别挂!宁琮,我们...能不能见一面?就一面!
我有话跟你说,很重要的话!求你了!”“没空。”“明天!明天中午!就半小时!不,
十五分钟!地点你定!”他语速快得像连珠炮,“求你了,琮琮,
看在...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过去的情分?”我重复了一遍,每个字都像冰渣子,
“陈墨,你跟我提情分?你配吗?”电话那头,他的呼吸猛地一窒。
“我知道我不配...”他声音低下去,带着点哽咽,
“我知道我伤透了你...但我现在真的...真的只想弥补。琮琮,给我个机会,就一次。
我发誓,最后一次打扰你!见了这次,我保证...再也不烦你!”我捏着手机。指尖冰凉。
三年了。这通阴魂不散的电话,像跗骨之蛆。甩不掉,膈应人。也许,是时候做个了断。
一次性,断个干净。“行。”我听见自己说,声音没什么起伏,“明天中午十二点半。
市中心,星悦城顶楼,‘半日闲’咖啡馆。过时不候。”“好!好!星悦城!半日闲!
十二点半!我一定到!”他声音瞬间拔高,透着狂喜,“谢谢你琮琮!谢谢你还愿意见我!
我...”我没等他说完。直接掐断了电话。屏幕暗下去。映出我没什么表情的脸。陈墨。
这个名字,连带那段糟心的过去,被我打包塞进记忆最角落的垃圾堆,盖了厚厚几层土。
三年没见。我甚至懒得去想他如今什么鸟样。当初分手,闹得极其难看。他赤红着眼,
像头被逼到绝境的野兽,冲我吼:“宁琮!你懂什么?你这种生下来就含着金汤匙的人,
懂我爬上来有多难吗?我要成功!我必须成功!你帮不了我,就别挡我的路!
”他所谓的“路”,就是攀上我们公司老总那个刚从国外镀金回来的独生女。他成功了。
靠着那张斯文俊秀的脸,和精心打造出来的“上进青年”人设,
成功把我这个谈了五年、陪他熬过最穷日子的“绊脚石”一脚踹开,
搭上了通往“上流社会”的青云梯。分手第二天,他就挽着那位千金的手,
高调出现在公司酒会上。而我,成了全公司的笑柄。“看,那就是陈墨的前女友,
被甩的那个。”“啧啧,听说当初倒贴得厉害,供陈墨读研呢...”“有什么用?
人家现在攀上高枝了,谁还记得她这垫脚石?”那些窃窃私语,像针,密密麻麻扎过来。
我没哭没闹。递了辞呈。用工作几年攒下的所有积蓄,加上父母支持的一点,
开了家小小的室内设计工作室。地方不大。地段也偏。但每一分钱,每一块砖,都干干净净。
是我宁琮自己的。工作室叫“拾光”。捡拾时光,也捡拾自己。生意磕磕绊绊,
慢慢有了起色。累,但踏实。我以为,生活终于上了正轨。陈墨这个名字,连同那些破事,
就该烂在过去的泥里。可他偏不。像甩不掉的鼻涕虫。每月七号,凌晨三点。准时来电。
骚扰。恶心。这次,必须做个彻底的了断。第二天中午,十二点二十。
我推开“半日闲”咖啡馆厚重的玻璃门。冷气扑面而来,驱散了外面的燥热。工作日的中午,
人不多。舒缓的钢琴曲流淌在空气里。我一眼就看到了靠窗位置的陈墨。他也看到了我。
立刻站起身,脸上堆起热切又局促的笑,快步迎了上来。“琮琮!你来了!”三年不见。
他变了。穿着剪裁精良的深灰色西装,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手腕上那块表,我记得,
是某个奢侈品牌的入门款,当初他盯着杂志看了好久,
念叨着“等以后发达了...”看来是“发达”了。只是那张曾经让我觉得干净俊朗的脸,
似乎被什么东西撑开了,皮肉有些松弛,眼底带着挥之不去的疲惫和...一丝油腻。
精心捯饬过的外表,也盖不住那股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急于证明什么的劲儿。“宁琮。
”我纠正他,声音平淡无波,绕过他伸过来的手,径直走向他对面的座位。
他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讪讪地收回手,跟着坐下。“琮琮...宁琮,”他改口,
双手交叠放在桌上,显得很紧张,“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我没接话。
拿起桌上的柠檬水,喝了一口。冰凉,微酸。“有话直说。”我放下杯子,“十五分钟。
计时开始。”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决心。“宁琮,我知道,过去是我**,
我猪油蒙了心!”他语速很快,带着痛心疾首的表演感,“我辜负了你,
辜负了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这三年,我每一天都在后悔!真的!”他抬眼,
努力想挤出点深情的泪光。可惜,演技退步了。眼眶干干的。“那个林薇薇,
”他提到他现任妻子的名字,语气带着明显的厌恶,“根本就是个被惯坏的草包!除了花钱,
什么都不会!脾气坏得要命,动不动就摔东西,指着鼻子骂我乡巴佬!
她爸妈更是...把我当条狗!呼来喝去!我在那个家,连喘口气都觉得憋屈!
”他越说越激动,脸涨红了。“宁琮,只有你!”他猛地倾身,双手越过桌面,
似乎想抓住我的手,被我冷冷一眼钉在原地,“只有你懂我!只有你是真心对我好!
不图我什么!我们在一起那五年,才是我最开心、最像个人的日子!”他喘着粗气,
眼神热切地像两团火。“我离婚了!”他几乎是喊出来,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宣告,
“上个月底,手续刚办完!财产分割?哼,他们林家防我跟防贼似的!但我净身出户也认了!
只要能摆脱那个火坑!”他死死盯着我的眼睛,声音压低了,带着蛊惑。“宁琮,
我们重新开始吧!好不好?我知道你现在开了工作室,不容易。我有能力了!
我这些年积累的人脉资源,都能帮你!我们一起,把事业做大!像我们以前计划的那样!
”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无比“真诚”。“还有...孩子的事...我知道,当初那个意外,
对你打击很大...是我**,那时候只顾着自己往上爬,
忽略了你...我们...我们还可以再...”“陈墨。”我打断他。声音不大。
但像一把冰锥,把他后面那些精心编织的煽情话语,全捅了回去。他愣住。“说完了?
”我问。“我...”他有点懵。“你的后悔,你的痛苦,你的不幸婚姻,你的净身出户,
你的宏图大业...”我一条条数着,语气平淡得像在念超市购物清单,“还有,你想帮我?
”我微微向前倾身,看着他的眼睛。那双曾经让我觉得像藏着星星的眼睛。
现在只剩下浑浊的算计和急切。“你凭什么觉得,”我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我宁琮,
是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备胎?是你走投无路时,捡起来就能用的接盘侠?”他的脸,
唰地白了。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嘴唇哆嗦着。“琮...宁琮,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真心...”“真心?”我扯了扯嘴角,一个毫无温度的笑,“你的真心,
三年前就喂狗了。现在跑我面前演什么深情?是被林家扫地出门,找不到下家,
又想起我这块被你踩过的垫脚石还算结实,想回来垫垫脚?”我的话,像淬了毒的针。
精准地扎进他最虚伪的伪装里。他脸上的肌肉抽搐着。那点强装的深情和悔恨,
像劣质墙皮一样簌簌往下掉。露出底下恼羞成怒的底色。“宁琮!”他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被戳穿的尖利,“你说话别这么难听!我放下身段来找你,是念着旧情!是给你机会!
你别不识抬举!”“身段?”我嗤笑一声,“陈墨,你浑身上下,
除了那身高仿西装和A货手表,还有什么值钱的身段?靠女人上位又被女人踹了的身段?
”“你!”他猛地拍桌站起来,引得旁边几桌客人侧目。他胸膛剧烈起伏,指着我的鼻子,
手指都在抖。“好!好!宁琮!你清高!你了不起!你以为自己开了个破工作室就翻身了?
就瞧不起人了?我告诉你!离开了林家,我陈墨照样是条龙!有的是人脉!有的是资源!
碾死你那个小破工作室,跟玩儿一样!”他喘着粗气,眼神阴鸷。“你等着!给脸不要脸!
有你哭着回来求我的时候!”他抓起桌上的手机和车钥匙,转身就要走。
背影都透着气急败坏的狼狈。“陈墨。”我又叫了他一声。他脚步顿住,没回头,
肩膀绷得死紧。“你的‘人脉’和‘资源’,”我慢悠悠地说,拿起手机,
点开屏幕看了一眼时间,“还剩三分钟。我建议你,坐下,听我说完最后几句话。
”他猛地转过身。眼神凶狠得像要吃人。“你还要说什么?!”“坐下。”我语气平淡,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他死死瞪着我,拳头捏得咯咯响。僵持了几秒。
也许是周围投来的目光让他难堪。也许是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还在作祟。
他最终还是铁青着脸,重重地坐回了椅子上。“说!”“第一,”我竖起一根手指,
“昨晚的电话,是我最后一次容忍。再有一次,不管是你,还是你找的猫三狗四,
我立刻报警。骚扰记录,我保存了三年。”他脸色变了变。“第二,”我竖起第二根手指,
“我的工作室,叫‘拾光’。干干净净,一砖一瓦都是我自己挣的。不劳你惦记,
更不怕你使绊子。想玩阴的?尽管放马过来。看看是你那点靠女人得来的‘人脉’硬,
还是我手里的真本事硬。顺便提醒你,恶意竞争,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看谁先耗死谁。
”他嘴唇抿得发白。“第三,”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清晰无比,“我们之间,
早就完了。从你为了攀高枝,亲手推掉我肚子里那个孩子,
还污蔑是我自己不小心摔掉的那一刻起,就彻底完了。连恨,都嫌多余。”陈墨的脸,
瞬间褪去所有血色。惨白如纸。眼神里充满了极度的震惊和...一丝猝不及防的恐惧。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脖子。
“你...你怎么...”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怎么知道的?”我替他说完,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陈墨,你是不是以为,当年你偷偷倒掉我的安胎药,
替换成活血的红花,做得天衣无缝?是不是以为,你买通那个小诊所的庸医,
让他一口咬定是我自己摔的,我就永远蒙在鼓里?”我看着他额头上瞬间冒出的冷汗。
看着他眼神里的慌乱和躲闪。心里一片冰凉的麻木。“人在做,天在看。”我轻轻地说,
“那个被你买通的庸医,后来医死了人,进去了。为了减刑,什么都吐出来了。录音,
转账记录,清清楚楚。我一直留着。”我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个很小的、老式的U盘。
轻轻放在桌面上。推到他面前。“这个,备份。原件,在我律师那里保管得很好。
”陈墨死死盯着那个小小的黑色U盘。像盯着一条毒蛇。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
刚才的气焰和威胁,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筛糠般的恐惧。
“宁...宁琮...”他声音抖得厉害,带着哭腔,
“你听我解释...当年...当年我也是没办法!林薇薇逼我的!
她不能容忍我跟你还有任何牵扯!更不能容忍你肚子里有我的孩子!
她说...她说如果我不处理干净,就让我滚蛋!我一无所有啊!我好不容易才爬上去!
我不能...”“所以,”我打断他歇斯底里的辩解,“为了你的前程,
你可以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栽赃给孩子的母亲。陈墨,你真不是个东西。
”我的声音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是在陈述一个早已确认、且令人作呕的事实。
他像被抽掉了脊梁骨,瘫软在椅子里。眼神涣散。“我...我补偿你!宁琮!你要多少钱?
我...我现在虽然净身出户,但我还有能力!我很快就能东山再起!你要多少?开个价!
只求你...求你别把这事说出去!求你了!”他语无伦次,带着绝望的哀求。“钱?
”我笑了,这次是真的觉得荒谬,“陈墨,你的脏钱,买得起一条命吗?
买得回我当年躺在冰冷手术台上,被清宫刮宫,疼得死去活来,还要听着护士议论‘看,
就是她自己不小心摔流产那个’的感觉吗?”我站起身。拿起包。“这个U盘,送你了。
算是对我们过去,彻底的一个了断。记住我的话,永远,别再来烦我。”“宁琮!
”他猛地扑过来,想抓住我的胳膊,被我侧身躲开。他扑了个空,狼狈地撞在桌子上。
“你不能这样!你这是要毁了我!毁了我啊!”他嘶吼着,像个输光了一切的赌徒,
涕泪横流。咖啡馆里所有人都看了过来。指指点点。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像看一团肮脏的垃圾。“毁掉你的,从来都是你自己那颗又贪又毒的心。”我冷冷地说完,
转身,毫不留恋地走向门口。玻璃门开合。将身后那片混乱和绝望的嘶吼,彻底隔绝。
阳光有些刺眼。我眯了眯眼。深吸一口气。空气里,
没有陈墨身上那股令人作呕的、混合着廉价古龙水和焦躁的味道。
只有初夏阳光晒在柏油路面上的,干净的气息。我掏出手机,拉黑那个纠缠了三年的号码。
动作干脆利落。像切掉一块腐烂的肉。然后,点开微信,置顶的对话框。
闺蜜林琰的头像在跳。【琮琮!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不是又演深情?你没心软吧?
快汇报战况!急死我了!】我笑了笑。指尖飞快地打字。【刚结束。渣滓已清理完毕。
】【**!效率!怎么清理的?快说说!是不是怼得他生活不能自理了?】【差不多。顺便,
把当年流产的真相,拍他脸上了。】对面沉默了几秒。然后,疯狂地刷屏。【!!!!!!!
!!!】【******!!!宁琮你牛逼大发了!!!】【他什么反应?
是不是当场吓尿了?!】【妈的!我就知道当年那事有鬼!那个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