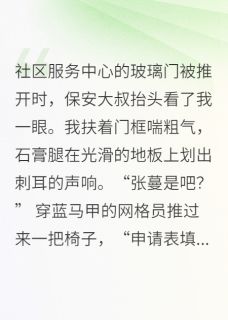
社区服务中心的玻璃门被推开时,保安大叔抬头看了我一眼。我扶着门框喘粗气,
石膏腿在光滑的地板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张蔓是吧?
”穿蓝马甲的网格员推过来一把椅子,“申请表填好了,身份证给我。
”手指在包里摸索时,手机又开始震动。这次是弟弟张磊打来的,我直接按了拒接。
“你这腿……”网格员盯着我的石膏皱眉。“没事,昨天摔的。”我把身份证递过去,
目光落在墙上的公示栏,我的名字在廉租房名单的最后一行。三个月前申请的时候,
妈还在电话里骂我浪费时间:“女孩子家家租什么房?早晚要嫁人的,
不如把钱给你弟还车贷。”那时我还在犹豫,总觉得血浓于水,
或许再忍忍就能换来他们的体谅。直到昨天傍晚,林薇踩着我的漫画书炫耀她的新美甲,
说“这些破烂早该扔了,占地方”。我伸手去抢,却被她推下楼梯。滚到最后一级台阶时,
后脑勺磕在水泥地上,眼前炸开一片金星。模糊中看见妈从厨房跑出来,
第一句话是“小薇有没有吓到?”,然后才瞥了我一眼,“装什么装,赶紧起来做饭。
”原来有些人心,是捂不热的。“签个字。”网格员把租赁合同推到我面前。我低头写字,
手腕的伤口被牵扯得生疼,笔锋却异常坚定。“钥匙明天能拿,今天先去物业领门禁卡。
”她忽然叹了口气,“我知道你家情况,上次你妈来闹,
说你自私自利……”我握着笔的手顿了顿。上周妈确实来过社区,撒泼打滚说我不孝顺,
把她和弟弟逼得活不下去,引来一群人围观。那时我还在公司加班,接到网格员电话时,
浑身的血液都在倒流。“她高兴就好。”我签完字,把合同折好放进包里。走到门口时,
手机再次震动,是银行的短信提醒。尾号8765的储蓄卡,到账200000元。
我愣住了,反复确认好几遍,数字后面的五个零刺眼得很。这张卡是大学时办的,
早就被我遗忘在抽屉角落,昨天摔下楼时从口袋里掉出来,刚才在医院才捡回来。
谁会往这张卡上打钱?正疑惑着,陌生号码打来电话,我犹豫了一下接起。
“请问是张蔓女士吗?”电话那头是温和的男声,“我是环球律师事务所的李哲,
您外公的遗产需要您来办理继承手续。”外公?这个词在我脑海里激起一阵模糊的涟漪。
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十岁那年的春节。记忆里是个穿中山装的老人,把一个红布包塞给我,
说“蔓蔓要好好学习,以后靠自己”。妈后来把红布包抢走,说“你外公偏心,
就疼你这个外孙女”,再后来就不许我再提他。“他……”我嗓子发紧,“去世了?
”“是的,三个月前。”李律师的声音很平静,“老先生留下一套四合院和一些存款,
指定由您继承。”四合院?我怀疑自己听错了,又或者是伤口感染引起的幻听。
“您方便来事务所一趟吗?地址在……”李律师报了个地址,是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
挂了电话,我站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台阶上,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脸上,暖得有些不真实。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张磊。我深吸一口气,按下接听键。“姐!你什么意思?
妈说你不借五万块?”他的声音像炸雷,“我换不了车,怎么去接客户?
耽误了生意你赔得起吗?”“赔不起。”我看着远处的高楼,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
“你什么态度?”张磊拔高了音量,“妈都气哭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
不然我就去你公司闹!”以前每次他说这话,我都会妥协。怕同事笑话,
怕领导知道家里的烂事,怕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丢了。可现在,我忽然觉得无所谓了。
“你去吧。”我轻轻说,“顺便告诉你一声,我已经辞职了。”上周被妈闹过之后,
领导找我谈话,话里话外暗示我影响了公司形象。那时我还在委曲求全,今天却觉得,
这样的工作,不做也罢。“你疯了?”张磊在电话那头尖叫,“辞职?
你不上班谁给我挣钱?”“你自己。”我挂断电话,顺手把他和妈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世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我拦了辆出租车,报出李律师给的地址。
司机师傅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姑娘,去那地方啊?都是大老板呢。”我笑了笑,没说话。
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曾经熟悉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路过以前上班的写字楼时,
我看见楼下的咖啡馆,想起无数个加班的深夜,我在这里点一杯最便宜的美式,
假装自己也能拥有片刻的轻松。那时总想着,等弟弟的车贷还完,等妈不再找事,
我就能喘口气了。原来困住我的从来不是钱,是那可笑的亲情枷锁。
出租车停在一栋复古的洋楼前,门口的石狮子威风凛凛。我付了钱,一瘸一拐地走上台阶。
玻璃门自动打开,穿西装的前台微笑着问:“请问有预约吗?”“我找李哲律师,预约好的。
”“请跟我来。”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脚步声被完全吸收。李律师的办公室很大,
墙上挂着好多证书,他站起来和我握手,目光落在我的石膏腿上时,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
“路上有点事,耽误了。”我解释道。“没关系,请坐。”他递给我一杯温水,
“您外公去世前留下遗嘱,所有遗产都归您所有,包括东城区的四合院,
还有银行存款八百七十万。”八百七十万。这个数字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我想起小时候,
妈总说外公重男轻女,从不疼张磊,所以我们才很少来往。原来他一直记得我。
“这是房产证和银行卡,密码是您的生日。”李律师把文件袋推过来,“还有这个,
是老先生特意嘱咐留给您的。”那是个褪色的红布包,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我颤抖着打开,
里面是一本相册,还有一张泛黄的存折。相册里全是我的照片,从满月到十岁,
每张下面都写着日期。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纸条,是外公的字迹:“蔓蔓,别学你妈,
要为自己活。”存折的余额是三千块,开户日期是我十岁生日那天。眼泪忽然决堤,
我趴在桌子上,哭得像个孩子。这么多年的委屈、隐忍、自我牺牲,
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原来我不是没人疼的,原来我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李律师递给我一包纸巾,安静地等我平复情绪。“谢谢您。”我擦干眼泪,
把红布包紧紧抱在怀里。“应该的。”他笑了笑,“四合院现在租出去了,租户下周到期,
您要是想住进去,提前说一声,我帮您联系。”“我想住进去。”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那是外公留下的地方,是真正属于我的家。走出律师事务所时,阳光正好。我站在路边,
掏出那张存有八百万的银行卡,指尖冰凉。手机响了,是陌生号码,我接起来,
听见妈气急败坏的声音:“张蔓!你把我拉黑了?你个白眼狼!赶紧把钱打给你弟,
不然我就去法院告你!”“你去告吧。”我看着街对面的奢侈品店,忽然想通了,“对了,
告诉你一件事,我外公给我留了套四合院,值几千万。”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爆发出刺耳的尖叫:“什么?那是张家的钱!你凭什么独占?我是你妈,我有份!
”“遗嘱上没你的名字。”我语气平淡,“还有,以后别再联系了,我们断绝关系。
”不等她反应,我直接挂了电话,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口袋里的手机还在震动,
大概是张磊用别的号码打来的。我没再理会,拦了辆出租车,报了四合院的地址。
司机师傅吹了声口哨:“那地方可是黄金地段,姑娘你住那?”“以后是了。
”我望着窗外,嘴角忍不住上扬。到了四合院门口,我掏出钥匙,手有些抖。
推开那扇朱漆大门,院子里的石榴树结满了果子,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青石板上,
一切都像梦里的样子。租户还没走,看见我愣了一下:“你是?”“我是房子的新主人。
”我笑着说,“下周再搬没关系,不急。”回到街上,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医院重新处理伤口。医生看着我的病历皱眉:“怎么现在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