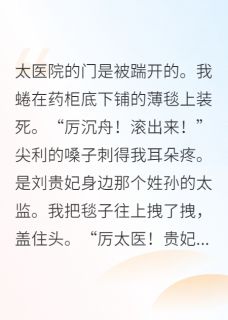
一场震动前朝后宫的腥风血雨,以雷霆手段迅速落下帷幕。尘埃落定那天,
皇帝在御书房单独召见了我。我跪在冰冷光滑的金砖地面上,头深深埋着,大气不敢出。
虽然真凶伏法,但我深夜闯宫、私下传递消息(尽管未遂),哪一条都是大罪。
皇帝坐在宽大的御案后,手里把玩着那块曾经赏赐给我的玉如意。书房里静得可怕,
只有更漏滴滴答答的声音。“厉沉舟,”皇帝的声音听不出喜怒,“你医术,不错。
”我心头一紧,连忙道:“微臣惶恐!微臣……微臣只是略通皮毛,侥幸……”“侥幸?
”皇帝打断我,语气微扬,“一次是侥幸,两次,还是侥幸?”他指的是救温灼和救皇后。
我哑口无言,冷汗顺着鬓角滑落。“你胆子,更大。”皇帝的声音冷了下来,“私查宫闱,
妄传消息,深夜闯宫,惊扰圣驾……哪一条,都够砍你的脑袋。”“陛下恕罪!
”我重重叩首,“微臣……微臣自知罪该万死!但当时情势危急,真凶步步紧逼,杀人灭口!
微臣与温采女命悬一线,实乃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惊扰圣驾,罪该万死!
但求陛下念在……念在微臣一片赤诚,
只为揭露真相、替皇后娘娘申冤的份上……饶恕温采女!所有罪责,微臣愿一力承担!
”我把头磕得砰砰响。皇帝沉默着,手指在光滑的玉如意上轻轻摩挲。那沉默的压力,
几乎让我窒息。良久,他才缓缓开口,
语气带着一种深沉的疲惫和一丝难以捉摸的意味:“一力承担?你承担得起吗?
”我伏在地上,不敢答话。“厉沉舟,”皇帝的声音低沉下去,“你可知,朕为何留你性命,
还赏你这柄如意?”“微臣……微臣愚钝……”“因为你‘有用’。
”皇帝的话直白得近乎冷酷,“你医术,尚可。胆子,够大。心思……也够细。更难得的是,
你知道自己该在什么位置。”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如刀,仿佛能穿透我的脊背,“就像这次,
你查到了真凶,却知道凭自己的力量扳不倒,所以选择了最直接、也最冒险的方式,
把证据和麻烦,一起扔到了朕的面前。”我身体微微发僵。皇帝看得太透了。“这深宫,
前朝,”皇帝的声音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苍凉,“需要忠臣良将,开疆拓土,匡扶社稷。
也需要……庸医。”庸医?我一愣。“对,庸医。”皇帝的语气带着一丝淡淡的嘲讽,
“就像你给刘贵妃开的‘红枣姜汤’。有些病,不需要猛药,甚至……不需要治好。
只需要让它看起来‘在治’,让它‘温补’着,不恶化,不蔓延,就够了。这后宫,
也是一样。有些脓疮,挑破了,血流成河,伤筋动骨。捂着,用温汤养着,让它慢慢消下去,
虽然难看,但至少……维持着表面的体面,不至崩坏。”他站起身,走到我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将那柄玉如意轻轻放在我面前的地上。“厉沉舟,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我浑身冰冷,又仿佛被一道闪电劈中,瞬间明白了皇帝话中深意。他留我,
不是因为我有功,而是因为……我够“庸”,够“识趣”,能在这深宫里,
做一个他需要的、懂得用“温补方子”处理那些不能挑破的“脓疮”的“庸医”!
“微臣……”我喉咙干涩,艰难地吐出几个字,“微臣……明白了。”“明白就好。
”皇帝转身走回御案后,“温灼,朕会给她一个才人的位份,让她安心养伤。碧桐院,
以后就改叫静思苑吧。至于你……”他顿了顿,“太医院院判张明礼年事已高,
此次又受惊过度,已向朕请辞。院判之位……悬空。你就先做个院使吧。”院使?
太医院二把手?!这升迁速度简直如同坐火箭!但我知道,这不是奖赏,是枷锁!
是皇帝把我牢牢钉在了这个“庸医”的位置上,
成为他平衡后宫、处理那些“温补”之事的工具!“微臣……微臣才疏学浅,
恐难当大任……”我本能地想推辞。“朕说你能,你就能。”皇帝的声音不容置疑,
“做好你的‘温补’太医。不该你治的‘病’,别碰。不该你管的事,别问。这柄如意,
朕赏你了,就放在你的值房里,时时看着。退下吧。”“微臣……领旨谢恩!”我深深叩首,
捡起那柄冰冷沉重的玉如意,倒退着离开了御书房。走出紫宸宫,外面阳光刺眼。
我抱着那柄玉如意,感觉像抱着一座冰山。院使?太医院二把手?听起来风光无限。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从今往后,我这条咸鱼,算是彻底被腌渍入味,
挂在了皇帝需要的位置上,成了这深宫权力棋盘上一枚身不由己、专门负责“温补”的棋子。
院使的袍服穿在身上,沉甸甸的,压得我肩膀发酸。太医院正堂里,
属于院使的那张宽大桌案锃光瓦亮。下面站着的太医们,
包括那几个曾经对我爱答不理的资深太医,此刻都垂手肃立,眼神复杂,
敬畏中带着难以掩饰的疏离和……一丝嫉妒。“厉院使,这是今日各宫请脉的牌子,
请您过目。”一个年轻太医恭敬地将托盘呈上,上面放着代表各宫妃嫔的绿头签。
我扫了一眼。栖霞宫(刘才人,曾经的刘贵妃)的牌子在最下面,落满了灰。
凤仪宫皇后的牌子依旧在最顶端,只是旁边标注着“静养,张院判主理”。
还有其他一些妃嫔的牌子。我随手翻了翻,拿起一张写着“静思苑温才人”的牌子,
又拿起一张写着“兰芷轩赵美人”的牌子(赵美人以体弱多病、心思敏感闻名)。
“温才人处,我亲自去。赵美人那边……”我沉吟了一下,
看向旁边一个面相老实的中年太医,“周太医,你跑一趟吧。赵美人素来体虚,
你就按老方子,开些益气养血的太平方,叮嘱她放宽心,勿要多思多虑即可。”“是,
院使大人。”周太医躬身应下,眼神里似乎松了口气。给赵美人看病是苦差事,
开太平方最保险。我挥挥手,示意其他人散了。太医们鱼贯而出,偌大的正堂只剩下我一人。
空气里弥漫着药香和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走到那张宽大的院使座椅前,却没有坐下去。
手指拂过冰凉的桌面,最后落在那柄被高公公派人送来的、供奉在桌案一角的御赐玉如意上。
触手生凉。静思苑依旧偏僻,但院门口多了两个沉默的内侍守卫,是皇帝派来的。
院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那几棵老梧桐似乎也被精心照料过,抽出了些许新芽。
我提着药箱走进去。温灼,不,现在该叫温才人了,正坐在廊下晒太阳。
她穿着才人规制的浅碧色宫装,气色比之前好了许多,虽然依旧清瘦,但脸上有了点血色,
额头上的伤疤也淡了。只是眼神,比以往更加沉静,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
映着廊檐的影子。“厉院使。”她看到我,起身,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声音平静无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