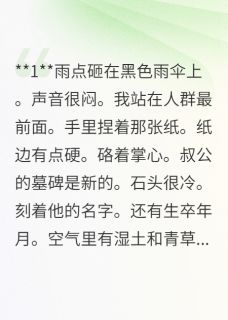
**1**雨点砸在黑色雨伞上。声音很闷。我站在人群最前面。手里捏着那张纸。
纸边有点硬。硌着掌心。叔公的墓碑是新的。石头很冷。刻着他的名字。还有生卒年月。
空气里有湿土和青草的味道。混着廉价香水的味道。来自我身后。律师姓周。他穿着黑西装。
领带打得一丝不苟。声音平板。没有高低起伏。“李志远先生遗嘱。”“名下所有财产。
”“包括银行存款、股票、房产、车辆及收藏品。”“估值约五千万元人民币。
”“由侄孙李默一人继承。”后面有人抽气。声音短促。像被掐住了脖子。“但,
”周律师推了下眼镜,“附加生效条件。”他看向我。镜片后的目光没什么温度。
“继承人李默。”“需与遗嘱见证人王建国、张春梅夫妇及其子赵天宇。
”“在遗嘱指定房产内。”“共同居住生活三个月。”“自今日起算。”“三个月期满。
”“无异议。”“遗嘱生效。”他顿了顿。补充道。“李志远先生特别注明。”“此条款。
”“意在考验人性。”“不可更改。”雨好像更大了。伞沿的水连成了线。落在地上。
溅起小小的水花。我的鞋尖湿了。冰凉的感觉渗进来。王建国是我大伯。张春梅是我二姑。
赵天宇是我堂哥。他们就在我身后。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像针。扎在我的背上。
周律师看着我。“李默先生。”“你是否接受?”我抬起头。雨水顺着伞骨流下。
在眼前形成一片模糊的水幕。墓碑上的字也花了。“接受。”我说。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
周律师点点头。把一份文件副本递给我。我接过来。纸张冰凉。王建国的手搭上我的肩膀。
很重。“小默啊,”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刻意压低的、做作的哽咽,“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就像照顾自己亲儿子一样。”张春梅凑过来。
她的眼圈是红的。不知是哭的还是别的什么。“是啊小默,别怕。”“有姑姑在呢。
”“你叔公……走得突然。”“我们就是你最亲的人了。”赵天宇站在他们身后。
比我高半个头。他双手插在裤兜里。眼神飘忽。嘴角似乎向上扯了一下。又很快压平。
“走了走了,”王建国招呼着,“雨大,别淋坏了。”他用力揽着我的肩膀。
半推着我离开墓地。他的力气很大。脚步迈得也快。我几乎跟不上。“那房子,
”张春梅紧走两步跟上,声音压低了,但掩不住热切,“就是城西那栋带大花园的?”“嗯。
”王建国应了一声,目光扫过我手里的文件,“钥匙呢?小默?
”我摸出周律师刚才一并给我的钥匙。铜的。有点沉。王建国一把拿了过去。掂了掂。“走!
”“先去看看地方!”“这鬼天气!”“晦气!”他加快了脚步。雨幕里。
他的背影显得迫不及待。那栋房子在城西的静湖苑。叔公生前很少来住。但一直雇人打理。
独栋。三层。带一个不小的院子。铁艺大门有些年头。爬满了藤蔓。湿漉漉的。
王建国用钥匙打开大门锁。“咔哒”一声。他率先推开。铁门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院子里的草坪修剪得很整齐。雨打在草地上。绿得发亮。一条鹅卵石小路通向主屋。
张春梅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这么大!”她小跑着踏上台阶。
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门往里张望。“哎呀!这客厅!”“这吊灯!”赵天宇也来了精神。
几步超过他爸妈。推开了没锁的玻璃门。“爸!妈!快看!”“这电视墙!够气派!
”王建国背着手。踱步进去。像在巡视自己的领地。他环顾着挑高的大厅。
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巨大的水晶吊灯即使没开灯。
也折射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光。名贵的红木家具沉默地彰显着价值。墙上挂着几幅油画。
我认出其中一幅的作者。拍卖行的常客。“不错。”王建国点点头。脸上没什么表情。
但眼神很亮。“老家伙……咳,你叔公,挺会享受。”他转向我。“小默啊。
”“房间怎么分?”“我们这一家三口。”“还有你。”他语气自然。仿佛天经地义。
张春梅已经快步走向一楼的走廊。推开一扇扇门查看。“这间大!采光好!带独立卫生间!
”她指着一间朝南的大卧室。“天宇住这间!”“年轻人,住得舒服点。
”她又推开隔壁一间稍小的。“这间也不小!”“建国,我们住这间!
”她完全没看剩下的房间。也没问我。
赵天宇已经把他背着的双肩包扔进了那个朝南的大卧室。
自己则一**陷进客厅中央巨大的真皮沙发里。
拿起茶几上一个看起来很沉的金属打火机把玩。“那……我呢?”我问。声音不大。
王建国好像刚想起我。“哦,楼上,”他随手指了指旋转楼梯,“楼上应该还有房间。
”“你自己去看看。”“随便挑一间就行。”“我们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
”“住楼下。”张春梅从“他们”的房间里探出头。“就是。”“小默你年轻。
”“多爬爬楼梯。”“锻炼身体。”我点点头。没说什么。提着我自己那个简单的行李包。
踏上楼梯。楼梯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二楼走廊幽深。有好几个房间门。
我推开最近的一间。是个书房。两面墙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堆满了书。
中间一张宽大的书桌。另一间是影音室。沙发很大。屏幕占据了一整面墙。再推开一扇门。
是个储物间。堆着些旧家具和箱子。落满了灰。最里面。走廊尽头。有一扇小门。
我拧开把手。房间很小。大概只有赵天宇那间的一半。朝北。窗户对着后院的高墙。
墙根下长着些耐阴的植物。光线很差。靠墙放着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一个简易衣柜。
一张旧书桌。桌面上空空荡荡。积着一层薄灰。
这大概以前是给保姆或者偶尔留宿的客人住的。我把行李包放在床上。拉开拉链。
拿出里面几件换洗衣服。挂进空荡荡的衣柜。声音从楼下传来。是张春梅。带着点不满。
“小默!下来一下!”我关上衣柜门。走下楼梯。张春梅站在客厅中央。指着厨房方向。
“去看看厨房有什么。”“这都几点了?”“折腾一天。”“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王建国坐在沙发上。占据了主位。拿着遥控器在开那台巨大的电视。
赵天宇躺在他旁边的贵妃榻上。两条腿高高翘起。搁在扶手上。脚上还穿着湿漉漉的球鞋。
鞋底蹭在米白色的昂贵皮革上。留下几道难看的污痕。他专注地刷着手机。眼皮都没抬。
我走进厨房。很大。很干净。设备齐全。嵌入式冰箱是双开门的。我拉开。
冷藏室里几乎是空的。只有几瓶矿泉水。几盒牛奶。冷冻室有几袋速冻水饺。一些冻肉。
“有什么?”张春梅的声音追进来。“有饺子。”我说。“饺子?”她的声音立刻拔高了,
“大晚上的就吃饺子?”“搬家第一天!”“多不吉利!”“滚来滚去的!”“像什么样子!
”“下点面条也行啊!”我拉开橱柜。上面几层放着崭新的锅碗瓢盆。下面一层。
有几筒挂面。“有挂面。”我说。“那就煮面!”张春梅命令道,“多放点青菜!
打几个鸡蛋!冰箱里有鸡蛋吧?”“有。”“动作快点!”“饿死了!”她转身走了。
我站在厨房中央。大理石台面冰凉。头顶的LED灯管发出冷白的光。我拿出锅。接水。
放在嵌入式的电磁炉上。按下开关。蓝色的数字跳动。水慢慢热起来。我找出面条。青菜。
鸡蛋。冰箱里还有一小把蔫了的葱。水开了。白色的蒸汽涌上来。
模糊了眼前铮亮的不锈钢抽油烟机面板。我把面条放进去。用筷子搅散。面条在滚水里沉浮。
变软。蒸汽扑在脸上。温热。带着面食特有的气息。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
是吵闹的综艺节目。主持人和嘉宾夸张的笑声。还有王建国偶尔的点评。“这什么玩意儿?
”“无聊!”赵天宇似乎换了个游戏。手机里传出激烈的枪击声和喊叫。“左边!左边有人!
”“傻X队友!会不会玩!”张春梅在客厅和他们的卧室之间走动。拖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
啪嗒。啪嗒。脚步声靠近厨房门口。“煮好了没?”她探进头。“快了。
”我看着锅里翻滚的面条。“多煮点!”她说,“天宇年轻,长身体,吃得多!
”“鸡蛋多放几个!”“别抠抠搜搜的!”“你叔公留下这么大产业。
”“还差这几个鸡蛋钱?”“真是!”她嘀咕着。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又远去了。
锅里的面条煮得有点胀了。我关掉火。拿起一个最大的汤碗。把面条捞进去。倒了点面汤。
又从锅里捞出煮好的三个荷包蛋。铺在上面。烫了几根青菜。撒了点葱花。葱花有点黄了。
我端着这碗堆得冒尖的面。走到客厅。放在那张宽大的玻璃茶几上。“面好了。”我说。
赵天宇第一个放下手机。坐起身。拿起筷子。直接把他碗里最大的两个荷包蛋夹走。
放进他自己面前的小碗里。又把面条挑了一大坨过去。直到他的小碗堆满。
他才把剩下连汤带水、没剩多少面条的大碗往中间一推。“行了。”他含混地说。
低头开始狼吞虎咽。王建国拿起筷子。在碗里搅了搅。挑了几根面条。皱了皱眉。
“清汤寡水的。”“没点油水。”“怎么吃?”张春梅也坐下。端起碗。小口吃着。
“凑合吧。”“第一天。”“明天我去买点好菜。”她看了我一眼。“小默。
”“你也坐下吃啊。”“站着干嘛?”“哦。”我转身回厨房。拿了个小碗。回来时。
茶几上那碗面已经空了。只剩下一点飘着油花的汤底。王建国靠在沙发上。摸着肚子。
赵天宇又躺了回去。继续打游戏。张春梅站起身。“我收拾一下。”她端起空碗和筷子。
走向厨房。很快。厨房传来水龙头哗哗的水声。我拿着空碗。站在茶几旁。汤底也凉了。
凝结起一层薄薄的白色油脂。像冷却的皮肤。**2**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摆。
卡着固定的节奏。单调地重复。早晨六点半。我的房门会被敲响。不轻不重。
刚好够把我从浅眠中惊醒。张春梅的声音穿透薄薄的门板。“小默!”“起来做早饭了!
”“天宇上学要迟到了!”我睁开眼。窗外还是灰蒙蒙的。没有光。只有高墙的暗影。
我起床。穿上衣服。冷水扑在脸上。驱散最后一点睡意。下楼。走进厨房。打开冰箱。
拿出牛奶。鸡蛋。面包片。或者速冻包子。开始忙碌。七点。早饭准时摆在餐桌上。
王建国打着哈欠坐下。拿起报纸。或者刷手机新闻。赵天宇睡眼惺忪。头发乱糟糟。
坐下就吃。抱怨牛奶不够热。或者煎蛋太老。张春梅会数落他几句。让他快点吃。别磨蹭。
然后话题会转到家里的开销。“小默啊。”张春梅端起牛奶。抿了一口。“家里牛奶快没了。
”“鸡蛋也不多了。”“还有天宇喜欢喝的那个进口果汁。”“上次买的都喝完了。
”她看着我。“待会你去趟超市。”“买点回来。”“钱……”她顿了顿。
“先用你身上那点。”“你叔公的钱现在不是还没到你手嘛。”“等三个月后。
”“姑姑加倍还你。”“一家人。”“不会亏待你的。”她从不会给我钱。买菜。买日用品。
交水电燃气费。甚至赵天宇要买新球鞋。王建国要买新鱼竿。都是用我的钱。
我放在钱包里的现金。还有银行卡里仅存的几千块生活费。像被拧开的水龙头。飞快地流走。
我点头。说:“好。”吃完饭。赵天宇一抹嘴。抓起书包。“爸,妈,我走了!
”门砰地关上。王建国慢悠悠吃完最后一口煎蛋。放下筷子。“我出去转转。
”“约了老刘下棋。”他也走了。张春梅开始收拾碗筷。她把油腻的盘子叠起来。端进厨房。
放在水槽边。“小默。”“把碗洗了。”“再把地拖一下。”“客厅地上。
”“天宇昨天带同学回来。”“踩得全是脚印。”“不像话!”她擦着手。走出厨房。
坐到沙发上。拿起电视遥控器。屏幕亮起。传出早间剧场的音乐声。我走进厨房。
拧开水龙头。冰冷的水冲在手上。油腻的碗碟堆在水槽里。沾着蛋黄和面包屑。
我挤了点洗洁精。拿起海绵。开始洗。水流声。碗碟碰撞的轻响。
盖过了客厅里电视剧的对白。洗好碗。沥干水。放进消毒柜。按下开关。嗡嗡的轻鸣响起。
我拿出拖把桶。接水。倒上清洁剂。搅拌出泡沫。提着沉重的桶。走到客厅。
张春梅陷在沙发里。看得入神。脚边扔着瓜子壳。还有几片薯片的碎屑。
我避开她伸在过道上的脚。从客厅另一头开始拖地。湿漉漉的拖把划过光洁的大理石地面。
留下深色的水痕。很快又变干。恢复光亮。拖到她脚边时。我停了一下。“姑姑。
”“抬下脚。”她似乎没听见。眼睛盯着电视屏幕。女主角正在哭诉。
我把拖把往前移了一点。碰到了她拖鞋的边。她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回脚。“哎哟!
”“看着点!”她不满地瞪了我一眼。“拖个地都毛手毛脚的!”“小心点!
”“这地板多贵!”“划坏了你赔得起吗?”她重新把脚放回地上。继续嗑瓜子。
瓜子壳轻飘飘地落在我刚拖干净的地面上。我沉默地拖过那一小块地方。
把瓜子壳和碎屑扫进簸箕。清理完客厅。我提着桶回厨房。清洗拖把。张春梅的声音追过来。
带着点慵懒的腔调。“小默啊。”“中午想吃红烧排骨。”“你去菜市场。
”“挑新鲜的肋排买。”“再买条活鱼。”“天宇爱吃清蒸的。”“对了。
”“楼下超市好像有进口车厘子。”“看着挺新鲜。”“也买两斤回来。”“贵是贵了点。
”“偶尔尝尝鲜嘛。”“快去快回啊。”“等着做午饭呢。”我擦干手。
从挂在厨房门后的旧外套里掏出钱包。打开。里面剩下的几张红色钞票。显得单薄可怜。
我抽出一张。其余的放回去。拉好拉链。穿上外套。走出别墅大门。阳光有些刺眼。
空气是冷的。我沿着小区的林荫道往外走。皮鞋踩在落叶上。发出脆响。菜市场在两条街外。
很热闹。人声鼎沸。混杂着鱼腥、肉臊、蔬菜泥土和熟食香料的气味。我在肉摊前停下。
挑了一扇看起来不错的肋排。老板麻利地剁好。装袋。秤砣高高翘起。“五十八块三!
”“算你五十八!”我递过那张百元钞票。他找给我一把零钱。油腻腻的。沾着生肉的血水。
我接过。塞进裤兜。又走到水产区。腥味更重。水盆里。鱼在浑浊的水里游动。
氧气泵咕噜噜冒着泡。我指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鲈鱼。“这个。”老板抄起网兜。利落地捞起。
鱼在网兜里剧烈挣扎。水珠四溅。“啪!”鱼被摔在案板上。老板举起木槌。对着鱼头。
狠狠敲了一下。鱼不动了。刮鳞。去内脏。冲洗干净。装进黑色塑料袋。“四十二!
”我付了钱。最后走到水果摊。红得发紫的车厘子堆在精致的竹筐里。标签写着:进口,
128元/斤。我拿起旁边的塑料小筐。挑拣着。尽量选大的。硬的。装满一小筐。
摊主过秤。“刚好两斤!”“两百五十六!”我拿出裤兜里所有的钱。数了数。
肉钱找零四十二。加上原本剩下的。刚好两百六十块。我递过去。摊主找回四张一元纸币。
我把皱巴巴的纸币塞回口袋。提着沉甸甸的肉、鱼和车厘子。往回走。袋子勒得手指发麻。
回到别墅。厨房里。张春梅正靠在流理台边。拿着手机。手指飞快地点着。似乎在聊天。
听到我进来。她头也没抬。“排骨洗洗。”“焯水。”“鱼放池子里。”“等会儿我来弄。
”“车厘子洗一盆。”“放客厅茶几上。”“我先吃点。”“渴死了。
”我把车厘子倒进洗菜篮。打开水龙头。冷水冲在鲜红的果子上。晶莹的水珠滚落。
我仔细地冲洗。每一颗都确保干净。沥干水。装进一个干净的玻璃水果盆。端到客厅茶几上。
张春梅已经坐在沙发上了。手机放在一边。她翘着腿。伸手就抓了一大把车厘子。塞进嘴里。
果核随意地吐在烟灰缸里。“嗯。”“还行。”“挺甜的。”她含糊地说。又抓了一把。
我回到厨房。拿出肋排。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冰冷的水冲在生肉上。粉色的肉。白色的脂肪。
水流带出淡淡的血水。洗完。放进锅里。加冷水。开火。蓝色的火焰舔着锅底。
冷水慢慢升温。水面开始浮起灰白色的泡沫。越来越多。聚拢在一起。我用勺子撇去浮沫。
倒掉。换上干净的热水。加入姜片。葱结。料酒。盖上锅盖。小火慢炖。接着处理鱼。
滑腻的鱼身。冰凉的鳞片刮干净了。露出粉白的肉。腹内已经清理过。我用水冲了冲。
在鱼身上划了几刀。抹上盐。淋了点料酒。放上姜片。葱段。等着备用。油烟机嗡嗡地响。
锅里炖着排骨。水汽顶着锅盖。发出轻微的噗噗声。肉香开始慢慢弥漫出来。客厅里。
张春梅吃车厘子的声音停了。电视换了台。在放一首吵闹的流行歌。王建国回来了。
带着一身外面的寒气。“哟!”“车厘子!”“好东西!”他乐呵呵地坐下。也抓了一大把。
“哪买的?”“挺新鲜!”“小默买的?”他看向厨房方向。“嗯。”张春梅应了一声。
“不错!”“懂事!”王建国嚼着果子。果核吐得啪啪响。“中午吃啥?”“红烧排骨。
”“清蒸鱼。”“好!好!”王建国很满意,“整两口!天宇中午回来吧?”“回。
”“让他也喝点。”“大小伙子了!”“该练练酒量了!”十二点刚过。赵天宇回来了。
书包往玄关地上一扔。“妈!饿死了!”“饭好没?”他冲进客厅。
一眼看到茶几上的车厘子。“哇!”“车厘子!”他直接端起玻璃盆。往自己怀里一倒。
红艳艳的果子滚了他一身。他抓起就往嘴里塞。“洗手去!”张春梅拍了他一下。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赵天宇嬉皮笑脸。又塞了几个。才跑去洗手。午饭摆上桌。
红烧排骨油亮诱人。清蒸鱼冒着热气。还有两个素菜。一个汤。王建国开了瓶白酒。
给赵天宇倒了小半杯。“来!”“尝尝!”“男人嘛!”赵天宇皱着眉。小心地抿了一口。
辣得直吐舌头。“咳!咳咳!什么玩意儿!”“慢慢来!”王建国哈哈大笑。“小默。
”张春梅叫我。“把电饭煲端过来。”“还有汤勺。”“拿个大点的。”我转身进厨房。
端出沉甸甸的电饭煲。放在餐桌旁的矮柜上。又拿来汤勺。递给她。他们开始吃饭。
没人叫我。排骨的浓香。鱼的鲜香。弥漫在餐厅里。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们。
王建国和赵天宇碰杯。赵天宇的脸皱成一团。又强行咽下。张春梅给赵天宇夹菜。
排骨堆满了他的碗。“多吃点!”“下午还要上课!”“用脑子!”他们吃得很快。
风卷残云。餐盘很快见了底。赵天宇放下筷子。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妈,我上学去了!
”他又抓了一把车厘子塞进书包侧袋。跑了。王建国喝干了杯底最后一滴酒。脸红红的。
“我去睡会儿。”他起身。摇摇晃晃走向卧室。张春梅还在慢条斯理地挑着鱼刺。
把最后一点鱼肉吃完。她放下筷子。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小默。”“收拾了吧。
”她站起身。也离开了餐厅。桌上杯盘狼藉。骨头。鱼刺。菜汤。米粒。沾满了桌面。
碗碟里剩下一点汤汁和油花。空气里是浓重的酒气。饭菜气。我走过去。拿起抹布。
开始擦桌子。油腻腻的。擦了好几遍。才勉强干净。把碗碟叠起来。端进厨房。
水槽里又堆满了。和早晨一样。冰冷的水再次冲在手上。洗洁精的泡沫。覆盖了油污。
水声哗哗。盖过了一切。下午。我回到二楼那个小房间。锁上门。从书桌最底下的抽屉里。
拿出一个不起眼的旧手机。黑色的。屏幕很小。款式很老。我按亮屏幕。
点开一个文件管理器。里面是分门别类的视频文件。日期标注清晰。文件名简单直白。
【卧室分配】【超市采购】【厨房命令】【车厘子】【午餐】【碗碟】我点开最新的一个。
【午餐】镜头对着餐厅。画面有些晃动。但很清晰。王建国给赵天宇倒酒。赵天宇皱眉喝下。
张春梅不断夹菜给赵天宇。排骨堆成小山。他们谈笑风生。没人看镜头一眼。也没人提起我。
仿佛我不存在。视频进度条走到最后。画面定格在他们离席的背影。我关掉视频。
把手机放回抽屉深处。推上。锁好。窗外。高墙的阴影拉得更长了。房间里光线更暗。
像一个盒子。傍晚。赵天宇放学回来。动静很大。书包砸在地板上的闷响。“妈!我电脑呢?
”他冲进客厅,声音带着烦躁,“我放客厅充电那个笔记本!”张春梅正在看连续剧。“啊?
没看见啊?”“你自己放哪儿了?”“我就放沙发上了!”赵天宇急吼吼地到处翻找,
“下午还在!充电线还在这呢!机器没了!”“是不是你爸收起来了?”“不可能!
他下午睡觉呢!”“那……”张春梅皱着眉,“家里进贼了?”“进什么贼!
”赵天宇猛地停下动作,像是想起了什么,目光刷地一下投向二楼,“楼上那个!
”他几步冲上楼梯。脚步声咚咚咚。像擂鼓。直奔我的房间。门没锁。他一把推开。
我正坐在书桌前。桌面上。放着一台银灰色的轻薄笔记本电脑。不是我的。
我的旧电脑是黑色的。笨重。放在桌子下面。赵天宇的眼睛瞬间瞪圆了。他冲进来。
指着桌上的电脑。“李默!”“你偷我电脑?!”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都鼓了起来。
我抬起头。看着他。没说话。“你哑巴了?!”他一步跨到桌前,伸手就要抢,“给我!
”他的手快要碰到电脑边缘时。我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清晰。“你的电脑?”“你确定?
”赵天宇的手停在半空。“废话!”他吼起来,“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这牌子!这型号!
这贴纸!都是我的!”电脑A面。贴着一个很显眼的骷髅头贴纸。“哦。”我点点头。
“那怎么在我桌上?”“还插着充电线?”赵天宇噎了一下。随即更加暴怒。“你问我?!
我还问你呢!肯定是你偷的!趁我不在家!偷偷拿上来!”“这是贼赃!”“我要报警!
”他声音很大。楼下的张春梅被惊动了。“天宇?怎么了?吵吵什么?”她踩着拖鞋。
也上来了。“妈!”赵天宇像找到了主心骨,指着桌上的电脑,“你看!我新买的电脑!
被他偷了!就藏在他桌上!”张春梅一看。脸色也沉了下来。她走进房间。
目光扫过桌上的电脑。又扫过我。带着审视和浓浓的怀疑。“小默。”“怎么回事?
”“天宇的电脑。”“怎么会在你这儿?”她的声音压着。但里面的冷意很明显。房间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