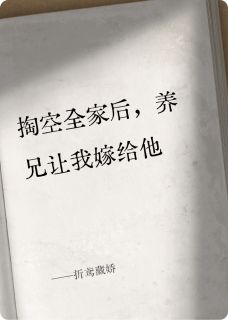
接下来的两天,凌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抑。前厅的喧嚣仿佛被冻结,
只剩下死一般的沉寂。苏夫人被禁足在偏僻阴冷的思过院,如同被打入冷宫,
往日仆从环绕的景象不复存在,只有两个面目刻板的老嬷嬷看守着。
送进去的饭菜一日比一日粗糙,曾经保养得宜的脸颊迅速凹陷下去,眼中只剩下绝望的灰败。
凌瑶则如同惊弓之鸟,被软禁在自己的绣楼里,她名下所有的店铺、田庄都被封查,
心腹管事被带走盘问,往日那些巴结奉承的丫鬟仆妇也作鸟兽散,
只留下几个战战兢兢的小丫头伺候着。她抱着膝盖蜷缩在床角,眼神空洞,
偶尔会突然尖叫哭喊,又或者歇斯底里地砸东西,彻底疯了。整个府邸的下人都屏息凝神,
走路踮着脚尖,说话压着嗓子,生怕一个不小心触怒了正处于暴怒边缘的凌威远,
或者……那位新晋掌权、手段莫测的珩之少爷。凌珩之的书房成了府中新的权力中心。
灯火彻夜不熄。
珠子的噼啪声、管事们低声禀报的嗡嗡声、以及凌珩之那低沉冷静、不带丝毫情绪的指令声,
不断从紧闭的门窗缝隙里透出来,像一张无形的网,笼罩着这座庞大的府邸。
凌鸢依旧扮演着她怯懦卑微的角色。她“吓得”闭门不出,
连饭食都只让贴身的小丫鬟送到门口。她“病”了,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
一副惊魂未定、弱不禁风的模样。府中众人或同情或鄙夷,
但无人再过多关注这个无足轻重的私生女。只有凌鸢自己知道,每一个寂静的深夜,
当府中彻底沉睡,她都会悄然起身,就着窗外微弱的月光,一遍遍翻阅着孙伯誊抄的账目,
推演着凌珩之可能的每一步棋路,思考着如何利用这场风暴。第三天清晨,
凌威远阴沉着脸坐在前厅主位,眼底布满血丝,显然一夜未眠。厅中气氛比前两天更加凝重,
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冰。凌珩之步履沉稳地走了进来,手中捧着一本厚厚的账册。
他依旧是那副清贵从容的模样,月白色的锦袍纤尘不染,只是眼下有着淡淡的青影,
昭示着连日的操劳。他身后跟着几个管事,个个屏息凝神,大气不敢出。“父亲。
”凌珩之躬身行礼,声音平稳无波,“三妹妹名下产业已清点完毕,公中亏空也已查实。
”凌威远猛地睁开眼,目光如电:“说!”“三妹妹名下十三间铺面,七处田庄,
其中五间铺面因经营不善早已抵押,实际可支配产业不足三成。所有产业变卖,按市价估算,
约可得银一万八千两。”凌珩之的声音清晰而冰冷,如同在宣读判决书。
凌威远的脸又黑了几分。“至于公中亏空,”凌珩之将手中的账册翻开,呈到凌威远面前,
指尖点在一行触目惊心的朱砂批注上,“经彻查,苏夫人确系挪用公帑白银三万七千两,
用于填补三**船队亏空,账目在此,人证物证俱在。”“砰!
”凌威远一拳狠狠砸在扶手上,紫檀木发出痛苦的**。“贱妇!蠢货!”他怒骂着,
胸口剧烈起伏。凌珩之面不改色,继续道:“此笔亏空,关系重大。下月新丝采买迫在眉睫,
西郊织坊坏账亦需填补,否则延误贡期,商誉受损,后果不堪设想。”他顿了顿,
目光平静地扫过厅中众人,最后落回凌威远身上,
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静:“儿子与几位管事商议,眼下唯有两条路可走。其一,
苏家倾囊相助。但据儿子所知,苏家近年亦不宽裕,三妹妹之前已从苏家挪借甚多,
恐难再拿出如此巨款。”他毫不留情地堵死了苏家这条路。“其二,
”凌珩之的声音陡然转冷,如同冰珠落地,“变卖府中……部分非核心产业,迅速回笼资金,
填补亏空,以解燃眉之急!”“变卖产业?!”凌威远猛地抬头,眼中怒火更炽,
“变卖哪里的产业?!我凌家基业,岂容……”“父亲息怒。”凌珩之微微躬身,
语气却带着一种掌控局势的强硬,“儿子所指,并非凌家根基产业。而是……”他的目光,
如同精准的刀锋,
缓缓转向了坐在下首、一直冷眼旁观、此刻却骤然绷紧了身体的二**凌霜!
“而是二妹名下,位于淮安府的那两间‘锦绣阁’。”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凌霜身上!凌霜那张总是带着冷淡疏离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她猛地抬起头,那双清冷的凤眸死死盯住凌珩之,里面充满了震惊、难以置信,
以及被猝然侵犯领地的滔天怒火!“凌珩之!”凌霜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前所未有的尖锐和冰冷,“你什么意思?!我的锦绣阁是外祖留给我的嫁妆!
是母亲(指她生母,已故的凌威远侧室)的遗物!你凭什么动?!”凌威远也愣住了,
眉头紧锁,显然没想到凌珩之会把刀砍向凌霜。凌霜一向低调,产业也相对独立,
他从未想过动这一块。凌珩之面对凌霜的怒火,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依旧平静得可怕:“二妹息怒。我并非觊觎你的嫁妆。只是眼下府中危机,牵一发而动全身。
淮安府那两间锦绣阁,地段极佳,经营稳健,若变卖,至少可得银两万五千两以上,
足以填补大半亏空,解府中燃眉之急。且这两间铺面与凌家核心盐务关联不大,
变卖影响相对可控。”他条理清晰,字字句句都打在“大局”和“危机”上,
将一场**裸的掠夺,包装成了迫不得已的壮士断腕!“与盐务关联不大?”凌霜怒极反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