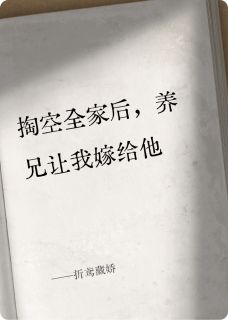
前厅的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描金绘彩的灯笼依旧明亮,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恐慌与寒意。空气中残留的熏香混合着未散的酒气,此刻闻起来只觉刺鼻。
凌威远端坐在主位的紫檀木太师椅上,脸色铁青,他手中的白玉扳指被捏得咯咯作响,手背上青筋虬结。
苏夫人瘫坐在一旁的绣墩上,钗环散乱,哭得双眼红肿,脸上的脂粉被泪水冲刷出狼狈的沟壑,紧紧攥着凌瑶的手。
而凌瑶早已哭得脱力,眼神涣散,瘫软在母亲怀里,嘴里只剩下无意识的、断断续续的呜咽:“我的船……我的货……全没了……全没了……”
厅中站满了人。大**凌珏、二**凌霜、三**凌瑶。几位大管事垂手肃立,大气不敢出。空气中只剩下苏夫人压抑的抽泣和凌瑶绝望的呓语。
当凌珩之带着凌鸢踏入前厅时,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带着审视、探究、以及一丝不易察觉的幸灾乐祸。
凌鸢敏锐地捕捉到那些目光。她迅速低下头,身体微微瑟缩,下意识地往凌珩之身后躲了半步,手指紧紧攥着他的衣袖一角,如同受惊过度、寻求庇护的雏鸟。那副惊惶无助、楚楚可怜的模样,瞬间激起了在场某些人的同情,也坐实了她“被凌瑶欺凌后吓坏了”的形象。
凌珩之感受到衣袖传来的轻微拉扯,脚步没有丝毫停顿,神色平静无波。他上前几步,对着主位上的凌威远躬身行礼,声音沉稳:“父亲,母亲。方才在园中遇到阿鸢妹妹受了惊吓,安抚片刻,来迟了,请父亲责罚。”他刻意强调了“安抚”和“惊吓”,将凌鸢的迟到归因于凌瑶的恶行。
凌威远阴鸷的目光在凌珩之身上扫过,又落在他身后低着头、肩膀还在微微颤抖的凌鸢身上,眉头拧得更紧。他看到了凌珩之手背上刺目的烫伤水泡,也看到了凌鸢那副惨兮兮的模样。这让他对凌瑶的怒火更添几分,却也因眼前的乱局而更加烦躁。
“哼!”凌威远重重一拍扶手,紫檀木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吓得凌瑶又是一哆嗦。“责罚?责罚谁?!一个两个都不省心!”他凌厉的目光扫过瘫软的凌瑶,“哭!就知道哭!凌家的脸面都让你丢尽了!”
“老爷!”苏夫人像是被踩了尾巴,猛地抬起头,尖声道,“瑶儿已经够惨了!她丢了那么多货,赔了那么多银子,您不安慰她,还……”
“银子?!”凌威远像是被点燃了火药桶,霍然起身,指着苏夫人怒喝,“你还敢提银子!我问你!她那船队冒险出海的钱是哪里来的?!我明明严令近期海运风险极大,不得轻动!她哪来那么大的胆子?!哪来那么多的本钱?!”
这一连串的质问如同重锤,狠狠砸在苏夫人心上。她脸色瞬间煞白,眼神闪烁,支吾着说不出话来。挪用银子填补凌瑶亏空的事,是她背着凌威远做的,本想等凌瑶的“暴利”赚回来再神不知鬼不觉地补上窟窿,却没想到等来的是灭顶之灾!
“我……我……”苏夫人嘴唇哆嗦着,求助的目光下意识地看向站在一旁的凌珩之,希望他能看在往日情分上,或者为了凌家大局,帮她说句话,哪怕只是模糊焦点。
“父亲息怒。”凌珩之适时地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盖过了苏夫人的支吾和凌瑶的呜咽,“三妹妹此次损失确实巨大。当务之急,是理清损失几何,尽快弥补亏空,稳住商号和债主,以免动摇我凌家根基。”
他这番话,看似在为凌瑶母女解围,实则精准地将话题引向了最核心的问题——钱!亏空的钱从哪里补?!
凌威远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但怒火更炽:“弥补?拿什么弥补?!她名下那些铺子、田庄,早就被她挥霍得差不多了!这次的本钱……”他阴冷的目光再次射向苏夫人,“苏氏,你告诉我,她这次出海的本钱,到底从何而来?!”
苏夫人被逼到墙角,冷汗涔涔而下。她求助无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是……是我挪用了……挪用了账上……预备下月采买新丝的一笔银子……”声音越说越低,最后几不可闻。
“轰——!”
仿佛一颗惊雷在厅中炸响!
所有管事都倒吸一口冷气!挪用公帑!这在规矩森严的凌府,是足以剥夺掌家权的大罪!更何况是在凌威远盛怒之下!
“苏!玉!锦!”凌威远一字一顿,声音如同来自九幽地狱,眼中是滔天的怒火和失望,“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私自挪用银子,纵容女儿胡作非为!你眼里还有没有家规!还有没有我这个家主?!”
“老爷!我……我也是为了瑶儿,为了我们凌家啊!我本想……”苏夫人彻底慌了神,语无伦次地辩解。
“为了凌家?!”凌威远怒极反笑,笑声冰冷刺骨,“我看你是为了你那不成器的女儿!为了填她的无底洞!你知不知道,下月新丝采买关系到明年开春的皇商供奉?!你知不知道,这笔银子若补不上,延误了贡期,我凌家会有灭顶之灾?!”
“扑通”一声,苏夫人再也支撑不住,滑跪在地:“老爷!老爷饶命!妾身知错了!妾身这就想办法!这就让苏家送银子来填补!求老爷开恩啊!”
凌瑶也吓得停止了哭泣,惊恐地看着盛怒的父亲和跪地求饶的母亲,浑身抖如筛糠。
凌威远胸口剧烈起伏,看着跪在脚下、仪态尽失的苏氏,眼中是毫不掩饰的厌恶和冷酷。他深吸一口气,强压怒火,目光如刀般扫过厅中众人,最后落在一直垂手肃立、仿佛置身事外的凌珩之身上。
“珩之。”凌威远的声音带着压抑的疲惫和不容置疑的命令,“你立刻去清点凌瑶名下所有产业,评估损失,同时彻查公中账目,看看苏氏究竟挪用了多少!所有亏空,三日之内,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数目和……填补方案!”他将“填补方案”四个字咬得极重。
“是,父亲。”凌珩之躬身领命,声音平静无波,仿佛只是在接受一项寻常的差事。他抬起头,目光不经意地与站在角落、依旧低垂着头、仿佛被眼前变故吓呆了的凌鸢,有过一刹那极其短暂的交汇。
凌鸢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掩去了眼底一闪而过的、冰冷的了然。凌珩之的第一步棋——“挪用公帑”这把刀,已经精准地悬在了苏氏母女的头顶!而且,是凌威远亲手递给了他这把刀!
凌威远疲惫地挥挥手,语气森寒:“夫人禁足思过院,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探视!凌瑶名下所有产业,暂由珩之代管!府中内务……”他凌厉的目光扫过几个管事嬷嬷,“暂由王嬷嬷(凌珩之安插的人)协理!都给我滚下去!”
最后一声怒喝,如同惊雷。
众人如蒙大赦,纷纷行礼告退,脚步匆忙,生怕被这滔天怒火波及。
苏夫人被两个粗壮的婆子强行架起,拖了下去,口中犹自哭喊着“老爷开恩”。凌瑶则被丫鬟半扶半抱地带走,眼神空洞,如同失了魂。
偌大的前厅,瞬间只剩下凌威远沉重的喘息声,以及角落里,那个依旧低着头、仿佛被遗忘的影子——凌鸢。
凌威远疲惫地揉着眉心,目光扫过角落,看到凌鸢那副惊魂未定、单薄可怜的样子,想到她方才也被凌瑶当众欺凌,心头那点残余的、对“污点女儿”的厌弃,似乎被一丝极其微弱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烦躁所取代。
“你还杵在这里做什么?”凌威远的声音带着不耐,却没了平日的刻薄,“还不回你的院子去!晦气!”
“是……父亲。”凌鸢的声音细若蚊蚋,带着浓重的鼻音和哽咽,身体又是一颤,仿佛被吓到。她深深地福了一礼,动作带着刻意的僵硬和惶恐,然后低着头,脚步踉跄地、几乎是逃也似的退出了前厅。
走出灯火通明的前厅,踏入回廊的阴影,夜晚的凉风拂过脸颊。凌鸢脸上那惊惶无助的表情迅速褪去,只剩下冰冷的平静。
她微微侧头,眼角的余光瞥见不远处书房的方向——凌珩之已经带着两名心腹管事,步履沉稳地走了进去。他手中,握着凌威远刚刚赋予的、足以撬动凌家根基的权力钥匙。
凌鸢的唇角,在无人看见的阴影里,勾起一抹极淡、极冷的弧度。她拢了拢衣襟,没有回自己偏僻的西跨院,而是脚步一转,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更深沉的夜色中,朝着府邸另一侧、一个不起眼的、堆放杂物的偏院走去。那里,住着一个“病弱”的、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的账房老仆——一个曾经受过柳氏(凌鸢生母)恩惠、如今只忠于凌鸢的“暗棋”。
她需要知道,苏氏挪用的具体数额,以及……凌珩之接下来会如何利用这把刀。
夜色如墨,凌府这座庞大的府邸,在表面的风暴平息后,更深沉的暗流,正无声地涌动。权力的棋盘上,两颗最危险的棋子,已经开始各自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