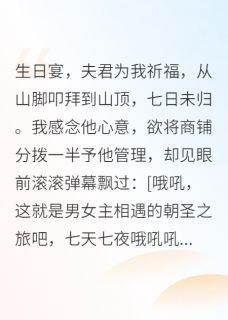
生日宴,夫君为我祈福,从山脚叩拜到山顶,七日未归。我感念他心意,
欲将商铺分拨一半予他管理,却见眼前滚滚弹幕飘过:[哦吼,
这就是男女主相遇的朝圣之旅吧,七天七夜哦吼吼~][炮灰夫人好惨啊,
本来心善想抬女主为贵妾,殊不知只是个血包……][还有俩月他们的团宠宝宝就上线了,
搓手手。]他们的团宠宝宝?我眉头一皱。可夫君他……根本不行啊!
1“女主”挺着孕肚上门时,我正躺在院子中晒太阳。生日宴看到弹幕后,我派老家人上山。
将夫君衣衫不整地摁在禅院中,自此“气”得一病不起。公婆是不能侍奉的,
庶务是不能管理的。唯独燕窝烧鸭胭脂露,一刻都不得缺。那女子嫌恶地盯着我手中鹅腿,
察觉我目光时又故作蒲柳之姿,盈盈下拜,惹人爱怜。“夫人,我有喜了,是阮郎的。
”大丫鬟彻芝眼睛一瞪,一扫帚就打了过去。“胡说什么,姑爷软这种事也能随意张扬吗?
哦……阮郎,不好意思听错了。”我掀起眼皮。彻芝这傻大个向来手狠,
又早听说这女子打算先抢男人后抢钱。怨恨颇深。只一下,
就将柳月娘**在外的手背抽得通红。于是我放心地把眼睛闭上。“彻芝,去找你姑爷!
才干了校尉,就有骗子上门了,这可了得?”彻芝扔了扫帚,往门外走,
一边走一边拿扫帚抽地。“姑爷最是诚实,跪瓷片子时说了没有女人就是没有女人!
等姑爷回来,我当他面,铁砂掌打烂骗子的嘴!”尘土飞扬中,柳月娘肉眼可见地慌了。
“夫……夫人,我是月娘呀,夫人上巳节看我表演时,还和阮郎说,很满意我,
要抬我给阮郎做贵妾呢!”彻芝顿了一顿,哈哈大笑。
“我家**还指着隔壁张嫂家的猪要给姑爷做妾呢,现在还不是挂那当腊肉了,柳姑娘,
姑爷惧内,不可能纳妾的。”柳月娘被吓得花容失色,连连后退,踉跄地退出大门。
彻芝叉着腰回头一挑眉,我俩对视一笑。2阮修文搂着柳月娘进院时,
还带着满脸愠怒的阮母。弹幕唰唰飘过。[这母子俩真不要脸,
偷了夫人的头面捐官还趾高气扬,像自己的钱。][侍女真威武!
但这么狠以后会被穿小鞋吧呜呜呜。][真不想夫人死,
主要看不惯这对狗男女坐享夫人的商业江山。]阮母尚不知自己偷钱行迹败露,
还一副大户人家老封君的姿态。拐杖砸地,跺得“铛铛”响:“阮盛氏!你这女子好不懂事!
我阮家三代单传,当初便讲你要有孕才能进门,你不肯,你瞧瞧,误我子嗣!
”阮修文倒是郎情妾意,含情脉脉。“珠英,你多年无子,便许月娘个平妻之位,
老了你也有个依靠,不是吗?”我摸摸手边黄梨木方桌,瞧瞧我真金白银买回的宅子,
再看看眼前这仨分不清大小王的烂人。手中茶碗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你们他妈的是不是忘了啥叫入赘!盛阮氏!”彻芝配合地挥舞起了扫帚。柳月娘一见扫帚,
登时脚软,直接瘫在原地。而阮修文训练有素,“扑通”一声儿跪下,嘴中词儿不假思索,
一溜就吐了出来。“娘子!有你才有今天,你说往东我绝不往西,你说杀狗我绝不喂鸡!
”我跐着脚踏,斜眼看向已经气到发抖又不敢出声的阮母。突然莞尔一笑。
“平妻也不是不可以商量,毕竟我与妹妹情同姐妹,效仿娥皇女英也未尝不可。
”弹幕开始还是一片哈哈哈笑话阮修文,及至我话一出,顿时哀嚎一片。[完了完了,
夫人被下降头了吗?怎么就答应了。][嘻嘻嘻,不懂你们为什么喜欢个死人,钱包而已,
还能多有智商,坐等宝宝出生喽。][不好看,业务繁忙,我要去下一个世界了。
]我瞧着阮母得意洋洋,望着阮修文与柳月娘相携而去的身影。笑了。放松警惕,
才能收利息后跑路嘛~3近来阮修文早出晚归准备喜事儿,面上神色却一天不如一天。
因为我雇了几个地痞小流氓,天天去阮修文的值房惹事儿。这几个活宝当着阮修文上司的面,
撒泼犯浑要赌债。被揪住就开始放赖。“我们要找姓阮的要债,你姓阮又没欠债,
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在这儿要债?”强词夺理,气得阮修文顾不得体面,
亲自抄了板子上去揍。这番操作,不仅仅是弹幕,连彻芝都不理解。“**,
您这不是一天二十两,上门送人头嘛?”我只笑,让她且看着。不过半个月,
阮修文便臭着脸,不去当值,只天天把自己关书房了。[笑死,
县太爷和我司HR一样会说话,“哎呀,我也是为了你好,看看得罪谁了,
这月银子照付”阴阳怪气.jpg。][???没看懂,咋就被辞了?
][哈哈哈哈哈夫人好谋划啊,你要是老板,你愿意要一个麻烦缠身的员工吗?
]但这哪够呢,我又派了以前总跟他“沆瀣一气”的小伙计,去书房和他要债。
那伙计只一进去,就听得书房中笔墨纸砚土定瓶,噼里啪啦一顿响。
阮修文的声音高得都已经变调。“钱钱钱!商贾之人果然无情无义,我可是从九品校尉,
难道会缺了你这点阿堵物?”彻芝神色迷茫,
一边给我打扇一边嘀咕:“那小六子不是说县官辞退了姑爷么,怎么姑爷还这么理直气壮。
”我一口一颗白糖罂荔枝,甜得口角生香。“男人都要面子,你瞧,
咱们的大鱼这不就要来了吗?”瞧着蹑手蹑脚从书房门口退出,又溜进库房的阮母。
我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4阮母溺爱阮修文,见不得她亲亲好儿子在我手上吃亏。
从前我只是有所猜忌。自有了弹幕提醒后,我顺利揪住了她从库房里顺东西当掉的证据。
可笑的是她不光要拿出去卖,还要回到我面前摆阔。不过这年头,婆婆只自己偷东西,
而不是集结全村鸡鸭鹅狗男女老少逼媳妇交出铺子,已着实算个好人。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先记着账。近来阮修**校尉,开销骤增,单靠阮母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野心。
他索性找了伙计里应外合。阮修文自诩娶平妻是正经的婚事。
阮母又卯足了劲儿要证明阮修文才是一家之主。想必要这两位偷盗的数额不会少。
我满意地看着阮母抱着两个包裹,鬼鬼祟祟溜出门去。“去,彻芝,叫当铺那头收网了。
”5我赶到当铺时,门口已经围满街坊四邻,热闹极了。阮母偷出的金银珠宝撒了一地,
本人正躺在地上撒泼。“哎呀,老身攒了这么多年的体己,这掌柜的张嘴就诬陷老身是偷的,
天理何在呀!”当铺钱掌柜抿着嘴,梗着脖子,自带宁死不屈的样子。“你是惯犯,**!
我已报官,等官家来,公道自在人心!”阮母听见报官,显然有几分慌。眼珠子滴溜一转,
正好看见了混在人群中的我。“儿媳呀!有人要冤死你娘!
”她随手揪过一个看热闹的老妇人,指着我。“大姐你瞧瞧,
我媳妇可是咱十里八村有名财主,我犯得着偷东西吗?他红口白牙污人清白,赔钱!
必须赔钱!”蔡知县也正在这时出现。群情激愤,义愤填膺。
阮母带头喊着要蔡知县将“黑心当铺”查封。衙役已围上钱掌柜。我在此时上前一步。
“且慢。”迎着蔡知县的目光,我柔柔一笑。“大人,官是我让报的。“毕竟丢东西的人,
是我。”6县衙里,我扯着小手绢装柔弱小女子。把自己说得可怜兮兮。父母早亡,
守着偌大家业招赘。又多年无所出,只得含泪同意夫君再娶。谁想再娶出了银子还不够,
还要被偷嫁妆添补。方才在当铺门口坚贞不屈的钱掌柜,这会儿表演起来比我还卖力。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表明阮母如何几次三番销赃,自己又是如何碍于小主人颜面忍气吞声,
敢怒不敢言。我们主仆二人,泪洒县衙。闻者伤心,听者落泪。从前我姑息养奸时,
弹幕骂我软弱可欺,很是活该。这会儿全是拍案叫好的。[妙绝!夫人会演,
钱掌柜也会演哈哈哈哈。][我本来还担心没监控没指纹怎么证明东西是自己的,
哈哈哈销赃销人家家里去了!][这情节我爱看了,小三上位文变大女主爽文,
夫人打他丫的!让他们占你财产还要骂你短命鬼!
]最妙的是蔡知县前几日方为了地痞流氓大闹县衙之事心存不满。正愁一口郁气没地方出,
于是一拍惊堂木,将阮修文一同拘到县衙。“大胆阮修文!竟敢纵容母亲侵夺正妻嫁妆!
该当何罪!”阮母和阮修文人都傻了。阮母话都说不流畅:“大人,
这这这……这盛氏可是我家人,我不过拿自己儿媳妇的东西,有何过错。
”蔡知县惊堂木又一响。“刁妇竟还敢质疑本官,来人,给本官打!”阮母被摁倒打板子,
木板与皮肉接触噼啪作响。阮修文求饶不成,终于将视线放在我身上。“珠英,夫妻一场,
娘亲遭此大难,你不心疼吗?”我瞧着他孝写满脸的模样,泪流满面地点点头。能不心疼吗,
开审前我塞了蔡知县一千两的银票。一响五百两!心疼死我了。“那你快让大人放了娘亲,
不要打了!”我用手帕挡着脸,温柔地应承了下来。“好的,夫君,全听你的吩咐。
”然后我直起了腰。“大人,婆母年老,怕是承受不住如此酷刑。”在阮修文欣慰的目光中。
我话锋一转。“还是打夫君吧!毕竟一切都是他指使的!
”7我带来了柜上与阮修文里应外合的伙计。那伙计一个滑跪,磕头痛哭控诉三件套。
“他逼我的,我对不起东家,我撞死算了!”但他不撞死,他一边渲染自己该死,
一边把阮修文的事全抖出来了。一个没有固定差事的人,为什么能让烟花女子有喜呢。
怎么认识的?是认识一次吗?银子哪来的?蔡知县也是个男人,这点花花肠子还是有的。
但蔡知县宠妻名声在外,夫妻和睦。拿妻子的嫁妆去嫖,最重要的还被放在光天化日下示众,
真是斯文扫地。蔡知县也不揪着阮母了。十八套刑罚全招呼在了阮修文身上。
阮母还来不及高兴自己免于责罚,就见心头肉被打到皮开肉绽。一时呼天喊地,
连叫家门不幸,娶了如此丧门星。眼见阮修文是一点一点,连求饶的声音都弱了。
阮母彻底急了。“你这堂官收我银子又撵走我儿,天下乌鸦一般黑,
莫不是与我那不守妇道的媳妇滚在了一处?才如此袒护?”蔡知县为官十载,
何时见过当堂戳破他贿赂的,脸都青了。“大胆刁妇!口出狂言,竟敢当堂污蔑本官!来人,
将这对不知悔悟的母子打入大牢!老的罚去舂米,小的拉去挖河!
判罪民阮修文与盛掌柜和离!欠盛掌柜的银钱用家资抵债!除去阮修文簿中姓名,永不录用!
”阮修文被拉走之前,拼死地拉住我的衣袖。“珠英……珠英,我对不住你,
但月娘的孩子是咱们唯一的依靠,请你一定照顾好孩子!”……如此离谱,
连之前盛爱团宠宝宝的人都看不下去了。[这他妈是什么古早文男主,这么渣!][和离啊,
你听不懂啥叫和离吗?奸夫**臭不要脸,呵忒!]我亦是强遏制住自己翻白眼的冲动,
决定最后送阮修文个惊喜。“你放心去吧,我定照顾妹妹。”8阮修文放心地走了。
我迅速变卖了阮家几亩田,乡下院子,并着阮母半生体己。脚底抹油,溜了。
溜之前我还特意留了个耳聋门童对付来寻人的柳月娘。“不是文家!啥软?什么?
你要给我修脚?”“钱!我要赎身的银子呀,阮家儿子要生青楼了!”“漏了找桶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