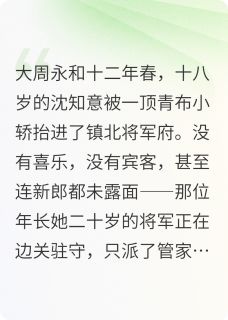
大周永和十二年春,十八岁的沈知意被一顶青布小轿抬进了镇北将军府。没有喜乐,
没有宾客,甚至连新郎都未露面——那位年长她二十岁的将军正在边关驻守,
只派了管家来接她过门。沈知意坐在新房中,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嫁衣上粗糙的绣线。
这件嫁衣是继母临时从旧衣铺子里买来的,针脚歪斜,颜色暗沉,
与她曾经幻想过的凤冠霞帔相去甚远。烛光摇曳,映照出她清丽却苍白的脸庞。"夫人,
将军传话回来,说边关战事吃紧,恐怕三个月内都无法回府。"丫鬟春桃小心翼翼地禀报。
沈知意轻轻"嗯"了一声,自己掀开了盖头。铜镜中映出一张陌生的脸——那是她自己,
却又不像是她自己。曾经的沈家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如今却成了镇北将军萧景珩的续弦,一个为了家族利益而被牺牲的棋子。"替我更衣吧。
"她轻声吩咐,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春桃犹豫道:"夫人不等将军...""他不会来的。"沈知意打断她,
自己解开了嫁衣的系带,"从今往后,在这府中,我们只需做好自己的本分。"三个月后,
萧景珩终于回府。沈知意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夫君——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
眉宇间刻着深深的皱纹,眼神锐利如刀。他看她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件无关紧要的摆设。
"将军。"沈知意福身行礼,声音轻柔。萧景珩只是点了点头,
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不到一瞬,便大步走向书房。"不必准备我的晚膳,我在书房用。
"春桃气愤地跺脚:"夫人,将军怎能如此待您!"沈知意摇摇头,唇角勾起一抹苦笑。
她早已知晓,萧景珩的前妻柳如烟是京城第一才女,三年前病逝后,萧景珩便再未展颜。
她这个被硬塞进来的续弦,又算得了什么呢?日子如流水般过去。萧景珩常年驻守边关,
偶尔回府也是独居书房。沈知意渐渐习惯了这种被忽视的生活,她在后院辟了一方小天地,
种花养草,吟诗作画,倒也自得其乐。直到那个雨天。
沈知意在整理书房时——这是她为数不多被允许进入的地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暗格。
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一叠诗稿和一幅画像。画像上的女子眉目如画,温婉动人,
正是萧景珩的亡妻柳如烟。诗稿上的字迹娟秀飘逸,字里行间满是才情。
她轻轻抚过那些纸张,忽然明白了萧景珩为何对她如此冷漠。在他心中,
永远住着一个无法替代的人。"夫人在看什么?"冰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沈知意惊得差点打翻烛台。萧景珩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脸色阴沉得可怕。"将军恕罪,
妾身只是..."她慌乱地想要解释。萧景珩大步上前,一把夺过她手中的诗稿,
眼中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谁准你动如烟的东西?"沈知意垂下眼帘,
长睫在脸上投下一片阴影。"妾身知错,请将军责罚。"萧景珩盯着她看了许久,
最终只是冷冷道:"出去。"那夜,沈知意辗转难眠。
她提笔写下一首诗:"深院无人独倚楼,月明如水照孤愁。君心似铁妾如絮,
随风飘荡不自由。"写完后,她将诗笺悄悄放在了书房门口。第二天清晨,
她发现诗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被揉皱后又被抚平的纸——她的诗被批改了,
字迹苍劲有力,是萧景珩的手笔。"深院无人独倚楼,月明如水照孤愁。君心非铁妾非絮,
何必自怜叹不自由。"沈知意捧着那张纸,忽然笑了。这是他们成亲以来,
第一次真正的交流。从此,诗词成了他们之间无声的对话。沈知意常在书房留下新作,
而萧景珩总会批改后放回原处。有时是一两个字,有时是整句重写。渐渐地,
批语中开始夹杂着简短的评论。"用'寒'字不如'清'字贴切。""末句意境甚佳。
"半年后的一个雪夜,萧景珩醉酒归来。沈知意听到动静,披衣起身,
在回廊上遇到了踉踉跄跄的将军。"如烟..."萧景珩眼神迷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
"你回来了..."沈知意僵在原地,心如刀割。但当她看到萧景珩眼中滚落的泪水时,
所有的委屈都化作了心疼。"将军,您醉了。"她轻声说,扶着他往卧房走去。
萧景珩突然停下脚步,捧起她的脸仔细端详。"不,
你不是如烟..."他的声音忽然清醒了几分,"你是...知意。"那一刻,
沈知意的心跳漏了一拍。这是他第一次叫她的名字。第二天清晨,萧景珩出现在她的院中,
神色复杂。"昨夜...多谢夫人。"沈知意正在修剪一株梅枝,闻言手上一抖,
剪掉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将军不必言谢,这是妾身分内之事。"萧景珩走近几步,
目光落在她冻得通红的手指上。"天寒地冻,夫人何必亲自做这些粗活。""闲来无事,
打发时间罢了。"她轻声回答,不敢抬头看他。一阵沉默后,
萧景珩突然道:"夫人的诗...写得很好。"沈知意惊讶地抬头,正对上他深邃的目光。
那一瞬间,她仿佛看到了冰封已久的湖面裂开了一道缝隙。"不及将军批改得好。
"她微微一笑,眼中有了光彩。从那天起,萧景珩回府的次数多了起来。
他会在晚膳时分出现在饭厅,沉默地吃完她亲手准备的饭菜;他会在她弹琴时驻足聆听,
虽然从不评价;他还会在她生病时派人送来珍贵的药材,却从不亲自探望。
但沈知意已经心满意足。至少,他不再当她是空气。春天来临时,萧景珩邀她同游后山。
那是他们第一次并肩而行,沈知意紧张得手心冒汗,不小心踩空了一阶石阶。
萧景珩眼疾手快地扶住她的腰,两人距离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小心。"他低声道,
却没有立刻松开手。沈知意闻到他身上淡淡的松木香,
混合着铁锈般的气息——那是常年征战的男人特有的味道。她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回府的路上,萧景珩突然问:"夫人可会骑马?"沈知意摇摇头:"妾身自幼体弱,
未曾学过。""明日我教你。"他说完,大步走开了,留下沈知意站在原地,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二天,萧景珩果然带她去了马场。
他亲自为她挑选了一匹温顺的母马,耐心地教她如何上马、握缰。当他从身后环住她,
手把手教她控制马匹时,沈知意几乎忘记了呼吸。"放松,跟着马的节奏。
"他的声音近在耳畔,温热的气息拂过她的耳垂。一个月后,沈知意已经能够独自骑马小跑。
萧景珩总是骑着那匹名为"追风"的黑色战马跟在她身侧,目光中带着她看不懂的情绪。
夏日的一个傍晚,沈知意在凉亭中弹琴。那是一首她自己谱的曲子,婉转缠绵,
诉说着无法言明的心事。弹到动情处,她轻声吟唱:"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我知道。"沈知意猛地回头,琴弦"铮"地一声断了。
萧景珩不知何时站在亭外,眼中是她从未见过的温柔。"将军..."她的声音颤抖着。
萧景珩走进凉亭,轻轻握住她受伤的手指。"流血了。"他掏出手帕,小心翼翼地包扎。
"不过是小伤..."沈知意试图抽回手,却被他握得更紧。"对我而言,不是。
"萧景珩抬头直视她的眼睛,"知意,我..."就在这时,管家匆匆跑来:"将军,
边关急报!"萧景珩的表情瞬间恢复了往日的冷峻。他松开沈知意的手,接过信函快速浏览,
眉头越皱越紧。"备马,立刻召集亲兵。"他简短地命令,然后转向沈知意,欲言又止。
沈知意强忍泪水,勉强笑道:"将军军务要紧,妾身...等您回来。
"萧景珩深深看了她一眼,突然上前一步,将她拥入怀中。这个拥抱短暂而有力,
然后他转身大步离去,没有回头。沈知意站在原地,手中还攥着那条沾了血的手帕。
她不知道,这一别,将是漫长的两年。萧景珩离去的第三个月,沈知意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这个消息让她又惊又喜。她小心地抚摸着自己尚且平坦的腹部,
想象着那里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她和萧景珩的孩子。春桃高兴得直抹眼泪,
立刻要去给边关送信,却被沈知意拦住了。"将军正在前线作战,不能让他分心。
"她轻声说,眼神温柔而坚定,"等他凯旋归来,再给他一个惊喜。"随着肚子一天天隆起,
沈知意的诗作也越发温柔。她写春日里绽放的海棠,写夏夜中闪烁的萤火,
写秋日金黄的稻田,写冬日皑皑的白雪。每一首诗里,都藏着对远方夫君的思念与期盼。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写罢,她轻轻叹了口气,
将诗笺收入匣中。这些诗,她已经很久没有放在书房了——自从萧景珩出征后,
那里便落了锁,钥匙被管家郑重地收着,说是将军的命令。怀孕七个月时,
边关传来噩耗——萧景珩所率部队遭遇埋伏,全军覆没,将军本人下落不明,恐已战死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