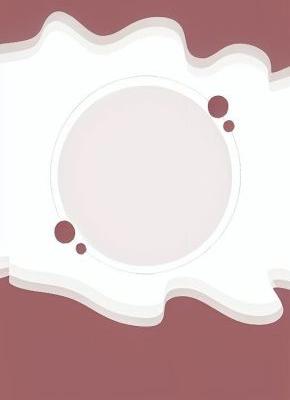
翌日清晨,天光微熹,透过窗纸洒入书房,在布满灰尘的空气里切割出几道朦胧的光柱。
沧溟早已站在窗边,他无需凡俗的睡眠,只是静默地站了一夜,如同龙宫中那些亘古不变的玉雕。凡间的夜晚,比他想象的更为喧嚣——虫鸣、风声、更夫遥远的梆子声,还有隔壁卧房里,那清浅而规律的呼吸声。这些细微的声响,构成了一首陌生的、属于人间的夜曲。
门被轻轻推开,沈清弦端着简单的早膳走了进来。一碗清可见底的米粥,一碟酱菜,还有一个白水煮蛋。她已换上了一身干净的月白襦裙,发髻梳得整齐,只是眼底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公子醒了?”她将托盘放在小几上,目光快速扫过纹丝未动的床铺,微微一怔,却体贴地没有多问,“用些早膳吧,只是粗茶淡饭,莫要嫌弃。”
沧溟的目光落在那些食物上。龙宫宴饮,琼浆玉液,龙肝凤髓亦不稀奇,何曾见过如此…素净之物。他依着昨日“进食”的经验,坐到几前,拿起竹筷。
米粥寡淡,酱菜咸涩,煮蛋则带着一股纯粹的、属于生命本源的气息。他进食的动作很慢,一举一动都透着一种近乎仪式的优雅,与这简陋的环境格格不入,却又奇异地和谐。
沈清弦在一旁静静看着,心中那份异样感愈发清晰。这人失忆了,言行举止间的贵气与习惯却无法抹去。她越发肯定他来历不凡。
“公子,”等他用完,沈清弦收拾着碗筷,状似随意地开口,“我今日要去前面书铺打理,你若觉得烦闷,可以在院中走走,或者……看看书?”她指了指那一架子的书籍。
沧溟顺着她的指引看去。那些以竹简、纸张承载的文字,在他眼中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他点了点头。
沈清弦去了前铺,隐约传来她与偶尔上门顾客的交谈声,声音清软,耐心周到。
沧溟走到书架前。指尖拂过书脊,抽出一本《山河志异》,书页泛黄,带着岁月的沉香。他翻开,里面记载着凡间的地理风貌、奇闻传说,甚至还有一些关于“龙王布雨”、“山神显灵”的志怪故事,写得活灵活现,在他眼中却显得粗陋而失真。凡人以自己的想象,揣度着他们无法理解的存在。
他又拿起一本《诗经》,翻开一页,恰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描绘男女思慕的诗句,直白而热烈,与他所修持的清冷神道背道而驰。情爱,这便是情劫需要触及的领域么?
他正凝神间,沈清弦端着一杯清茶走了进来,见他手持书卷,眉眼间露出一丝浅淡的笑意:“公子也喜读书?”
沧溟放下书卷,没有回答,反而问道:“这些书,你都读过?”
“大多读过。”沈清弦将茶放在他手边,“家父在时,常督促我读书明理。虽不能科考,却也觉得书中自有天地。”
她的目光落在《诗经》那页,脸上微微泛红,连忙移开视线,转而看到桌角那几张她平日练字的纸,上面是她临摹的卫夫人簪花小楷,清秀工整。
“胡乱写的,让公子见笑了。”她有些赧然。
沧溟的目光扫过那些字。在他看来,笔画间虽力求工整,却失之绵软,少了风骨。他忽然开口:“笔。”
沈清弦愣了一下,随即会意,忙从笔架上取下一支兼毫笔,又在砚台中研墨。
沧溟接过笔,触手是凡间劣质毛笔的粗糙感。他蘸墨,铺开一张新纸。沈清弦屏息在一旁看着。
只见他落笔,手腕悬停,动作看似随意,笔下却如有千钧。墨迹淋漓,并非楷书,也非行草,而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古老字体,结构奇古,笔画如刀刻斧凿,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苍茫而威严的气息,仿佛不是写字,而是在铭刻某种法则。
那是一个“溟”字。取自他神讳之一,意为浩瀚之海。
一字既成,满室皆静。连窗外海棠树上的鸟雀似乎都噤了声。
沈清弦怔怔地看着那个字,只觉得心口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撞了一下。这字……绝非凡俗书生能写得出!她甚至能感觉到那笔墨间蕴含的某种难以言喻的压迫感。
“你……”她张了张嘴,却不知该问什么。
沧溟放下笔,看着纸上墨迹未干的字,似乎也察觉到自己无意间流露的异常。他沉默片刻,才道:“依稀……记得如何写。”
这个解释如此苍白,沈清弦却无法追问。她看着那个“溟”字,又看看他深邃的眼眸,一个念头隐隐浮现。
“你……可是想起了自己的名字?”
沧溟迎上她探究的目光,那目光清澈,带着纯粹的疑问与关切,并无畏惧,也无贪婪。他想起龟丞相的叮嘱,需得有一个合理的身份。
“沧溟。”他缓缓开口,声音低沉,仿佛这两个字本身就带着某种重量,“似乎……是这个名字。”
“沧溟……”沈清弦低声重复了一遍,只觉得这名字与他的人,与他写下的字,无比契合,仿佛天生就该属于他。“很好听。”
她看着那张写着“溟”字的纸,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道:“那……你还想起了什么?家在哪里?可有亲人?”
沧溟(此刻或许该称他为沧溟了)摇了摇头,墨黑的眸子里适时地流露出恰到好处的空茫与一丝……不易察觉的疏离。
“只有这个名字。”
沈清弦看着他,心底那点疑虑被浓浓的同情压了下去。忘了来处,忘了归途,只记得一个名字,该是何等的彷徨无助。她柔声道:“想不起来便慢慢想,不急。你既记得名字,便是好的开端。”
她小心地收起那张写了“溟”字的纸,仿佛那是什么珍贵的物什。“沧溟公子,你暂且安心住下。外面……或许还有人在寻你,我会留意的。”
沧溟看着她小心翼翼的动作,和她眼中纯粹的善意,心湖那圈陌生的涟漪,似乎又微微扩大了些许。
这凡间女子,与他预设的“情劫对象”,似乎……并不完全一样。
而沈清弦,则拿着那张字纸,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前铺。她看着窗外熙攘的街道,再低头看看手中力透纸背、气象万千的字迹。
沧溟。
她轻轻念着这个名字,仿佛要将它刻进心里。他究竟是谁?来自何方?这场突如其来的相遇,是福,还是祸?
日子便如溪水般,看似平静地向前流淌。
沧溟,这个名字如同投入沈清弦心湖的一颗石子,漾开的涟漪尚未平息,却已不得不融入日常的琐碎。他依旧“想不起”过去,顺理成章地在书铺后的小院住了下来。
起初,是十足的笨拙与格格不入。
沈清弦在前铺招呼客人,售卖笔墨,或是替人代写书信时,沧溟便留在后院。他试图帮忙打扫,手中那把寻常的竹帚在他手里却显得沉重而不听使唤,扫地的动作生硬得像在执剑,扬起的灰尘让他那习惯龙宫澄澈空气的感官微微不适。他看着沈清弦利落地提水、生火、淘米,那些在她做来流畅自然的动作,于他而言,每一步都如同破解一道陌生的法诀。
他站在灶前,看着那跳动的、橙红色的凡火,眼中闪过一丝极淡的审视。龙族控水御火本是天赋,但这需要小心控制的、用于烹煮食物的微弱火焰,让他感到一种被拉入尘埃的桎梏。
沈清弦看在眼里,并不说破,只是在他又一次险些打翻水桶时,轻柔地接过,笑着说:“这些粗活我来就好,沧溟公子若是得闲,不如帮我看看前日新进的那批书,可有刻本不佳、需要剔除的?”
她给了他一个体面的、符合他“身份”的差事。
沧溟默然应下。于是,他大部分时间便坐在书房靠窗的位置,翻阅那些堆积的书籍。阳光透过窗棂,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投下安静的光影。他看书极快,过目不忘,那些经史子集、杂谈志怪在他眼中毫无秘密可言。偶尔,他会将一本刻本模糊、或内容荒诞不经的书册单独放置一旁。
沈清弦得空时来看,发现他挑出的,竟都是些真正有瑕疵或价值不高的书籍,无一错漏。她心中的讶异更深,却也只化作一声轻叹,将疑惑压入心底。
这日午后,天气有些闷热。沈清弦在井边浆洗衣物,额上沁出细密的汗珠。沧溟坐在海棠树下,目光落在她因用力而微微泛红的手腕上。凡人的躯体,竟是如此容易疲累与沾染尘垢。
他忽然起身,走到井边。
“我来。”他声音依旧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
沈清弦一愣,还未反应过来,他已接过她手中那件浸了水的厚重外衫。然而,下一刻,只听“刺啦”一声细微的响动——那棉布的质地,竟受不住他下意识施加的、未经驯化的力道,从袖口处裂开了一道口子。
两人俱是一怔。
沧溟看着手中破裂的衣物,再看向沈清弦错愕的神情,那双古井无波的眸子里,第一次掠过一丝清晰的、名为“无措”的情绪。他习惯了移山倒海的力量,此刻却败给了一件凡间衣衫。
沈清弦看着他僵立的样子,先是惊讶,随即,眼底漫上一点真切的笑意。她接过那件裂了的衣服,声音温和,带着安抚的意味:“不碍事的,公子,这布料旧了,本就容易破。缝几针就好。”
她没有丝毫责备,反而觉得此刻显得有些笨拙的他,比平日里那副清冷疏离、仿佛随时会羽化登仙的模样,要真实可亲得多。
沧溟沉默地看着她拿出针线,手指翻飞,灵巧地将那裂口缝合,针脚细密匀称。那细小的银针在她指尖,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他忽然意识到,在这凡尘,他所拥有的力量或许能打败山河,却未必能妥善地缝补一件衣衫。这是一种全新的、关于“力量”的认知。
傍晚,沈清弦简单做了两菜一汤。一盘清炒时蔬,一碟腊肉,一碗豆腐汤。她将米饭盛好,放在他面前。
沧溟看着桌上的饭菜。经过几日,他已能勉强适应这些食物的简单味道。他学着沈清弦的样子,端起碗,执起筷。
饭至中途,沈清弦犹豫了一下,夹了一小块瘦多肥少的腊肉,轻轻放入他碗中。
“公子尝尝这个,是去岁冬月自家腌的,味道尚可。”
这是一个极其自然的、带着关怀的动作。沧溟的动作却顿住了。他看着碗中那块色泽深红、泛着油光的肉,龙族天性不喜这等腌制之物,更不习惯……与他人如此亲近的分享食物。
沈清弦见他不动,以为他不喜,忙道:“若是不合口味……”
“无妨。”沧溟打断她,声音低沉。他依着这几日观察到的“凡人礼仪”,用筷子夹起那块肉,送入口中。咸香韧硬的口感在唇齿间弥漫开,与他习惯的清淡灵物截然不同。他咀嚼得很慢,仿佛在品味某种难以言喻的滋味。
他抬眼,看到沈清弦正看着他,眼中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期待。
“尚可。”他终是给出了评价。
沈清弦眉眼弯了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得到了某种肯定,低头继续吃饭,嘴角噙着一抹浅浅的笑意。
那一刻,沧溟忽然觉得,口中那陌生而粗糙的食物,似乎也并非全然难以忍受。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不,这小院里没有华灯,只有书房和卧房各一盏昏黄的油灯。
沈清弦在灯下做着绣活,补贴家用。针线篮里,除了寻常丝线,还有几缕颜色更鲜亮、质地更柔软的彩线,是她准备用来绣制更精致的香囊,以期卖个好价钱。
沧溟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手中虽拿着一卷书,目光却并未落在字上。他看着跳跃的灯焰在她专注的侧脸上投下柔和的阴影,看着她纤细的手指牵引着彩线,在素绢上逐渐勾勒出缠枝莲的纹样。空气中弥漫着灯油燃烧的气味、淡淡的墨香,以及她身上传来的、一种极淡的,像是雨后青草混着皂角的清新气息。
安静,却并不令人感到孤寂。
这与龙宫万年不变的璀璨明珠、冰冷玉阶、以及臣属们恭敬却疏离的氛围,完全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是微小的、脆弱的、充满烟火气的,却带着一种奇异的……温度。
他心口那枚被隐藏的逆鳞,安安静静,并无异样。
情劫,该如何渡?是沉浸其中,再行斩断?龟丞相语焉不详,只道“顺其自然,劫满自明”。
顺其自然……
他看着灯下女子温婉的眉眼,第一次对这场既定的“修行”,产生了一丝极其微茫的疑虑。
而这疑虑,如同投入静深古潭的一粒微尘,尚不及泛起涟漪,便沉入了无尽的幽邃之中。
那场雨,来得毫无征兆。
先是天色暗沉,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下来,闷得人喘不过气。随即,豆大的雨点便砸落下来,噼里啪啦,带着一股秋日的肃杀与寒意。这雨一连下了三日,没有停歇的意思,镇子外的河水眼见着浑浊上涨,漫过了低处的田埂。
起初,镇上人只当是寻常秋汛。直到雨势渐小,河水退回河道,一种无声的恐慌才开始如同湿冷的雾气般,在青石巷陌间弥漫开来。
先是东头的王猎户家的小儿子发起高烧,上吐下泻,不过两日,便虚弱得下不了床。紧接着,临近河边的几户人家也陆续出现了类似的症状。镇上的李郎中忙得脚不沾地,药铺里的几味常用草药很快见了底,却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皱着眉道是“水湿侵体,邪气内蕴”,开的方子吃下去,却如同石沉大海,不见起色。
恐慌像藤蔓般缠绕住这个平日宁静的小镇。人们紧闭门户,空气中弥漫着煎煮草药的苦涩气味,以及一种更深沉的、名为绝望的气息。
书铺的生意自然也冷清下来。沈清弦坐在前铺,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眉头微蹙。她想起前日去井边打水时,听邻人低声议论,说上游怕是冲下来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这病……怕是要过人。
“邪气?”她无意识地低语。
坐在后院窗边看书的沧溟,翻动书页的手指微微一顿。他那远超常人的灵觉,早已感知到这片天地间萦绕的那股异常的、带着污秽与死寂的气息。这并非寻常水患后的疫病,倒更像是……某种水底积年的阴秽之物,被洪水带出,侵染了生灵。
对他而言,这不过是弹指间便可驱散的微末尘垢。龙神之息,至阳至清,涤荡这等污秽易如反掌。
他甚至能“听”到远方龙宫属臣通过水脉传来的、细微的请示波动——是否需要驱散这片区域的疫气?
不能。
龟丞相的告诫言犹在耳:“陛下,凡人生死有命,福祸自担。若以神力干涉,恐扰乱命数,于情劫有碍,反遭天谴。”
情劫……他下界是为渡劫,而非行善。这些凡人的生死,与他何干?
他重新将目光投回书卷,那密密麻麻的文字却仿佛失去了意义。脑海中浮现的,是沈清弦昨日出门,将自家存着的一点艾草分送给邻近染病老人的身影。她回来时,裙角沾了泥水,脸色有些发白,却还是强撑着打理铺子,为他准备饭食。
她也是这芸芸凡人中的一员。脆弱,易折。
就在这时,前铺传来一阵压抑的咳嗽声,随即是沈清弦有些慌乱的低呼:“周大娘?您怎么了?”
沧溟起身,走到通往前铺的门帘边,悄然望去。
只见一个头发花白、面色蜡黄的老妇人扶着门框,几乎站立不稳,正是住在斜对面的周大娘。她儿子前日也病倒了,家中想必已是乱成一团。
“清弦……丫头,”周大娘气息微弱,眼神浑浊,“我……我怕是也……家里没了米,栓子(她儿子)还躺着,能不能……求你……”
沈清弦连忙上前扶住她,丝毫不顾忌可能被传染的风险:“大娘您别急,先坐下。我屋里还有些米,这就给您拿去。”她将老妇人扶到一张椅子上坐下,转身便要去后院取米。
经过门帘时,她看到了站在那里的沧溟。四目相对,沈清弦在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里,看到了一片冰冷的平静,仿佛门外正在发生的苦痛,与他隔着一重无法逾越的屏障。
她脚步微顿,眼底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无奈,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却什么也没说,只是匆匆去了后院。
沧溟站在原地,能清晰地闻到从周大娘身上传来的、那股带着腐朽气息的病气。也能听到沈清弦在后院米缸里舀米时,那略显急促的呼吸声。
凡人的挣扎,如此鲜明而刺目地呈现在他面前。
沈清弦将一小袋米塞给周大娘,又仔细叮嘱了几句,才将颤巍巍的老人送出门。她回到铺子里,沉默地用清水反复净手,背影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单薄而疲惫。
“你……不怕?”沧溟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依旧没什么起伏。
沈清弦转过身,脸上带着倦色,却勉强笑了笑:“怕。怎么会不怕。”她看向窗外空寂的街道,声音轻了下来,“可是周大娘平日待我极好,我爹去得早,她没少接济我。如今她家有难,我若因惧怕而袖手旁观,于心何安?”
于心何安。
四个字,轻轻飘飘,却像一把未曾开锋的钝刀,撞在沧溟那颗万年不动的心上。
龙族行事,循的是天地法则,强弱定理,何曾在意过“心安”?这凡间女子的准则,简单,直白,却又如此……沉重。
是夜,雨终于停了,一轮冷月孤悬天际。
沈清弦发起了低烧。她把自己关在卧房里,隔着门对沧溟说,只是今日劳累,有些着凉,睡一觉便好,让他切勿靠近。
沧溟站在书房中,能清晰地感知到一墙之隔的地方,那原本清润平和的气息,此刻正被一丝微弱却顽固的秽气缠绕、削弱。凡人的躯体,果然不堪一击。
他走到窗边,仰望那轮冷月。东海龙宫的方向,水脉的波动再次传来,带着询问之意。
他只需一个意念,甚至无需动用本尊神力,仅凭这化身与生俱来的、一丝微不可查的龙息,便能驱散这小镇上空的疫气,自然也能净化她体内的病秽。
这于他,易如反掌。
然而,抬手之间,指尖凝聚的微光却迟迟未动。
干预命数,情劫反噬……龟丞相的话语如同冰冷的锁链。
他闭上眼,沈清弦白日里那句“于心何安”,和她强撑笑意的疲惫面容,交替浮现。
许久,他指尖的微光缓缓散去。
他终究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负手立于窗前,任由那清冷的月辉洒满周身,如同披上了一层冰霜的铠甲。那无形的屏障,似乎并未消失,反而因他的“清醒”与“克制”,变得更加坚不可摧。
情劫之路,莫非就是要他这般,眼睁睁看着她在凡尘的苦海中挣扎,直至……勘破这虚妄的牵绊?
他第一次觉得,这月华,有些过于寒凉了。
而卧房内,沈清弦蜷缩在床榻上,额角沁出冷汗,身体一阵阵发冷。昏沉之间,她仿佛又看到了沧溟那双平静无波的眼睛。
他,到底是谁?为何能在这满城惶惑之中,如此……超然物外?
一个模糊而惊人的念头,如同黑暗中划过的闪电,骤然照亮了她混乱的思绪,却又迅速沉入更深的迷惘与无力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