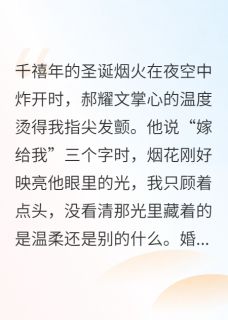
千禧年的圣诞烟火在夜空中炸开时,郝耀文掌心的温度烫得我指尖发颤。
他说“嫁给我”三个字时,烟花刚好映亮他眼里的光,我只顾着点头,
没看清那光里藏着的是温柔还是别的什么。婚礼办得风光,红木圆桌从饭店大堂排到走廊,
叔叔端着酒杯过来时,郝耀文正给我剥虾,动作自然得像做过千百遍。“耀文这名字,
”叔叔呷了口酒,目光在郝耀文脸上打了个转,“倒像香港**片里,那种藏得很深的角色。
”郝耀文笑了笑,把剥好的虾放进我碗里:“叔说笑了,我就是个跑船的,哪敢跟电影里比。
”那时我信了。信他每天凌晨出门跑长途,信他手机里偶尔响起的陌生号码是货主,
信他衬衫领口偶尔沾着的烟味是跟伙计们凑局时染上的。直到两年后,
我在他枕头下摸到一个烫金笔记本,第一页就写着“耀文”——但后面跟着的,
是另一个姓氏,和一长串我看不懂的代号。1千禧年的圣诞夜,
尖沙咀的风裹着咸腥味往人骨头里钻。我缩着脖子往广场挤,郝耀文跟在后面,
大衣下摆扫过我的脚踝,像只沉默的影子。“挤这么前做什么?”他从后面圈住我的腰,
掌心熨帖地贴在我冻得发僵的小腹上,“等下烟花炸起来,人潮能把你卷走。”我挣了挣,
没挣开。他的力气总这样,看着清瘦,胳膊上的肌肉却硬得像块铁。周围的人开始欢呼,
倒计时的声浪一波叠一波,我转头看他,霓虹灯在他脸上明明灭灭,鼻梁高得像把刀。
“看我做什么?”他低头,呼吸喷在我额头上,带着点薄荷烟的味道,“等下烟花亮了,
再看就晚了。”话音刚落,第一簇烟花就在头顶炸开。金红色的光铺下来,
把他的眼睛照得透亮。人群里的尖叫快掀翻屋顶,他突然低下头,嘴唇擦过我的耳廓,
声音压得很低,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彩霞,嫁给我。”我愣住的瞬间,
第二簇烟花又炸了。这次是绿色的,像把伞撑开在天上。他从大衣内袋摸出个小盒子,
打开时,戒指上的碎钻闪得人眼晕。不是什么名贵款式,银托子磨得发亮,
倒像是戴过些年头。“我知道你嫌我跑船,三天两头不着家。”他的拇指摩挲着我的手背,
指腹有层薄茧,“但我保证,结了婚就不跑了。找个码头的活,朝九晚五,陪你吃晚饭。
”周围的人还在疯,有人举着相机挤过来,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我看着他手里的戒指,
突然想起第一次见他的样子。2在油麻地的排档,他穿着件黑色皮夹克,
正跟人争一箱冻虾的价钱,骂人的话糙得像砂纸,转头看见我,却突然闭了嘴,
耳根红得厉害。“说话啊。”他有点急了,喉结滚了滚,“不乐意?”我摇摇头,
把手指伸过去。戒指套上来时有点松,他皱了皱眉:“回头找师傅改改。”烟花还在放,
红的绿的紫的,把夜空染得像块打翻了的调色盘。他牵着我的手往回走,
穿过涌来涌去的人潮,谁撞了我一下,他立刻把我往怀里带,眼神冷得像冰,
对方讪讪地说了句对不起,他也没应声。“你刚才那眼神,能把人吓死。
”我拽了拽他的袖子。“怕什么?”他低头看我,嘴角勾了勾,“谁敢动我的人。
”半个月后的婚礼,摆在湾仔最体面的酒楼。我穿着租来的婚纱,站在门口迎客,
高跟鞋跟陷进地毯里,拔都拔不出来。郝耀文穿着一身白西装,头发梳得油亮,
正跟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握手。那男人背对着我,说话时肩膀微微耸动,像只斗胜了的公鸡。
“那是谁啊?”我凑过去问他。“我叔的朋友,在**做事。”他替我理了理头纱,
指尖碰过我耳垂,有点凉,“等下他过来敬酒,你少说话,笑就行。”开席时,
那男人果然端着酒杯过来了。他长得富态,肚子挺得像个皮球,眼睛却亮得很,
扫过郝耀文时,突然停住了。“耀文是吧?”他咂了口酒,“好名字。
”郝耀文笑了笑:“刘先生过奖。”“不是过奖。”刘先生的手指在酒杯沿上敲了敲,
“前阵子看部港产片,里面有个角色也叫耀文,是个狠角色。”他顿了顿,眼睛眯成条缝,
“跟你一样,看着斯文,眼神里有东西。”郝耀文的手顿了顿,手里的酒瓶晃了晃,
酒液溅在桌布上,晕开个深色的圈。“刘先生真会开玩笑。”他把酒瓶放下,
拿起茶壶给刘先生添水,“我就是个跑船的,哪懂什么狠不狠。”“哦?跑船的?
”刘先生挑了挑眉,“跑哪条线?”“东南亚。”郝耀文的声音很平,听不出情绪,
“新加坡,马来西亚,偶尔去趟泰国。”“那辛苦。”刘先生没再追问,干了杯里的酒,
转身走了。他的皮鞋踩在地毯上,没什么声音,倒像猫走路。3郝耀文拿起桌上的烟盒,
抽出一根叼在嘴里,没点火。我看见他的指节泛白,捏着烟盒的手紧了紧。“怎么了?
”我碰了碰他的胳膊。“没事。”他把烟塞回烟盒,扯出个笑,“去给宾客倒酒。
”婚礼闹到后半夜才散。我坐在梳妆台前卸头饰,镜子里映出郝耀文的影子,
他正站在窗边打电话,背对着我,声音压得很低。我听见“货”“码头”“今晚走”几个词,
心里咯噔一下。“不是说结了婚就不跑船了吗?”我转过身问他。他挂了电话,转过身来,
脸上没什么表情:“这批货急,走一趟就回来。”“什么时候走?”“现在。”他走过来,
弯腰抱了抱我,身上的古龙水味混着点烟草味,“等我回来,带你去买戒指,买个大的。
”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我扒着窗户看他上车,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滑进巷口,
像条鱼游进了海里。4之后的日子,他果然常不在家。有时走三五天,有时走半个月,
回来时身上总带着股海腥味,衬衫领口偶尔沾着点口红印,他说是码头的**蹭的,
我没敢问。他给的家用很足,一沓沓的钞票放在抽屉里,用橡皮筋捆着,
上面还带着点油墨味。我想去银行存起来,他不让,说放家里方便。“怕什么?
”他捏着我的下巴笑,“谁敢来偷?”有次他回来,胳膊上缠着绷带,
说是卸货时被箱子砸的。我给他换药,看见伤口边缘整整齐齐,倒像是刀划的。“怎么弄的?
”我忍不住问。“说了被箱子砸的。”他皱了皱眉,把胳膊抽回去,“女人家别问那么多。
”我没再问。只是夜里睡不着,总想起刘先生那句话,想起那部港产片里的耀文,
想起郝耀文藏在床底的黑色皮箱,锁得死死的,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5这天早上,
我去市场买鱼,蹲在摊前挑拣时,突然一阵恶心,扶着墙干呕起来。
卖鱼的阿婆看我脸色发白,递了张纸巾过来:“姑娘,是不是有了?”我愣住了。
扶着墙站起来,阳光刺得人眼睛疼。远处的海面上,几艘货轮正缓缓驶进港口,
烟囱里冒出的黑烟,在蓝天上拖出长长的尾巴。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郝耀文。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手指悬在接听键上,突然不敢按下去。电话接起来时,
郝耀文的声音带着点海风的潮气:“在哪?”“市场。”我捏着手机,指尖发紧,
“刚买了条鱼。”“早点回家。”他顿了顿,“我今天不出去。”我回到家时,
他正系着围裙在厨房转悠。阳光从百叶窗钻进来,在他背上割出几道亮纹。他转过头,
手里还拿着把菜刀,刀刃上沾着点葱花。“回来了。”他把刀放下,接过我手里的鱼,
“买这么大条,吃得完?”“想喝鱼汤。”我换了鞋,看着他处理鱼,手指在鱼鳞上刮过,
动作利落得不像个跑船的。那天他没出门。晚上坐在沙发上看录像带,放的是部老**片,
里面的黑帮小弟被人追着砍,他看得眼皮都不抬。**在他肩膀上,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须后水味,突然说:“刘先生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拿遥控器的手顿了顿,没回头:“什么话?”“说你像电影里的耀文。
”电视里的枪声突然炸响,他把音量调大了点:“老人家随口说的,你也当真。
”6从那天起,他真的不怎么出门了。每天早上去楼下买豆浆油条,回来时带份报纸,
坐在餐桌旁翻得沙沙响。下午要么修修家里的旧收音机,要么就趴在阳台栏杆上抽烟,
看着远处的码头出神。我问他怎么不跑船了,他总说“停海”,
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天傍晚,门被敲得砰砰响。我打开门,是我弟阿杰,
背着个双肩包,校服领口敞着,一股汗味混着烟味涌进来。“姐!”他挤进门,
看见沙发上的郝耀文,立刻站直了点,“姐夫也在啊。”郝耀文抬了抬眼皮:“放学了?
”“嗯,今天没晚自习。”阿杰把书包往地上一扔,自来熟地拉开冰箱找汽水,“姐夫,
听说你最近不跑船了?”“嗯。”“那多无聊。”阿杰灌了口汽水,打了个嗝,
“我跟你去跑船呗?反正我也不想读书了,不如早点挣钱。”我刚端着水果出来,
听见这话皱起眉:“阿杰,胡说什么?好好上学去。”“姐你别管。”阿杰转向郝耀文,
眼睛发亮,“姐夫,带我一个呗?我能吃苦,搬箱子扛货都行。”郝耀文没说话,
从烟盒里抽出根烟点燃,烟雾在他脸前缭绕。“你还小。”“不小了!再过半年就十八了!
”阿杰凑过去,“我知道姐夫你不是普通跑船的,上次我跟同学去码头玩,
看见有人跟你鞠躬呢,还喊你……”“阿杰!”我打断他,心里发慌,“去洗手,准备吃饭。
”7晚饭时,阿杰一个劲给郝耀文倒酒。米酒的甜香飘满桌子,郝耀文喝了两杯,
脸颊有点红。阿杰又提起要跟他干活的事,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了不行!
你要是敢退学,我就告诉爸妈!”“姐你这人怎么这样……”阿杰嘟囔着,转向郝耀文,
“姐夫,你说句话啊。”郝耀文夹了块排骨放进我碗里,看着阿杰:“你真想干?”“想!
”“不怕累?”“不怕!”郝耀文笑了笑,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下:“行啊,自家兄弟,
有什么怕的。”我气得说不出话,饭也没吃,转身进了卧室。
听见外面阿杰兴奋地跟郝耀文打听这打听那,郝耀文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
偶尔传来酒杯碰撞的脆响。8夜里把阿杰安排在客卧,他喝得脸红脖子粗,
倒头就打起了呼噜。我回房时,郝耀文正坐在床边解领带,衬衫领口敞开着,
露出锁骨上淡淡的疤痕——上次他说是被箱子砸的,现在看来,倒像是道旧伤。
他凑过来想抱我,我往旁边躲了躲。他的手僵在半空,眼神沉了沉:“还在气?”我没说话,
从抽屉里拿出那张孕检单,递到他面前。灯光落在纸上,“怀孕六周”几个字格外清晰。
他的眼睛慢慢睁大,伸手接过单子,指尖有点抖。看了足足有半分钟,他突然抬头看我,
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接着,他猛地把我拽进怀里,勒得我骨头都疼。
“彩霞……”他的声音有点哑,埋在我颈窝里,“真的?”我点点头,感觉脖子上湿乎乎的,
不知道是他的汗还是别的什么。他抱了我很久,久到我快喘不过气,才松开手,
双手扶着我的肩膀,反复打量我,嘴角咧得老大,露出点孩子气的傻气。“我要当爹了?
”他问。“嗯。”他突然转身往客厅跑,我听见他打开冰箱,拿出剩下的米酒,
对着瓶口猛灌了两口。窗外的月光照进来,他的影子落在墙上,又高又瘦,
像棵突然活过来的树。“明天我就去找人,”他转过身,眼睛亮得吓人,“把那批货处理掉。
”“什么货?”我追问。他顿了顿,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发,动作很轻:“没什么,
以后不跑船了,专心陪你。”我看着他眼里的光,心里却像压着块石头。
客卧里传来阿杰的梦话,含含糊糊的,像是在喊“姐夫”。郝耀文的手还放在我头上,
掌心的温度很烫,烫得我有点发慌。9郝耀文说换了工作的那天,
正蹲在阳台给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浇水。他背对着我,白衬衫后领沾着点灰,
像是刚从什么脏地方回来。“做什么的?”我晾着衣服,声音透过洗衣机的嗡鸣传过去。
“码头仓库,管收发。”他转过身,手里还捏着洒水壶,壶嘴滴着水,
在地板上砸出小小的印子,“不用出海,晚上能回家吃饭。”我没再问。有些事,他不想说,
问了也是白问。就像他抽屉里那些捆得整齐的钞票,票面总带着股潮湿的霉味。
就像他偶尔深夜接的电话,开口总是用几句拗口的南洋话,声音压得低到听不清。
他确实回来得勤了些。有时提着烧腊铺的叉烧,有时带几瓶冰镇啤酒,
坐在餐桌旁慢悠悠地喝,眼睛盯着电视里的赛马新闻,手指在桌沿上敲出规律的节奏。
我问起阿杰,他总是含糊其辞。“那小子野,在码头学开叉车,说比上学有意思。
”“昨天见他跟几个搬运工打牌,赢了不少。”“不用管他,男孩子就得摔打摔打。
”我心里发沉,却抓不到实证。直到那天去码头送汤,远远看见阿杰穿着件不合身的工装,
正帮着郝耀文搬一个印着外文的木箱。10箱子封得严实,被叉车托起时,
侧面隐约露出红色的斑驳。阿杰看见我,脸唰地白了,扔下手里的撬棍就往仓库后面躲。
郝耀文站在原地没动,叉车的轰鸣声盖过了我的质问。他走过来接过保温桶,
手指触到我的手背,凉得像冰。“你让他搬的是什么?”我的声音发颤。“香料。
”他打开保温桶,舀了勺汤,“南洋来的胡椒,金贵得很,怕磕着。”“那红色是怎么回事?
”他抬眼看我,睫毛在眼下投出片阴影:“装货时蹭到的,老鼠血。”我没再说话,
转身往公交站走。风卷着码头的腥气扑过来,吹得人睁不开眼。身后传来阿杰的喊声,
他追了几步,被郝耀文拽了回去,两人的争执声混在海浪拍岸的声响里,碎得不成样子。
11冲突是在半个月后爆发的。那天半夜,门被砸得震天响。我披着衣服打开门,
两个穿制服的男人站在门口,证件上的徽章陌生又刺眼。“是郝耀文的家属?
”带头的男人说着生硬的粤语,眼角有道疤,“我们是境外警务处的。
”郝耀文从卧室走出来,衬衫扣子扣得歪歪扭扭,手里捏着根没点燃的烟。“什么事。
”“你弟弟阿杰,”疤脸男人从皮包里抽出张照片,“是不是跟你一起做事?
”照片上的阿杰穿着件花衬衫,站在艘货轮前比耶,背景里的集装箱印着我看不懂的标识。
我的腿一软,扶住了门框。“他怎么了?”郝耀文的声音很平。“三天前,
槟城码头发生械斗,两帮人抢地盘,火并时伤了不少人。
”疤脸男人的手指在照片边缘敲了敲,“我们在现场找到这个,是你弟弟的。
”他拿出个银色的打火机,外壳上刻着个歪歪扭扭的“杰”字。是我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
“人呢?”我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失踪了。”疤脸男人看着郝耀文,“现场有目击者说,
他跟着你手下的人搬‘水货’,被卷进火并里,没来得及跑。”郝耀文突然笑了笑,
从烟盒里抽了根烟递过去,被疤脸男人挡开了。“警官说笑了,我就是个管仓库的,
哪懂什么水货。”“是吗?”疤脸男人从包里又抽出几张照片,“那这几个箱子怎么说?
你上个月从槟城接的货,里面装的可不是香料。”12照片拍得模糊,
却能看清箱子被撬开的缺口,露出里面裹着黑布的长条状东西。
我突然想起阿杰身上那股洗不掉的火药味,想起郝耀文床底那个锁死的皮箱,
想起那些带着异味的钞票。“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郝耀文往门口站了站,
挡住我的视线,“要搜查?拿warrant(warrant:搜查令)来。
”疤脸男人没动,只是盯着他:“郝耀文,道上都叫你‘文哥’吧?槟城那批货,
是你接的‘硬货’,对不对?”他顿了顿,声音压低,“现在两边都在找你,你躲得过一时,
躲得过一世?”郝耀文的手猛地攥成拳头,指节泛白。我看着他的侧脸,
突然发现他耳后有块新的疤,上次他说是刮胡子不小心划的,现在看来,
倒像是被子弹擦伤的。“人我会找。”郝耀文的声音冷得像淬了冰,“但我警告你,
别吓着我老婆。”疤脸男人笑了笑,收起照片:“我们还会再来。”他转身时,看了我一眼,
“郝太太,有些事,知道得早,对谁都好。”门被带上时,我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
郝耀文背对着我,肩膀微微耸动,像头被激怒的兽。“阿杰……”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他突然转身抱住我,力气大得像要把我揉进骨血里。“别怕。”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发颤,
“我会把他找回来,一定。”窗外的海面上,不知何时泊了艘黑色的船,没有开灯,
像块浮在水上的礁石。我摸着自己隆起的小腹,能感觉到里面微弱的胎动。
郝耀文的心跳震得我胸口发疼,可我知道,有些东西,从阿杰拿起那个撬棍开始,
就再也回不去了。13搬家那天,卡车在山路上盘了三小时。我扒着车窗看出去,
海平线早没了踪影,只有层层叠叠的山,绿得发黑,像要压到头顶来。郝耀文扶我下车时,
我脚一软,差点摔倒。他的手扣在我腰上,很紧,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道。“新家清静,
适合养胎。”他说话时看着远处的山坳,眼神飘得很。房子是栋独栋小楼,墙皮新刷过,
白得晃眼。窗户装着栏杆,铁条粗得像码头的缆桩。我摸着栏杆问他:“这是防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