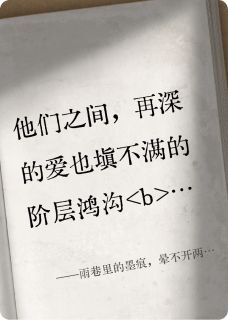
他们之间,再深的爱也填不满的阶层鸿沟一苏清沅在画廊打第三份工时,
总觉得那幅临摹的《雨巷》挂得太偏。九月的雷阵雨裹着热风砸下来,
她踩着塑料拖鞋去关窗,后腰撞翻了画架。卷轴“啪嗒”落地,
末端的墨痕蹭到了刚进门的人——黑色风衣下摆沾了道灰蓝,像水墨画里不慎洇开的败笔。
“对不住!”她慌忙去捡,手指却先一步被人捏住。
男人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渗过来,带着沉木熏香,和画廊里松节油的味道格格不入。
“沈先生?”老板从里间跑出来,额角冒汗,“您怎么亲自来了?”苏清沅这才抬头。
男人垂着眼,长睫在眼下投出片阴影,鼻梁高挺,唇线抿得平直。他没看她,
指尖捻着那道墨痕,声音淡得像雨丝:“这幅画,我要了。
”老板笑得更殷勤:“沈先生好眼光,这是我们学生……”“多少钱?”他打断,
视线终于落到她身上。苏清沅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裙,帆布鞋沾着颜料,
手里还攥着块皱巴巴的抹布。她被那目光看得发慌,小声说:“画有瑕疵,我重画一幅给您。
”男人挑了下眉,像是觉得有趣:“不必。”他刷卡时,
苏清沅瞥见他钱夹里露出半张老照片,泛黄的底色上,穿军装的老人眉眼和他有七分像。
后来她才从老板嘴里听到,沈砚之是沈家长孙,住的地方有专门的恒温画库,
墙上挂着的真迹,够她打一辈子工。那幅《雨巷》被他的助理取走时,
苏清沅偷偷在画轴里塞了张便签,写着“若不喜,可寄回”。地址是她租的老小区,七楼,
没电梯。当然,便签石沉大海。二再见到沈砚之,是在沈氏集团的慈善晚宴上。
苏清沅作为校报记者跟着老师来打杂,穿着借来的黑色小礼裙,裙摆扫过光可鉴人的地板,
总觉得像只误入天鹅湖的灰雀。她缩在角落整理要交给老师的稿件,
忽然听到身后有人笑:“沈少,听说你最近收了幅学生临摹的画?”“随手买的。
”沈砚之的声音,比雨天时更冷些。苏清沅笔尖一顿,墨水在纸上晕开个黑点。
她转身想走,却撞进他怀里。香槟洒了他一身,也溅湿了她廉价的礼裙。“抱歉。
”她低头去擦,手指刚碰到他的西装,就被他攥住。“苏同学?”他认出她了,
语气里带着点玩味,“又见面了。”周围的目光像针一样扎过来。
有人认出她是美院的穷学生,窃笑声里裹着毫不掩饰的轻蔑。沈砚之却没松手,
反而从侍者托盘里拿了杯果汁递给她:“赔我件西装?
”苏清沅脸发烫:“我……我没那么多钱。”“那就欠着。”他松开手,
指尖有意无意擦过她的手腕,“下次见面再还。”那晚之后,
沈砚之开始出现在她的生活里。他会开着黑色宾利停在美院门口,
摇下车窗看她抱着画板跑出来;会带她去吃巷尾的馄饨,看着她把醋瓶倒空,
自己却一口不吃;会在她熬夜赶画时,默默坐在画室角落处理文件,
落地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苏清沅知道他们之间隔着云泥。他的朋友叫他“砚之”,
谈论的是她听不懂的股市和政策;她的室友叫她“清沅”,操心的是下个月的房租和奖学金。
可沈砚之看她的眼神太认真,他说“清沅,别想那么多”,语气里的温柔,
让她忍不住想踮脚够一够那片遥不可及的云。三沈砚之第一次带苏清沅回沈家老宅,是冬至。
车开进那条种满银杏的巷子时,苏清沅攥紧了他的手。老宅是民国时的建筑,朱漆大门,
铜环兽首,门内传来隐约的钢琴声。沈砚之的母亲坐在客厅,穿香云纱旗袍,看见她时,
嘴角的笑意淡了淡:“是小苏吧?坐。”饭桌上,长辈们聊起沈砚之的婚事。
沈老爷子呷了口酒:“陈家那丫头不错,你们俩小时候还订过娃娃亲。
”苏清沅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沈砚之忽然开口:“爷爷,我有女朋友了。”满桌寂静。
沈母的脸色沉下来:“砚之,别胡闹。”“我没胡闹。”他握住苏清沅的手,放在桌上,
“她叫苏清沅,我想娶她。”那天的饭吃得像场酷刑。
苏清沅听见沈砚之的表妹跟人小声说:“她身上那裙子,是去年的旧款吧?
”看见自己带的伴手礼——两罐亲手做的腌菜和她特意挑选的自以为上的了台面的礼物,
被佣人随意放在了玄关角落。回去的路上,车开得很慢。苏清沅望着窗外掠过的霓虹,
轻声说:“沈砚之,我们算了吧。”他猛地踩下刹车,转过头看她,
眼底有红血丝:“苏清沅,你再说一遍?”“我们不合适。”她别过脸,眼泪掉下来,
“你家的门槛太高,我跨不过去。”“那我们就这样你甘心吗?
”苏清沅没有回答车内氛围陷入沉寂。那之后,沈砚之开始和家里对抗。
他搬去了自己租的公寓,不再参加那些所谓的“联谊”;他带苏清沅见他最亲近的发小,
说“这是我认定的人”;他甚至学会了做番茄炒蛋,笨拙地在厨房里忙乎,
油星溅到昂贵的衬衫上,也只是笑笑。苏清沅以为,爱真的能抵万难。她开始学着喝红酒,
学跳华尔兹,努力想融入他的世界。可当沈砚之的奶奶生病,她提着保温桶去医院,
却被护士拦在外面:“抱歉,沈家人交代了,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她站在医院的走廊里,
看着沈砚之被一群穿着考究的亲戚围住,他朝她投来抱歉的眼神,却抽不开身。那一刻,
苏清沅忽然明白,有些鸿沟,不是爱就能填平的。
四沈砚之的母亲找主动苏清沅谈话是在沈砚之的奶奶葬礼结束后的一个周末,在一家茶馆。
女人坐在对面,慢条斯理地沏茶,香气袅袅,语气却像冰:“小苏,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
但你和砚之,不是一路人。”她推过来一张支票:“离开他,这些钱够你读完研究生,
还能买套不错的房子,当然最好是出国,我们家在国外还是有些人脉的。
你随时可以直接联系我。”苏清沅默声,她大脑短暂宕机,
女人又补充:“砚之现在未必可以给你这么多。”声音染上些许不满的怒意。
苏清沅没看那张支票:“阿姨,我喜欢沈砚之,不是因为这些。”“可你能给他什么?
”女人抬眼看她,“他从小吃的用的,你奋斗一辈子都未必能企及。你忍心他为了你,
跟家里决裂,被人戳脊梁骨?”那天晚上,苏清沅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
是沈砚之和陈家**的合照。照片里,他站在宴会厅中央,她挽着他的手臂,郎才女貌,
像一对璧人。苏清沅知道那是角度问题,沈砚之跟她说过,那天是为了应付家里,
才去见了陈**。可心里那根刺,还是扎得生疼。她去沈砚之的公寓收拾东西时,
特意联系了沈母,他现在应该还在老宅。
她看着满屋子属于自己的痕迹——阳台上晾着的帆布鞋,冰箱里剩下的半瓶醋,
画架上那幅没画完的《他》,忽然觉得像场梦。她留下了一枚戒指,
是沈砚之送她的第一份礼物,银质的,很简单,却被她戴了很久。还有一张便签,
上面写着:“沈砚之,谢谢你曾照亮过我。但我们,终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沈砚之晚上回到公寓时,公寓里已经没有苏清沅的东西了。他疯了一样给她打电话,
关机;去美院找她,老师说她一个月前就已经申请了交换生,
可能明天就走;去她租的老小区,房东说她昨天就搬走了。他站在七楼的楼道里,
手里攥着那枚戒指,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原来有些东西,不是他想要,就能留住的。
五苏清沅在巴黎的第三年,画里的雨终于少了些。她的个展开在玛莱区的老画廊,
展出的《巷尾》系列里,有幅画总被人问起:画面角落有半辆黑色轿车的轮廓,隐在雨幕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