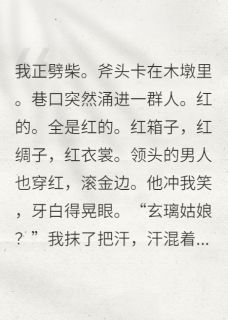
我正劈柴。斧头卡在木墩里。巷口突然涌进一群人。红的。全是红的。红箱子,红绸子,
红衣裳。领头的男人也穿红,滚金边。他冲我笑,牙白得晃眼。“玄璃姑娘?”我抹了把汗,
汗混着灰,脸上肯定一道黑:“谁?”“宸王,夜宸。”他声音不高,巷子里却死静,
连狗都不叫了。王爷?我低头看看自己磨破的袖口,露脚趾的鞋,
再看看那排到巷子外头的红箱子。“找错人了。”我使劲拔斧头。纹丝不动。他两步过来,
轻松一提,斧头在他手里轻得像根草。“没找错。”他把斧头放回我脚边,
“城南槐树胡同最西头,破院门,歪脖子枣树,户主姓玄,玄璃。”**着柴堆,
眯眼看他:“王爷,我欠你钱?”“未曾。”“我救过你命?”“今日初见。
”“那你带着聘礼,”我指了指那堆红,“堵我家门口?”他点头,笑得更好看:“对,
来入赘。”我捡起斧头,掂了掂:“王爷,我这儿,只有破屋两间,耗子一窝,西北风管够。
你图什么?”邻居王婶扒着墙头,眼珠子快掉下来。“图你。”他答得干脆,“图你这个人。
”我嗤笑出声:“我?破落户一个,爹娘死得早,吃百家饭长大的野丫头,大字不识几个,
力气倒有一把。王爷,你眼神不好?”他身后一个管家模样的老头,脸皱得像苦瓜,
小声嘀咕:“王爷,这…太不成体统…”夜宸没理他,只看着我:“眼神好得很。玄璃姑娘,
给句痛快话,收不收?”“不收。”我拎起斧头,转身往院里走,“门小,王爷金贵,
挤不进来。”吱呀——那扇风一吹就倒的破院门,被我甩上。落了栓。门外静了一瞬。
王婶的尖嗓子穿透门板:“哎哟喂!玄丫头!你疯啦?那是王爷!王爷啊!”“王爷怎么了?
”我隔着门喊回去,“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能强塞给我当赘婿!”门外响起低低的笑声。
是夜宸。“脾气对路。”他说,“东西放这儿,人,我改日再来。”脚步声远去。
王婶还在墙头跺脚:“玄璃!你个榆木疙瘩!泼天的富贵啊!你不要给我啊!
”我抄起一根细柴棍扔过去:“王婶,接着!够你烧壶水!”墙头人影一闪,没了。
院里死静。歪脖子枣树掉下几片叶子。我看着那扇破门,手心有点汗。夜宸。宸王。
当今天子最小的弟弟。据说俊美无俦,权势滔天。更据说,性情乖张,行事…不怎么要脸。
他跑来我这破落户门口,说要入赘?图我穷?图我破?图我会劈柴?骗鬼呢。夜里,
我翻来覆去。屋顶有片瓦松了,月光漏进来,正好照在墙角爹娘牌位上。“爹,娘,
”我对着那点光小声说,“咱家祖坟…是不是冒青烟了?还是…冒黑烟了?”没人回答。
只有耗子在梁上跑酷。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梆梆梆!有人砸门。不是敲,是砸。
力气大得门框都在抖灰。“谁啊!”我吼了一嗓子,胡乱套上外衣,趿拉着破鞋去开门。
门栓刚拉开。一股大力猛地推来。我踉跄着后退几步,差点坐地上。
门口站着个穿锦缎的婆子,脸盘子大,涂得煞白,眉毛画得细长,吊梢眼,看人带着钩子。
她身后跟着俩粗壮仆妇,还有几个抬着箱子的家丁。箱子也是红的,
比昨天夜宸带来的小一号。“玄姑娘?”婆子捏着嗓子,眼神像刀子,把我从头刮到脚,
嘴角撇得能挂油瓶,“就这儿?”“有事?”我站稳,拍拍手上的灰。“奉我家夫人命,
来瞧瞧。”婆子扭着腰,径直往院里走,那俩仆妇立刻跟上,像两尊门神,
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夫人?哪位夫人?”我皱眉。婆子停在院当间,
环视我那两间东倒西歪的屋子,还有晾在绳子上打补丁的衣裳,鼻子里哼出一股冷气。
“自然是宸王府未来的当家主母,苏挽云,苏**!”婆子拔高了调门,尖利刺耳,
“苏**心善,听说王爷被这胡同里的…腌臜东西缠上了,特意遣老奴来瞧瞧,
究竟是何方神圣,敢肖想王爷!”她目光钉子似的扎在我脸上:“啧啧,
果然…名不虚传的‘破落户’。”我抱着胳膊,靠在那棵歪脖子枣树上:“看完了?
看完了滚蛋。我这地儿小,容不下大佛。”“放肆!”一个仆妇厉声呵斥,
“敢对容嬷嬷无礼!”哦,容嬷嬷。我掏掏耳朵。“玄姑娘,”容嬷嬷皮笑肉不笑,
“老奴劝你一句,乌鸦别想着攀高枝。王爷金尊玉贵,不过是一时兴起,拿你逗个乐子。
苏**端庄贤淑,与王爷青梅竹马,那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识相的,拿了这点‘辛苦钱’,
”她朝旁边箱子努努嘴,“闭上嘴,滚出京城,永远别再出现。否则…”她拖长了调子,
阴森森地盯着我:“这京城里,悄无声息少个把人,跟碾死只蚂蚁没两样。”我看看那箱子。
再看看容嬷嬷那张抹了粉的老脸。“说完了?”我问。容嬷嬷一愣。我弯腰,
从地上捡起一块半截砖。掂了掂。挺顺手。“你…你想干什么?”容嬷嬷脸色微变,
往后缩了半步。“我这人,脾气不太好。”我掂着砖头,“尤其烦大清早扰人清梦,
还满嘴喷粪的。”我猛地扬手!“啊——!”容嬷嬷尖叫着抱头蹲下。
砖头擦着她梳得油亮的发髻飞过去。“哐当!”精准无比地砸在她带来的那个红箱子上。
箱子盖被砸开一条缝。露出里面白花花的…银锭子。“滚。”我拍拍手上的土,
“带着你的银子,还有你那张老脸,一起滚。再敢踏进我这院子,下次砸的,就不是箱子了。
”容嬷嬷吓得脸真白了,抖得像筛糠。两个仆妇也白了脸,赶紧把她架起来。“你…你等着!
小贱蹄子!有你好果子吃!”容嬷嬷被拖着往外走,还不忘回头撂狠话。“砰!
”我再次甩上门。落栓。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心脏跳得有点快。苏挽云?青梅竹马?
未来的当家主母?我走到墙角,对着爹娘的牌位。“爹,娘,你们说,这都什么事儿啊?
”牌位静悄悄的。我走到被砸开的箱子旁,踢了一脚。银子滚出来几锭。成色不错。
够我吃几年饱饭。我弯腰,捡起一锭。沉甸甸。冰凉的触感。我掂了掂,然后,用力一扔。
银子在空中划了个弧线。“噗通!”精准地落进院角那口腌咸菜的大缸里。
水花都没溅起多少。“晦气钱。”我嘟囔一句,转身回屋补觉。刚躺下没多久。
门外又有动静。这次不是砸门。是轻轻的叩击声。笃,笃,笃。很有耐心。
我烦躁地掀开破被子,冲出去:“有完没完!让不让人睡…!”拉开门。
后面的话卡在喉咙里。门外站着夜宸。没穿红。一身墨蓝常服,玉冠束发,少了昨日的张扬,
多了几分清贵。他手里没拿东西。就一个人。身后也没跟着那群抬箱子的。巷子里空荡荡。
只有晨风卷着几片落叶打旋儿。他看到我,眉头几不可查地皱了一下,视线落在我脸上。
我这才想起,脸没洗,头发像鸡窝,还带着起床气。“看什么看!”我没好气,
“没见过美人起床?”他居然笑了。嘴角弯起一点弧度,像初春冰河裂开第一道缝。
“是没见过这么…”他顿了顿,似乎在找词,“生机勃勃的。”我翻个白眼:“王爷,
您到底想干嘛?昨天那堆红还在巷子里堆着呢,招苍蝇。”“苏家的人来过了?”他问,
语气淡,听不出情绪。“来了个老妖婆,带了一箱银子,让我拿钱滚蛋。”我抱着胳膊,
斜睨他,“您那位青梅竹马的手笔?”“她不是。”夜宸语气冷了一瞬,又恢复如常,
“银子呢?”“扔咸菜缸里了。”我指指院角,“想要?自己去捞。
”他真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那口半人高的咸菜缸,盖子歪在一边。他没动。目光转回来,
落在我脸上,很专注。“玄璃。”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声音低沉,敲在耳膜上。
“跟我合作。”他说。我掏掏耳朵:“合作?王爷,您看看我这院子,除了耗子,
还有什么能跟您合作的?”“你有脑子。”他上前一步,离我很近。
他身上有股清冽的松木香,混着淡淡的墨味。很好闻。跟他这个人一样,矛盾。
“你昨天拒了我,今天砸了苏家的箱子。”他垂眼看着我,睫毛很长,
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说明你不傻,也不怕。”“我傻不傻,怕不怕,关你什么事?
”我梗着脖子。“帮我个忙。”他声音压低,只有我们俩能听见,“做我的‘破落户王妃’。
”我差点被自己口水呛到。“王爷,您病得不轻?药不能停?”“苏挽云的父亲,
是户部尚书苏柄添。”他无视我的嘲讽,语速平稳,“也是当年,构陷玄机营督造玄明,
贪墨军资,致其夫妇自尽于狱中的…主谋之一。”我的呼吸,停了。血液好像瞬间冻住。
耳朵里嗡嗡作响。玄明。督造玄明。我爹。我猛地抬头,死死盯住他。他脸上没有任何戏谑,
眼神沉静得像深潭。“你说什么?”我的声音发紧,干涩得厉害。“你爹玄明,玄机营督造,
专司军械改良。”他清晰地吐出每一个字,“五年前,西北战事吃紧,
一批新制强弩在运送途中被劫,图纸遗失。追查之下,所有证据都指向你爹监守自盗,
贪墨巨额军资。你爹娘在狱中…自尽身亡。”他顿了顿。“玄机营被裁撤,相关人员流放。
你那时只有十三岁,因是女眷,又查无实证,被逐出京城,自此下落不明。”风好像停了。
歪脖子枣树的叶子也不动了。世界很安静。只有他低沉的嗓音,和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爹娘的脸,在记忆里已经模糊。只记得爹总是很晚回来,身上带着铁锈和油的味道。
娘会温一碗热汤等他。他们走得很突然。一群凶神恶煞的人冲进家里。翻箱倒柜。
爹娘被带走。再也没回来。邻居偷偷告诉我,爹娘死了。死的不光彩。让我快跑。我跑了。
从京城的**,变成了四处流浪的野丫头。最后蜷缩在这槐树胡同最破的院子里。苟延残喘。
我慢慢松开抱着胳膊的手。指甲掐进了掌心。不疼。“证据呢?”我问,
声音哑得自己都陌生。“苏柄添书房里,有一本暗账。”夜宸看着我,“记录了他这些年,
通过军需采买,贪墨的巨额银两。其中一笔,时间、数额,
与你爹当年‘贪墨’的军资完全吻合。”“那账本,”我吸了口气,“能扳倒他?”“能。
”他答得斩钉截铁,“但苏柄添老奸巨猾,书房守卫森严,暗账藏匿之处更是隐秘。
我需要一个‘意外’,一个能让他暂时离开书房,并且不会起疑的‘意外’。”他顿了顿,
目光落在我脸上。“比如,他最疼爱的女儿苏挽云,即将到手的‘宸王妃’之位,
突然被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破落户’抢走。他会愤怒,会急于去安抚女儿,
会想办法除掉那个碍眼的‘破落户’…那段时间,就是机会。”我明白了。全明白了。
为什么是宸王。为什么是我。“所以,你找上我。”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没有怜悯,
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清醒,“因为我是玄明的女儿,因为我够‘破落’,够不起眼,
也够…恨他们。”“是。”他没有否认,“我需要一个理由,
一个足够轰动、足够让苏家父女阵脚大乱的理由,接近苏府。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够胆,
够聪明,也够…有理由配合我。”“事成之后呢?”我问,“扳倒苏柄添,替我爹娘**?
”“不止。”他唇角勾起一丝极冷的弧度,“当年构陷玄督造的,苏柄添只是台前卒。
我要的,是他背后那条更大的鱼。”“谁?”“现在还不能说。”他摇头,“知道太多,
对你没好处。你只需要知道,事成之后,我保你爹娘沉冤得雪,保你一世富贵安稳。
你若想离开,我赠你足够逍遥的金银,天下之大,任你去。”我沉默了很久。
看着墙角爹娘那两块简陋的牌位。看着这破败得四处漏风的院子。看着自己磨出茧子的手。
五年的颠沛流离。五年的隐姓埋名。五年的…恨。“成交。”我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夜宸眼中,终于掠过一丝极淡的、近乎满意的光。“不过,”我补充,“我有条件。”“说。
”“第一,在你拿到账本之前,我是你‘强娶’的王妃。在外人面前,戏要做足。但私下里,
你离我远点。”他挑眉:“可以。”“第二,**昭雪那天,我要亲眼看着苏柄添下狱。
”“理所当然。”“第三,”我盯着他,“那个容嬷嬷,还有今天来的那两个仆妇,
我要她们的手。”夜宸似乎有些意外,深深看了我一眼。“她们只是走狗。”“狗咬了人,
”我扯了扯嘴角,“也得打。不然不长记性。”他沉默片刻。点头。“好。”“最后,
”我指了指院角那口咸菜缸,“把你的银子弄走。还有昨天堆在巷子里的,都弄走。看着烦。
”他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一眼。“那是聘礼。”“腌咸菜缸里的聘礼?”我嗤笑,
“王爷品味真独特。”他嘴角抽了一下,似乎想笑,又忍住了。“我会让人处理。
”他转身要走。“等等。”我叫住他。他停步,回头。“王爷,”我看着他挺拔的背影,
“你为什么要查我爹的案子?为什么要对付苏柄添背后的人?”他站在晨光熹微的巷口,
侧脸轮廓有些模糊。“为了…一个公道。”声音很轻。随风飘过来。“也为了,这京城,
该变变天了。”他说完,大步离开。背影很快消失在巷子拐角。我关上门。背靠着门板,
慢慢滑坐到地上。心脏还在狂跳。手心里全是冷汗。爹。娘。五年了。女儿…好像找到路,
走回来了。接下来的日子,鸡飞狗跳。夜宸的动作快得吓人。当天下午,
一队穿着王府侍卫服的人就开进了槐树胡同。领头的是个冷面青年,叫墨影。他指挥着人,
把巷子里堆积如山的“红”都抬走了。顺便,还带走了我那口腌咸菜的大缸,
说是王爷吩咐“处理干净”。王婶扒着墙头,看得眼珠子发直。
“玄…玄丫头…你真…真攀上王爷啦?”我正蹲在院里磨那把豁了口的柴刀。“王婶,
”我头也不抬,“缸没了,以后咸菜借你家缸腌点?”王婶“哎哟”一声,缩回了脑袋。
第二天,天刚亮。更大的阵仗来了。这次不是箱子。是宫里的阵仗。
几个穿着内侍服饰的公公,捧着明黄的卷轴,在一队金甲侍卫的簇拥下,
浩浩荡荡挤进了我这小破院。领头的公公面白无须,声音尖细。“玄氏女璃,接旨——!
”胡同里跪了一地。我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跪在满是尘土的小院里。
圣旨上的词儿文绉绉的,我听懂了大意。宸王夜宸,执意求娶城南民女玄璃。
天子拗不过幼弟,特此赐婚。封玄璃为宸王正妃。择吉日完婚。公公念完,
笑眯眯地把圣旨递给我:“玄姑娘,哦不,王妃娘娘,大喜啊!快接旨谢恩吧!
”我接过那卷沉甸甸、明晃晃的绸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夜宸这疯子,动作真快。
连圣旨都弄来了。“谢…陛下隆恩。”**巴巴地说。公公又说了几句场面话,
留下几箱宫里赏赐的“添妆”,才带着人呼啦啦走了。留下小院,
和院外围得水泄不通、指指点点的邻居。“我的老天爷啊…真成王妃了?”“圣旨都下了!
还能有假?”“这玄丫头…祖坟冒青烟啦?”“啧啧,宸王什么眼光啊…”议论声嗡嗡的。
我抱着圣旨,站在院子中央。感觉像在做梦。一个荒诞无比,又冷硬如铁石的梦。
消息像长了翅膀,瞬间传遍京城。宸王要娶一个破落户!圣旨赐婚!整个京城都炸了锅。
茶楼酒肆,街头巷尾,所有人都在议论。宸王府的门槛,据说快被踏破了。有来探口风的,
有来劝谏的,更多的是想攀关系的。但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我的小破院,成了风暴中心。
但诡异的安静。没人敢轻易靠近。除了一个人。苏挽云。在圣旨下达后的第三天。她又来了。
这次,没带容嬷嬷,也没带凶神恶煞的仆妇。只带了一个贴身丫鬟。她自己。
穿着一身素雅的月白襦裙,发髻上只簪了一支白玉簪。清水芙蓉。弱柳扶风。
站在我那破院门口,像一幅画掉进了泥地里。她眼圈红红的,像是哭过。看到我出来开门,
她盈盈一福,声音带着哽咽:“玄…玄姐姐…”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苏**,别乱叫。
我爹娘就生了我一个。”她身子晃了晃,像被风吹倒的花。丫鬟赶紧扶住她。
“玄姑娘…”她抬起泪眼,楚楚可怜,“挽云…是真心来贺姐姐大喜的。”“哦,贺礼呢?
”我抱着胳膊,倚在门框上。她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问,噎了一下。“我…我…”“没带啊?
”我点点头,“那慢走不送。”我作势要关门。“等等!”她急忙上前一步,
差点被门槛绊倒,“玄姑娘!我…我知道你恼我。前日容嬷嬷无礼,我已知晓,
已重重责罚了她!今日特来赔罪!”“责罚?”我挑眉,“怎么责罚的?”“打了二十板子,
撵去庄子上做粗活了!”她急急地说,眼泪又掉下来,“都是下人不懂事,
冲撞了姐姐…姐姐要打要罚,挽云绝无怨言,只求姐姐…只求姐姐…”她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跪在我满是灰尘的院子里。“求姐姐开恩!把宸王殿下…还给挽云吧!”她哭得梨花带雨,
肝肠寸断,“我与殿下青梅竹马,十数载情意…姐姐,你行行好!你想要什么?金银?珠宝?
宅院?我都可以给你!只求你别拆散我们!没有殿下…挽云活不下去啊!”她哭得情真意切。
我听得面无表情。这演技。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苏**,”我蹲下身,
平视着她哭肿的眼睛,“你听好了。”她抽泣着,泪眼婆娑地看着我。“第一,
不是我拆散你们。是夜宸自己带着聘礼,堵我家门口,死乞白赖要入赘。圣旨也是他求来的。
你要哭,找他去。”她脸色白了白。“第二,”我凑近她,压低声音,只有我们俩能听见,
“你爹苏柄添,做过什么亏心事,你心里真没数?你在这儿跟我演什么情深意重?
”她猛地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我,像是见了鬼。连哭都忘了。“第三,”我站起身,
拍拍膝盖上的灰,“我这人脾气不好,尤其讨厌别人在我家院子里哭丧。晦气。
”我朝她身后努努嘴。“门在那儿,自己滚。还是说,想让我‘请’你出去?
”苏挽云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她死死咬着唇,指甲掐进了掌心。那眼神,
怨毒得像是淬了冰。“你…你给我等着!”她猛地站起身,推开丫鬟的搀扶,
踉踉跄跄地跑了出去。月白的裙角沾满了院里的尘土。背影狼狈不堪。我关上门。
世界清净了。夜宸这招“破落户王妃”,果然够狠。苏家这父女俩,快被逼疯了。
接下来的日子,宸王府的人开始频繁出入我这小院。量体裁衣的绣娘。教导礼仪的嬷嬷。
送来各种首饰、用度的管事。小院被堆得满满当当。王婶看我的眼神,
已经从震惊变成了敬畏,还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讨好。我没心思管这些。我只关心一件事。
夜宸那边的进展。他偶尔会来。总是在晚上。像一道影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院子里。
有时是翻墙。有时是…走门。我坐在门槛上啃一个冷硬的窝头。
他站在院中那棵歪脖子枣树下。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苏府最近很热闹。
”他声音没什么起伏,“苏柄添称病告假,闭门不出。苏挽云病了,说是伤心过度。
”我咽下干涩的窝头:“狗急跳墙了?”“快了。”他看着树梢稀疏的叶子,“暗哨回报,
苏柄添的书房,最近夜间守卫增加了两倍。他本人,几乎寸步不离。”“他在怕。”我说。
“怕失去权势,怕失去女儿唾手可得的‘宸王妃’之位,更怕…”夜宸转过头,
月光落在他深邃的眼底,“当年的事,被翻出来。”“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我把最后一点窝头塞进嘴里。“等一个时机。”他走近几步,递过来一个油纸包。
热乎乎的。带着肉香。“什么?”“烧鸡。”他言简意赅,“光啃窝头,没力气。
”我接过来,打开。油光锃亮,香气扑鼻。我扯下一只鸡腿,狠狠咬了一口。真香。“谢了。
”我含糊不清地说。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狼吞虎咽。“你…”我啃着鸡腿,抬头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