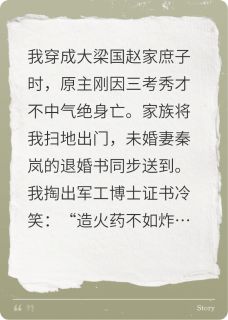
我穿成大梁国赵家庶子时,原主刚因三考秀才不中气绝身亡。家族将我扫地出门,
未婚妻秦岚的退婚书同步送到。我掏出军工博士证书冷笑:“造火药不如炸臭豆腐。
”当我在市集靠臭豆腐日进斗金时,郡主楚小萱却中了迷魂散倒在**席上。
后来我为大殿下造复合弓横扫猎场,用现代战术碾压蛮族大军。皇帝封我为异姓王那日,
秦岚跪在府外求当侧妃。我揽过楚小萱的腰,将香水配方甩进火盆:“王妃爱自由,
本王陪她浪迹天涯——秦姑娘,让让路?”1腐臭味混着雨后的土腥气钻进鼻腔时,
我正躺在半截破草席上,盯着漏风的茅草屋顶发呆。几滴浑浊的雨水不偏不倚砸在眉心,
冰凉黏腻。屋外传来刻意拔高的呵斥,刀子似的刮着耳膜。“……**胚子生的小贱种!
三考连个秀才都中不了,倒有脸死在府里脏老爷的地界?夫人心善,赏你几吊钱滚蛋!
别污了赵府门楣!”一个粗布钱袋砸进来,滚了两圈,停在我手边,
豁口处露出几枚黯淡的铜板。原主残留的记忆碎片裹挟着绝望和不甘,
狠狠冲撞着意识——寒窗十年,屡试不第;生母早逝,嫡母刻薄;兄弟欺凌,前途无望。
最后那点执念,在得知连最后的指望——那桩与城中商贾秦家的婚约也岌岌可危时,
彻底崩断了心弦。军工院最年轻的项目带头人赵勤博士,
竟成了大梁国云州赵家这窝囊废庶子赵勤。我扯了扯嘴角,喉咙里泛上铁锈般的血腥味。
挺好,地狱开局,省得我找**。刚撑着坐起,破木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一个穿着体面绸衫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雨水打湿了他精致的鞋尖。
他嫌恶地用袖子掩住口鼻,眼神扫过这四处漏风的窝棚,像在看一堆秽物。是秦府的管事。
“二公子,”他语气平板,透着公事公办的冷漠,“我家**心善,念及旧情,
不忍当面退婚令您难堪。这是退婚书,您按个手印,两家便算两清了。
”他身后的小厮立刻捧上一个托盘,一份洒金红笺刺眼地摊开,旁边搁着劣质的印泥。
原主残留的那点悲愤猛地烧灼起来。我闭了闭眼,压下不属于自己的情绪。再睁开时,
只剩一片冷冽的平静。我伸手,没碰那退婚书,只把地上散落的铜钱一枚枚捡起,攥在手心,
冰凉硌人。“有劳。”声音嘶哑得厉害,却没什么波澜,“烦请转告秦**,她的‘善心’,
赵勤记下了。”管事眼底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大约觉得我在强撑,只催着按印。
鲜红的指印落在“秦岚”娟秀的名字旁,像一滩凝固的血。人走了,破屋彻底死寂下来。
掌心那七枚铜钱,是我全部的家当,也是这操蛋世界给我的启动资金。军工博士?
我掂了掂那几枚铜钱,无声嗤笑。这年头,造火药不如炸臭豆腐来得实在。
2云州城西的市集,永远弥漫着一股复杂浓烈的气味。
汗味、牲畜味、劣质脂粉味、食物腐败味……浑浊地搅和在一起。我蹲在角落,
面前摆着个豁了口的瓦盆,里面浸泡着几十块灰白、表面长满诡异绒毛的豆腐块。
一股难以言喻的、直冲天灵盖的恶臭正源源不断地从盆里散发出来,
形成一片肉眼可见的“禁区”,行人无不掩鼻绕行,投来厌恶的目光。“赵二?你疯了?
”旁边卖草鞋的老汉捏着鼻子,瓮声瓮气地喊,“这‘霉千王’狗都不碰!
你弄这一盆想毒死谁?”他说的没错,“霉千王”是云州出了名的**货,
穷得实在活不下去的人家才买回去,用重盐重辣勉强压住那臭味,聊以充饥。我没理他,
专注地看着盆里翻滚的气泡。这盆“霉千王”花光了我最后三枚铜钱。剩下的钱,
买了最劣质的菜籽油、一小包粗盐、一丁点茱萸粉,还有一小捆柴火。一个破陶炉,
一口豁了边的铁锅,就是我的全部家当。生火。倒油。劣质菜籽油在锅里“滋滋”作响,
冒出呛人的青烟。恶臭在高温的催化下,陡然升级!
仿佛一百双三年没洗的裹脚布同时在烈日下暴晒。老汉怪叫一声,
连滚带爬地拖着草鞋摊子往后挪了足足两丈远。整个市集这一角瞬间清空,骂声四起。
“哪个杀千刀的煮屎呢?!”“赵家那扫把星!他疯了!”我充耳不闻。油温到了。
用两根临时削尖的树枝做成的长筷,夹起一块滑腻腻、长满绿毛的豆腐,沥了沥水,
轻轻滑入滚油中。“滋啦——!”奇变陡生!那令人作呕的恶臭,在热油的猛烈烹炸下,
竟如同被一只无形的手瞬间扭转!一股难以形容的霸道异香,混合着焦脆、发酵的醇厚气息,
猛地炸开!这香味如此蛮横,瞬间撕裂了市集浑浊的空气,霸道地钻进每一个人的鼻腔。
像沉睡的巨兽被惊醒。原本避之不及的人群,脚步顿住了。捏着鼻子的手迟疑地放下,
贪婪地嗅着这从未闻过的奇香。无数道惊疑、探寻、渴望的目光,
“唰”地聚焦到我这个角落,聚焦到油锅里那几块翻滚着、逐渐变得金黄酥脆的豆腐块上。
第一块炸好的豆腐捞出,沥油。金黄的外壳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油光。
我把它放在一片洗净的树叶上,用小竹刀划开。内里是蜂窝状的、雪白柔嫩的豆腐心,
热气裹挟着那股奇异的浓香喷涌而出。我撒上一点点粗盐和茱萸粉。周围死寂一片。
所有眼睛都盯着那块豆腐,吞咽口水的声音此起彼伏。“此物,名曰‘臭豆腐’。”我开口,
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嘈杂,“闻之奇臭,食之异香。三文钱一块,敢尝者来。
”短暂的死寂后,一个挑着柴火的黝黑汉子最先忍不住了。
他“啪”地拍出三枚铜板:“娘的!老子砍头都不怕,还怕你这块豆腐?!给我来一块!
”他接过豆腐,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带着赴死般的表情,闭眼咬了下去。“咔嚓!
”酥脆的外壳碎裂声清晰可闻。他的表情瞬间凝固。随即,眼睛猛地瞪圆,
脸上肌肉剧烈地抖动了几下,仿佛被雷劈中。“咋样?毒死没?”有人急不可耐地问。
汉子没说话,喉结疯狂地上下滚动,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
另一只手已经迫不及待地伸进怀里掏钱,含糊不清地吼:“再……再来五块!不!十块!
给俺家婆娘娃娃带!”轰!人群炸了锅。那汉子狼吞虎咽、恨不得把舌头吞下去的模样,
就是最好的活招牌!三文钱一块?这霸道的香气,值了!“给我来两块!”“我要三块!
”“排队!排队啊!我先来的!”豁口的瓦盆前,瞬间挤成了沙丁鱼罐头。
铜钱叮叮当当砸进我装钱的破瓦罐里,悦耳至极。油锅翻腾,金黄的臭豆腐一块块捞出,
奇异的浓香彻底征服了云州西市。我机械地炸着豆腐,收钱,
最初的麻木被一种冰冷的亢奋取代。军工博士?我掂量着迅速沉下去的瓦罐。
在这操蛋的世界里,第一桶金,就从征服他们的鼻子和舌头开始。
3臭豆腐摊子成了西市一景,更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破茅屋换成了有瓦遮头的小院,
油锅从一个变成了三个。每日天不亮,小院门口就排起长队,铜钱如流水般涌来。
这泼天的富贵,自然也引来了鬣狗。“都滚开!不长眼的东西!
”一声嚣张的暴喝在人群后炸响。拥挤的队伍像被刀劈开一样,瞬间分开一条通道。
我那名义上的嫡出大哥赵胜,一身锦缎华服,摇着把附庸风雅的折扇,
带着几个满脸横肉、敞胸露怀的家丁,大摇大摆地走到我的摊子前。他拿扇子掩住鼻子,
斜睨着油锅里翻滚的金黄豆腐块,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贪婪和恶毒。“哟,老二,出息了啊?
”赵胜拖长了调子,阴阳怪气,“在这腌臜地方,鼓捣些猪狗食,倒骗了不少铜板?
看来赵家把你扫地出门,反倒是成全了你?”排队的人群噤若寒蝉,敢怒不敢言。
赵家是云州望族,赵胜更是出了名的纨绔恶霸。我眼皮都没抬,专注地翻动着油锅里的豆腐,
声音平淡:“托大哥的福,饿不死。”“饿不死?”赵胜冷哼一声,折扇“啪”地一收,
指着我,“你这**胚子,丢尽了我赵家脸面!弄这些臭气熏天的东西,污了云州地界!
赶紧收拾你这破烂摊子滚蛋!否则……”他身后的家丁配合地撸起袖子,露出粗壮的胳膊,
狞笑着上前一步。气氛瞬间绷紧。排队的人群又往后缩了缩。卖草鞋的老汉急得直跺脚,
却不敢吭声。我停下动作,终于抬眼看向赵胜。他的得意洋洋写满整张脸,
仿佛吃定了我这个卑微的庶弟。我拿起油勺,慢条斯理地舀起一勺滚烫的热油,
那金黄的液体在勺里晃荡,冒着青烟。“大哥,”我开口,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这油,刚滚开。你说,要是泼到人脸上,会不会比臭豆腐还香?
”赵胜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瞳孔猛地一缩,下意识地后退半步。他身后的家丁也僵住了,
看着那勺冒着青烟的滚油,喉结滚动,没人敢上前。“你……你敢!”赵胜色厉内荏地尖叫,
声音都变了调,“我可是赵家嫡长子!”“嫡长子?”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丝冰冷的笑意,
“我现在姓赵,却不再是赵家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哥,要不要试试?”手腕微微前倾,
滚油在勺边荡起危险的弧度。赵胜的脸“唰”地白了。他死死盯着那勺油,额头冒出冷汗。
他毫不怀疑我这个“疯子”真敢泼过来!僵持了足足十息,空气凝固得让人窒息。最终,
赵胜狠狠一跺脚,指着我的手指都在抖:“好!好你个赵勤!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
我们走!”他带着家丁,狼狈地挤出人群,像一群斗败的公鸡。直到他们消失在街角,
凝固的人群才“轰”地一声爆发出议论。“赵二爷硬气!”“吓死我了!
那油真泼下去……”我面无表情地放下油勺,继续炸我的豆腐。心里却清楚,
赵胜的报复绝不会停止。这小小的臭豆腐摊,已经成了风暴中心。4暴风雨来得比预想更快。
几日后一个深夜,瓢泼大雨砸得屋顶噼啪作响。我刚盘点完当日的进项,
铜钱特有的气味混着雨水的土腥,竟让我紧绷的神经有了一丝诡异的安宁。突然,
院门传来一声沉重的闷响,像是有什么重物砸在了上面!我抄起门边一根抵门的硬木棍,
悄无声息地贴到门后。侧耳细听,除了哗啦啦的雨声,只有一种压抑的、断断续续的**,
像受伤的小兽。不像围攻。我猛地拉开门栓。一个湿透的身影顺着打开的门直接倒了进来,
重重摔在冰冷的泥地上。借着屋内透出的微弱油灯光芒,
我看清了那人的脸——一张极其年轻、也极其苍白的脸。雨水冲刷着她精致的眉眼,
长发黏在脸颊颈侧,嘴唇却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嫣红。
她身上华贵的绫罗被泥水和不知名的污渍浸染得不成样子,但依然能看出价值不菲。是女人!
而且身份绝不普通!她似乎还有一丝意识,身体在冰冷的地上蜷缩着,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
喉咙里发出模糊的音节:“热……好热……别碰我……”她的脸颊潮红一片,眼神涣散迷离,
双手无意识地撕扯着自己湿透的衣襟。迷魂散!我脑中瞬间跳出这个词。
这玩意儿在话本里常出现,没想到今天撞上了活生生的案例。麻烦!天大的麻烦!
看这女子的衣着气度,非富即贵,能被人下这种药,背后的牵扯绝对小不了!她倒在我门口,
简直是块烫手山芋!理智告诉我应该立刻关门,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可看着她痛苦蜷缩、意识模糊中依旧喊着“别碰我”的样子,我握着门框的手紧了紧。
这该死的末世前的道德感!我低咒一声,迅速环顾雨幕笼罩的漆黑巷子,确认无人跟踪。
咬咬牙,俯身用力将这湿透滚烫的身体抱了起来。入手轻盈,却烫得惊人。
把她安置在屋内唯一那张简陋的木板床上,我立刻转身去翻找。
臭豆腐生意让我囤了些廉价的绿豆。飞快地熬煮出一碗浓浓的绿豆汤,
又翻出仅有的几味清心降火的草药,捣碎了混入汤中。撬开她紧咬的牙关,
费力地将这碗解毒汤灌了下去。她呛咳了几声,迷蒙的眼睛似乎有瞬间的聚焦,
茫然地看了我一眼,随即又被药力和**的双重作用拖入昏沉。体温似乎降下去一点,
但身体还在无意识地扭动,
断断续续地呓语:“……小萱……走开……走……”折腾了大半宿,
她的呼吸才终于平稳下来,沉沉睡去,只是眉头依旧紧锁。我瘫坐在冰冷的泥地上,
背靠着床沿,疲惫像潮水般涌来。窗外雨势渐小,天色透出一点灰白。麻烦暂时压住了,
但我知道,更大的风暴,才刚刚开始。5天光大亮时,床上的女子终于悠悠转醒。
她猛地坐起,眼神锐利如刀,瞬间扫视这间简陋破败的屋子,
最后落在我身上——我正靠在墙角打盹。她低头检查自己完好的衣物,又摸了摸自己的脸,
眼中的警惕才稍稍退去一丝,但审视的目光依旧冰冷。“你是何人?此处何地?
”她的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却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仪。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言简意赅:“赵勤。这是我家。昨夜大雨,你倒在我门外,中了迷魂散。
”听到“迷魂散”三个字,她脸色微变,眼中闪过一丝后怕和滔天的怒意,
随即又被强行压下。她抿了抿唇,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似乎在判断真伪。“楚小萱。
”她报出自己的名字,语气稍缓,“昨夜……多谢。”楚?大梁国姓!我心下一凛,
面上却不动声色:“郡主不必言谢,举手之劳。”昨夜她的呓语中,我已猜到了几分。
楚小萱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似乎没料到我这个市井小民能一口道破她的身份。
她没再纠结于此,利落地翻身下床,虽然脚步还有些虚浮,
但仪态已经恢复了上位者的从容:“昨夜之事,关系重大。今日之言,望你守口如瓶,
否则……”“昨夜风大雨急,我早早歇下,未曾见过任何人。”我平静地接口。
楚小萱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锐利得似乎要将我穿透。最终,她点了点头,
从腰间解下一块触手温润、雕刻着繁复螭龙纹的羊脂玉佩,
放在那张破旧的木桌上:“救命之恩,不敢言谢。此物暂押于此,他日必有重报。
”她顿了顿,补充道,“若遇难处,持此玉佩到城北‘漱玉轩’,自会有人助你。
”她不再多言,推门而出。清晨微冷的空气涌入,吹散了屋内残留的淡淡药味和女子幽香。
我拿起那块螭龙玉佩,温润细腻,价值连城。郡主楚小萱?这麻烦,似乎比我预想的还要大。
6楚小萱带来的风波暂时平息,但赵胜的报复却如跗骨之蛆。地痞流氓的骚扰变本加厉,
甚至勾结了坊市的小吏,以“污秽市容”为由,对我课以重税。臭豆腐的生意虽好,
却也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这时代的局限——食物易腐,难以远销,利润终究有天花板。
我需要新的支点。楚小萱留下的玉佩,成了破局的钥匙。我没有去城北的“漱玉轩”,
那地方一听就不是普通去处。我去了云州最大的香料行“天香阁”。“掌柜的,借一步说话。
”我将玉佩在柜台上一放,声音不大。正低头拨弄算盘的胖掌柜随意瞥了一眼,
当目光触及那块螭龙玉佩时,整个人像被雷劈中,猛地一哆嗦!他几乎是扑到柜台上,
双手捧起玉佩,仔细辨认,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冷汗“唰”地就下来了。“贵……贵客!
”他声音发颤,腰弯成了九十度,“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您……您有何吩咐?
小店定当竭尽全力!”“我要一些东西。
”我递过去一张早就写好的清单:高度白酒(最好是无色透明的蒸馏酒),
品质最佳的鲜花(茉莉、栀子、桂花等),密封性极好的瓷瓶或琉璃瓶,
纯净的油脂(茶油或杏仁油),还有纯碱、明矾等物。掌柜看着清单,有些迷惑,
但玉佩的威慑力压倒了一切:“有!都有!小人立刻去准备!最好的!马上送来!”很快,
我要的东西被小心翼翼地送进了我租下的一个僻静小院。接下来的日子,
我把自己关在院子里,隔绝了外界的纷扰。
蒸馏、萃取、冷凝、分离、提纯……现代化学实验室里的基础操作,
在这个时代简陋的条件下,变得异常艰难。失败了一次又一次,
刺鼻的怪味和焦糊味弥漫着小院。但我毫不动摇。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午后,
最后一滴清澈芬芳、凝聚着栀子花全部精华的液体,滴入了小小的琉璃瓶中。
我晃动着瓶中那比黄金还要珍贵的液体,馥郁、纯粹、毫无杂质的花香瞬间充盈了整个空间。
成了!香水!真正的、超越这个时**解的香水!我拿着第一瓶成功的栀子花香水,
再次踏入了天香阁。胖掌柜看到我,比上次更加恭敬。我拔开瓶塞,
一缕幽冷纯净、仿佛带着清晨露珠的栀子花香,如同无形的精灵,悄然弥漫开来。
掌柜的猛地吸了一口气,眼睛瞬间瞪得溜圆,整个人僵在原地,如同石化。
他贪婪地、近乎失态地连续深吸了几口,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狂喜,
再到一种近乎朝圣般的虔诚。“这……这是……”他声音抖得不成样子。“香水。
”我言简意赅,“滴一滴于腕间,可留香一日。比熏衣、香囊、香粉如何?”“仙露!
这是仙露啊!”掌柜的激动得语无伦次,
“小人……小人从未闻过如此纯粹、如此持久、如此……如此勾魂摄魄的香气!赵公子!不!
赵大师!您开价!开多少都行!这香露,小店全要了!”他看我的眼神,
已经像是在看一座移动的金山。“不卖。”**脆地收回瓶子,盖好塞子,“合作。
你出铺面、人手、原料、销路。我出方子和核心技艺。利润,三七分。我七,你三。
”掌柜的脸色瞬间涨红,似乎想争辩。但目光触及我腰间若隐若现的玉佩轮廓,
又想到这“仙露”背后代表的泼天富贵,他狠狠一咬牙,
肥胖的身躯猛地躬了下去:“全凭大师吩咐!
”“天香阁”悄然推出一种名为“花神泪”的香水,如同在云州城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那超越时代的、纯粹而持久的芬芳,瞬间俘获了所有贵族仕女的心。一瓶难求,价比黄金!
这泼天的富贵和声望,终于惊动了另一个人——秦岚。一个午后,
我正与天香阁掌柜核对账目,门外传来轻柔而略显局促的通报:“赵……赵公子,
秦家**……想见您一面。”掌柜识趣地退下。我抬眼,看到了站在门口的秦岚。
她比记忆中清减了许多,穿着一身素雅的月白襦裙,发间只簪了一支简单的玉簪,
脸上带着一丝刻意维持的平静,却掩不住眼底的复杂和一丝……悔意?“赵……赵勤。
”她开口,声音有些干涩,目光飞快地扫过我身上用料考究但样式低调的新衣,
又落在我身后堆着账册和香料瓶的案几上,最终定格在我脸上,“你……还好吗?”“托福,
饿不死。”我语气平淡,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秦**请坐。有事?
”我的疏离让她微微一僵。她依言坐下,双手无意识地绞着手中的丝帕,沉默了片刻,
才低声道:“我……我当初退婚,实是迫于家族压力,并非……并非我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