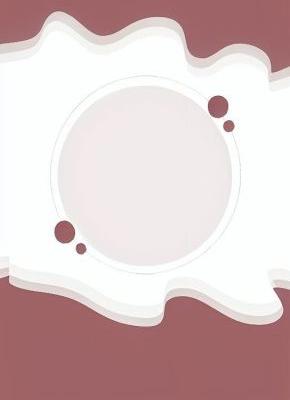
易琴箫日记终端:《再次见到严仪是在两年后的丘淳。(丘淳:中部地区的直辖市,
严仪故乡。)在一个荒废仓库的地下室。那时的他已经辞去教授职位,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
我把他接了回去。他很开心。第二天我们举办了隆重的世纪婚礼。幸福洋溢在我俩脸上,
全场嘉宾都为我们祝福。我们终于可以一辈子在一起了。
92年夏(严仪20岁易琴箫15岁易琴锦8岁)第一次见到严教授是在我八岁生日宴上,
那时他还只是个成绩优异的普通医学生。在氢气球被放出满天飞翔的时刻,在阳光下,
在鲜花里,在奏乐演唱间,在响彻云霄的掌声中,爸爸牵着他的手从人群中徐徐走来。
那一天,严教授成为了我哥——易琴箫的私人家教老师。
当爸爸亲自将严教授带到哥哥易琴箫身边时,我看见了哥哥眼里的悸动。
我知道哥哥是真的很喜欢严教授,可少年的喜欢粗鲁又莽撞,懵懂又青涩,
加上他自身错误的认知导致了后来两人的悲剧。
1995年春(严仪23岁易琴箫18岁易琴锦11岁)在严教授进入我家的第三年,
我发现了他与我哥的秘密…“严老师,你真的是Alpha吗?”易琴箫放下手中的书,
外头看向站在窗台边上的严仪——蓬松的短发在风中左右摇摆无意间翘起一根呆毛,
简洁干净的白色连帽卫衣上杵出一大截苗条脖子,
黑色修身牛仔裤把两条腿修得跟筷子般细长,
身上植物花香的洗衣粉味掺杂着实验室里不知名化学药物味飘进屋内。“?
”严仪不解的回头看向易琴箫,没有搭话。这个太子爷脾气古怪,性格顽固不化,
这三年来没少让他吃瘪,他真是一点也不想过多招惹。总之能少说话就少说话,
能少作为就少作为。“你不说话是几个意思?嫌我爸开的薪酬不够?”易琴箫说完,
站起走到严仪身边,目光绕着他上下打量。严仪看着才刚成年却已经同自己一样高,
体型还格外比自己强健的易琴箫心里发怵,挤出一抹标准的假笑,轻声问道:“题看好了吗?
”“你真的是Alpha吗?”易琴箫盯着他的眼睛又问了一遍。“不然呢?
”严仪歪头反问道。易琴箫听到回答,对着他露出一抹不明意味的微笑,严仪心悸,
想往后退的想法还没践行就毫无征兆被易琴箫一把揽住腰往怀里带。易琴箫抱住严仪,
凑在严仪耳边悄声说道:“不像啊,让我确认一下。”严仪听完,全身一惊,
猛然推开易琴箫,大吼道:“别开玩笑了!易琴箫,你太恶劣了!
”易琴箫被推倒在半开的玻璃门框上后脑勺撞得生疼,他抬头恶狠狠的瞪着严仪,
怒道:“**敢推我?”严仪被易琴箫的眼神和语气吓得发怵,不由脚步向后倒退,
正想说些什么来辩解,就被易琴箫猛扑过来推倒。严仪猝不及防的摔倒在地,摔得脑袋发昏,
眼冒金星,脊椎骨与胳膊肘酸软疼痛,一时之间动弹不得。下一秒,
严仪就被易琴箫死死抓住头发往沙发拖去,严仪痛的双腿直蹬,
想要抬手挣扎却因为软麻怎么也举不起来。易琴箫把严仪拖起甩在沙发上,捆住双手,
咧嘴笑道:“恶劣?你第一天认识我?我看你不爽很久了,今天让你尝尝好的。
”严仪很瘦很瘦,长期的营养不良让他发质微微泛黄,发丝蓬松又细软,皮肤惨白,
四肢缺力,典型的文弱白净小书生。他哪招架得住易琴箫的极端暴力,
身体和心理被吓得不轻。看见易琴箫绑住自己的双手,所有不好的预感都一股脑蹿上心头,
严仪瞪大双眼吼道:“你要干什么?放开我!”他不断挣扎,用脚去踢踹易琴箫,
被稳稳抓住。易琴箫紧紧掐住严仪的脚踝,邪魅的笑道:“严老师,你真的好瘦啊!我听说,
你家里很缺钱经常吃不饱饭,看来是真的。”“放开我!”严仪愤恨的看着易琴箫怒道。
并用合二为一的双手去推易琴箫的头,被易琴箫一巴掌轻易拍开。“严老师,你很缺钱,
做我的情人,钱和饭管够。”易琴箫抵着严仪的下巴说道。“滚!我不需要!
”严仪咬牙恶狠狠的瞪着易琴箫,眼里写满屈辱与愤怒。可易琴箫压根不在乎也不理会。
“滚!滚啊!滚!我不要!我不需要!滚!滚!
滚——”严仪绝望崩溃的嘶吼声划破整座庄园别墅沉寂的天空。那一天,家里全日休,
只剩哥哥,教授,我三人在家。哥哥因为要补课被迫被爸爸妈妈留下来同严教授关在家,
他以为我也和爸妈一起外出了,但其实那天我约了同学外出游玩,
直到中午被同学爽约临时在家。我嫌无聊加上被临时爽约心里不痛快,
便想着上楼去找哥哥玩,走到门口就目睹一切。那时我还小,不懂什么,
可严教授撕心裂肺的喊叫却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
这也为后来我爱上他埋下了一颗深深的种子。
1997年秋(严仪25岁易琴箫20岁易琴锦13岁)自十一岁那年目睹那件事后,
未来两年里,我都无法做到正面直视严教授。直到两年后,我与家里吵架跑了出去。
这一年我十三岁,严教授二十五岁。他经过自己超常的努力,
成为了业内一名非常优秀的学者。在缺乏陪伴与关爱的家庭中成长,
稍大一点我就学会了用叛逆与调皮捣蛋来引起父母的关注,可每次效果都适得其反。
我委屈的走在别墅区偌大的外景地段,边走边啜泣。“琴锦?”严教授意外的喊住我。
后面我告诉他,我跟家里人吵架跑了出来,他温柔的蹲在地上把我抱在怀里安慰,
他的身材干瘦,衣服上有一股清爽的花香,可怀抱却格外温暖。“别哭了,
严老师带你去个地方好不好?”他笑着伸出手邀请我握上去。我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到了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与家完全不同的,破旧,肮脏,黑暗,恐怖,冰冷,
阴湿的地方——凹凸不平石板路的石板路布满苔藓,稍不注意就是滑倒,
潮湿一点的地方仔细看就会有极其恶心的黑色软体虫与蚯蚓在爬行,
并且你不会知道哪一块儿石板是松动的,脚下一不留神就会中大奖,
别上一腿掺杂不少软小虫子的臭垢污水。路面两侧高立的洞砖墙上青苔密布,杂草也不少,
顶上修砌着朽木破房,不止有恶心的线形虫,
到蜗牛与鼻涕虫以及它们白花花的原液爬行痕迹…浓重的泥腥味里混合着木板烂掉的霉湿味,
地下污水的闷臭味,
和粪土发酵的热潮味最后才是一点点微乎其微到一晃头就会被遗忘的饭香烟火味…暮色暗沉,
看着深黑的巷子没有一丝灯光,每迈开步子往幽长的绿阶踏出一步,
我的身上就起一层鸡皮疙瘩。严教授在前面小心翼翼的探着石板,
确保没1有松动才叫我走动,他一步,我一步,一步,一步…我忍不住抓住他的衣袖,
还是一样的连帽白色卫衣,不禁让我想起两年半前的那个中午。现在的我进入青春期,
已经开始性启蒙,知道了很多事情。“怎么了?琴锦。”严教授回头看着我。“老师…我,
我怕,我冷,我不想走了,我们回家吧。”我低着头说道。“好,我们路过那家人户就回家,
好不好?”严教授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木房子说道。我答应他。到屋子外往里看,
昏暗的黄灯下,是视力不好的佝偻老人在打补丁,黑色污垢覆盖的方桌上,
同我大小年纪的瘦弱小孩在写作业。“老师,您带我来这是为了什么?”我忍不住开口问。
“你觉得是为了什么?琴锦。”严教授微笑着问我,我俩一同踏上折返的路,
脚下基本看不清地板了,他还是像来时一样,在前面小心翼翼的试探着松动的石板为我开路。
出了巷子来到马路上——一片完全不同的敞亮整洁干净的天地,我瞬间感到了解脱与救赎。
心里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感到诧异与吃惊。一股不真实感围绕在我心头,
我回头看了看身后深黑不见底的巷子,又看了看面前马路对面繁华,宁静和谐美好的都市,
心里震撼感慨良多。坐在回别墅的路上,严老师告诉了带我去那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