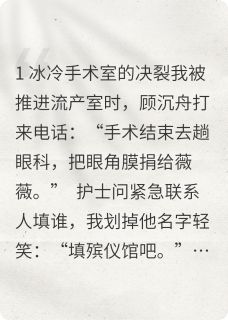
1冰冷手术室的决裂我被推进流产室时,顾沉舟打来电话:“手术结束去趟眼科,
把眼角膜捐给薇薇。”护士问紧急联系人填谁,我划掉他名字轻笑:“填殡仪馆吧。
”后来他跪在我墓碑前发疯:“你回来!我把眼睛挖给你!”可当大火吞没我们时,
我却把唯一氧气罩扣在他脸上。“顾沉舟,这次我真不要你了。
”---冰冷的无影灯悬在头顶,像一轮没有温度的太阳,刺得人眼睛发涩。
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钻进鼻腔,沉甸甸地压在肺叶上,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一股生铁般的腥气。身下的手术台硬得硌人,
金属特有的寒意透过薄薄的无菌布,丝丝缕缕地往骨头缝里钻。“苏晚?
”戴着蓝色手术帽、只露出一双冷静眼睛的医生低头看我,声音隔着口罩,显得有些遥远,
“最后一次确认,自愿终止妊娠,妊娠八周,手术知情同意书已签署,对吗?
”我的指尖在身侧冰凉的金属台沿上蜷缩了一下,指甲刮过光滑的表面,
发出一点细微的、只有我自己能听见的摩擦声。喉咙里干得发紧,像塞满了粗糙的沙砾。
我张了张嘴,想发出一个“对”字,却发现声带像是锈死了,只挤出一点微弱的气音。“对。
”我闭上眼,用尽力气,终于把这个字吐了出来。声音干涩得如同枯叶碎裂。
就在医生微微点头,准备示意护士开始术前准备时,我放在旁边置物柜上的手机,
突兀地、执拗地震动起来。嗡嗡的声响,在寂静得只剩下仪器低鸣和呼吸声的手术室里,
显得格外刺耳,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疯狂撞击玻璃。护士走过去看了一眼屏幕,
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手机,隔着几步的距离递向我:“苏**,是顾先生的电话。要接吗?
”顾沉舟。这个名字像一根烧红的针,猝不及防地扎进我的神经末梢。心脏猛地一缩,
随即是铺天盖地的麻木和一种近乎荒谬的钝痛。他打来做什么?是终于想起来,
他法律上的妻子今天正在手术台上,准备流掉他们“意外”得来的孩子?
还是…来看我的笑话,确认我是否足够痛苦?护士举着手机,屏幕执着地亮着,
那个熟悉的名字在跳动。手术室里所有人的目光,或探究,或同情,或纯粹的等待,
都若有若无地落在我身上,像一层无形的、令人窒息的网。
我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带着消毒水味道的空气,那气息**得肺叶生疼。然后,
我慢慢地、极其缓慢地,抬起那只没有打点滴的手。指尖因为冷意和紧张而微微颤抖,
但我还是异常平稳地,按下了绿色的接听键,并且点开了扬声器。
顾沉舟低沉而略显不耐的嗓音,瞬间在空旷安静的手术室里扩散开来,
每一个字都清晰无比地砸在冰冷的墙壁上,又狠狠反弹回来,
撞进我的耳膜:“手术结束了吗?”没有称呼,没有问候,单刀直入,直奔主题。
那语气平淡得像在询问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是否打印好了。我闭着眼,
长长的睫毛在苍白的皮肤上投下脆弱的阴影,没有说话。身侧的手指,在无菌布下死死攥紧,
指甲深深陷进掌心,试图用这点微不足道的刺痛来抵抗心脏深处那灭顶般的空洞。
他似乎也并不期待我的回答,短暂的停顿后,那带着不容置喙命令口吻的话语,
便如同淬了冰的刀子,精准无误地捅了过来:“结束之后,直接去一趟三楼眼科。
薇薇那边已经联系好了,她的眼角膜移植手术,不能再拖了。你把你的,捐给她。
”嗡——仿佛有一道无声的惊雷在脑海里炸开,所有的声音都在瞬间被抽离了。
只剩下他最后那句冰冷的话,在死寂的手术室里无限循环、放大。“你把你的,捐给她。
”捐给她?捐给林薇薇?原来如此。原来这才是他打来这通电话的真正目的。不是关心,
不是询问,更不是挽回。是为了他心尖上那抹永恒的白月光——林薇薇。她需要眼角膜,
而我苏晚,恰好有一双健康的眼睛,还恰好……躺在了手术台上,
成了一个可以被他随意处置的“物件”。一股浓烈的、带着铁锈味的腥气猛地涌上喉头。
胃里翻江倒海。我死死咬着下唇,口腔里瞬间弥漫开一股血腥味,才勉强压下了那阵恶心。
原来我的孩子,我腹中这块与他血脉相连的肉,在他眼里,
甚至比不上林薇薇重获光明的一个机会。他不仅要拿走这个孩子,还要顺便,挖走我的眼睛。
多么完美的废物利用。“苏晚?”电话那头,顾沉舟似乎因为我长久的沉默而更加不耐,
声音沉了下去,带着惯有的、掌控一切的压迫感,“听见没有?
别给我玩什么沉默或者装死的那一套。手术结束,立刻去眼科办手续!薇薇等不起!
”他以为我在赌气?在用沉默威胁他?在他眼里,我苏晚,连沉默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的痛苦,我的绝望,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场可笑的、为了引起他注意的表演?
一股冰冷的、带着毁灭意味的火焰,猛地从心脏最深处窜起,瞬间烧尽了所有的麻木和空洞。
那火焰如此猛烈,甚至驱散了手术室的寒意。我猛地睁开眼,眼底一片赤红,没有泪,
只有一片被烧灼后的荒芜死寂。“顾沉舟。”我的声音响了起来,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
却异常地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这平静之下,是彻底焚毁后的灰烬。
电话那头似乎顿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会用这样的语气直呼他的名字。
我盯着头顶那盏惨白的无影灯,一个字一个字,清晰无比地吐出来,
每一个音节都像是冰棱坠地,碎裂成渣:“你听好了。”“我的孩子,
不是为你那朵娇弱的小白花准备的祭品。”“我的眼睛,更不是你可以随意施舍给她的礼物!
”“她林薇薇的眼睛是瞎了,可你的心,早就烂透了!”最后一句,几乎是嘶吼出来的,
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和深入骨髓的恨意。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几秒钟后,
顾沉舟的声音才再次响起,那声音里的寒意,隔着电波都能将人冻僵:“苏晚,你再说一遍?
”那是一种风雨欲来的暴怒。我扯了扯嘴角,想笑,却发现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如同石雕。
再说一遍?何必呢。该说的,不该说的,
连同这三年来积攒的所有卑微、隐忍、爱恋和此刻滔天的恨意,
都在刚才那几句话里燃烧殆尽了。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动作干脆利落,没有丝毫犹豫。
屏幕瞬间暗了下去,那个名字也随之消失。手术室里死寂一片。医生和护士都屏住了呼吸,
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刚才那通电话的内容,足以让任何一个人感到不寒而栗。
“苏**……”拿着术前通知单的年轻护士小心翼翼地走上前,
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大概是被刚才那场隔着电话的交锋吓到了,
“麻烦您确认一下,紧急联系人……还是填顾沉舟先生吗?”紧急联系人?多么讽刺的词。
曾经,那张薄薄的纸上,我无比虔诚地写下他的名字,一笔一划,
都带着满心的依赖和甜蜜的幻想。幻想着如果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
第一个冲进来、为我担忧心疼的人,会是他。现在想来,真是愚蠢得可笑。他顾沉舟,
只会是我的催命符,绝不会是我的救命稻草。我抬起手,
那只手因为刚才情绪的剧烈波动而微微颤抖着,指尖冰凉。我摸索着,
从护士手中接过了那张轻飘飘却重若千钧的纸。目光落在“紧急联系人”那一栏。
“顾沉舟”三个字,曾经是我心尖上的朱砂痣,如今,却是我眼中最毒的刺。没有丝毫犹豫,
我拿起夹在板子上的笔。笔尖是冰冷的,像此刻我的心。我用力地、狠狠地,
在那三个字上划下!横!竖!撇!捺!黑色的墨水像污浊的毒血,
瞬间覆盖了那个曾经让我魂牵梦绕的名字。笔尖穿透了纸张,发出“嗤啦”的轻响,
仿佛在撕裂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往。我划得那么用力,那么决绝,
像是在亲手斩断一根连着心脏的毒藤,剧痛,却带着一种解脱的快意。
直到那个名字彻底被凌乱、粗暴的黑线掩盖,再也看不出原本的形状。
护士看着那几乎被划烂的一栏,脸上露出惊愕和不知所措。我停下笔,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
胸腔里空荡荡的,所有的爱恨情仇似乎都随着那几道黑线被划走了,
只剩下无边无际的荒凉和疲惫。我轻轻地将那张纸递还给护士,然后,抬起头,看向她。
脸上,缓缓地,绽开一个极其浅淡、极其空洞的笑容。那笑容里没有一丝温度,
像开在冰原上的花。“不填他了。”我的声音轻飘飘的,如同叹息,
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尘埃落定的平静。在护士茫然的目光中,我顿了顿,
用那种平静到可怕的语气,清晰地补了一句:“填殡仪馆吧。
”“……”整个手术室陷入了更深的死寂。空气仿佛凝固了,
只剩下仪器单调而冰冷的“嘀嗒”声,在无声地丈量着时间。护士拿着那张被划烂的纸,
手抖得厉害,脸色煞白,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医生也沉默着,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最终只是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没有人在说话。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
身体的麻药针剂被推入血管,一股冰凉的液体迅速蔓延开。意识如同沉入水底的石头,
开始变得模糊、沉重。视野里的无影灯光晕开始扩散,旋转,最后变成一片混沌的白。
在彻底失去意识的前一秒,我仿佛听见一声遥远的、沉闷的巨响,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腔深处彻底崩塌了,碎成了齑粉。没有痛感,
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冰冷的虚无。也好。就这样吧。顾沉舟,如你所愿。我们之间,
连同这个未曾谋面的孩子,一起……埋葬了。
2苏醒后的绝望深渊……意识是被一阵阵尖锐的、无法忽视的疼痛唤醒的。
那疼痛来自小腹深处,像有无数把钝刀在里面缓慢地绞动,
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那脆弱的伤口,带来一阵阵窒息般的痉挛。喉咙干得冒烟,
每一次吞咽都如同刀割。我费力地睁开沉重的眼皮,
视野里是医院病房熟悉的、令人压抑的米白色天花板。空气里依旧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
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血腥气。“晚晚?晚晚你醒了?
”一个带着哭腔的沙哑声音在耳边响起,充满了担忧和心疼。我艰难地转动僵硬的脖子,
看到闺蜜唐棠红肿得像桃子一样的眼睛。她扑在床边,紧紧抓着我的手,她的手心全是冷汗。
“吓死我了……你昏睡了一天一夜……”她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大颗大颗地砸在我的手背上,
滚烫,“感觉怎么样?疼不疼?饿不饿?要不要叫医生?”我张了张嘴,喉咙火烧火燎,
发不出一点声音,只能虚弱地摇了摇头。目光扫过病房,除了唐棠,没有别人。意料之中,
却还是让心口那空荡荡的冷意又加深了一层。唐棠看着我灰败的脸色和空洞的眼神,
似乎明白了什么。她咬了咬嘴唇,脸上闪过愤怒和心疼交织的情绪,
最终化为一声哽咽的叹息。她小心翼翼地扶着我,用吸管喂我喝了几口温水。
温水流过干裂的喉咙,带来一丝短暂的缓解,却浇不灭心底那片冻土。身体的疼痛是剧烈的,
清晰的,但它似乎被隔绝在了一层厚厚的玻璃罩子外面。真正吞噬我的,
是心口那个巨大的、被生生挖走的空洞。那里不再流血,只剩下麻木的、呼啸的寒风。
孩子……没有了。那个在我身体里悄然孕育了八周的小生命,
那个曾让我在绝望的婚姻里抓住一丝微弱光亮的小小希望,被他的亲生父亲,
以最冷酷的方式,宣判了死刑。为了另一个女人。“晚晚……”唐棠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忍不住,带着压抑的怒火低声道,“顾沉舟那个王八蛋!
他……他昨天下午来过了!”我的眼睫几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像濒死的蝶翼。
空洞的目光终于有了一丝聚焦,看向唐棠。“他来了?”声音沙哑得厉害,像破旧的风箱。
“嗯!”唐棠用力点头,眼圈更红了,是气的,“就在你刚被推回病房不久!那脸色……啧,
阴沉得跟暴风雨前的天似的!进来二话不说,就问你手术是不是做完了!
”唐棠模仿着顾沉舟那冰冷迫人的语气,每一个字都像冰锥扎在我心上。“我气不过,
骂了他两句畜生不如,他……”唐棠的声音哽了一下,带着后怕,“他当时那个眼神,
简直像要吃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质问我凭什么替他决定?
质问我是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说……他说……”唐棠吸了吸鼻子,
眼泪又掉下来:“他说‘我的孩子,轮不到她苏晚一个人做主!’晚晚,你说他还是人吗?
他怎么能这么对你?”我的孩子……轮不到我一个人做主?呵。多么可笑又霸道的宣言。
在他决定用我的孩子去换林薇薇的眼角膜时,他可曾想过,这也是我的孩子?
在他打来那通残忍的电话时,他可曾有过一丝一毫的犹豫?现在,孩子没了,
他倒想起来“做主”了?是来兴师问罪的吗?质问我为什么没有乖乖听话,
没有在流掉孩子之后,立刻把眼睛也剜出来,双手奉上给他的薇薇?一股冰冷的恨意,
混杂着强烈的恶心感,猛地冲上喉头。我猛地推开唐棠递过来的水杯,俯身干呕起来。
胃里空空如也,只呕出一些酸涩的苦水,烧灼着食道,也烧灼着我残存的理智。“晚晚!
你别激动!别这样!”唐棠吓得手忙脚乱,拍着我的背,声音带着哭腔,
“我们不提那个**了!不提了!你好好养身体,养好了我们就离开!离他远远的!”离开?
是的,必须离开。这个地方,这个男人,连同这三年不堪回首的婚姻,都让我窒息。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和屈辱的味道。我喘息着,用尽力气压下翻腾的胃液和恨意,
重新躺回枕头里。身体的虚弱和精神的极度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意识又开始模糊。
在陷入昏睡之前,我抓住唐棠的手,指甲几乎嵌进她的肉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我……”“我要出院……越快越好……”“帮我……离开这里……”唐棠紧紧回握住我的手,
用力点头,眼泪无声地滑落:“好!好!晚晚你放心!我帮你!我一定帮你离开这个鬼地方!
”得到她的承诺,紧绷的神经骤然松懈,黑暗再次温柔地、不容抗拒地席卷而来,将我吞没。
这一次,昏睡中不再是空茫的虚无,而是不断闪现的冰冷手术灯,男人冷酷命令的话语,
还有……一片刺目的血红。……身体像是被拆散了重组,
每一次移动都伴随着剧烈的疼痛和沉重的疲惫。在唐棠的全力奔走和打点下,仅仅三天后,
我就拖着尚未恢复元气的身体,强行办理了出院手续。医院门口,
初秋的风已经带上了明显的凉意,吹在脸上,像细小的冰针。我裹紧了唐棠带来的厚外套,
脸色苍白如纸,嘴唇毫无血色,整个人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慢点,晚晚,小心台阶。
”唐棠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满脸担忧。我点点头,每一步都走得极其缓慢,
小腹的伤口牵扯着,冷汗瞬间浸湿了鬓角。正要迈下最后一级台阶,
一辆线条冷硬、通体漆黑的劳斯莱斯幻影,如同蛰伏的巨兽,猛地一个急刹,
精准而霸道地横停在我们面前,挡住了去路。车门被大力推开。
锃亮的黑色皮鞋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接着是剪裁精良、一丝不苟的昂贵西裤。
顾沉舟高大的身影从车里出来,带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强大压迫感。
他俊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薄唇抿成一条冰冷的直线,深邃的眼眸像淬了寒冰的深潭,
直直地射向我。那目光锐利如刀,带着审视,带着毫不掩饰的怒意,
还有一丝……我无法理解的阴鸷和焦躁。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不可饶恕的事情。
“苏晚。”他开口,声音低沉,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裹挟着冰冷的寒意,
“谁允许你出院的?”唐棠瞬间就炸了,像护崽的母鸡一样挡在我身前,
怒视着顾沉舟:“顾沉舟!你还有脸来?晚晚出不出院关你屁事!她现在跟你没半毛钱关系!
你给我让开!”顾沉舟连眼角的余光都没给唐棠一个,他的视线如同冰冷的锁链,
牢牢地锁在我身上,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容置疑的掌控。“跟我回去。”他命令道,
语气是不容置喙的强硬,“你的身体还没好,需要休养。”休养?我几乎要冷笑出声。
他是在关心我的身体?还是在关心林薇薇的“眼角膜供应源”是否完好无损?
一股冰冷的恨意和强烈的恶心感再次翻涌上来。我强忍着,指甲死死掐进掌心,
用疼痛维持着最后一丝清醒。我抬起眼,
迎上他那双曾让我痴迷沉沦、如今却只感到彻骨寒冷的眸子。我的眼神平静无波,
像一潭死水,映不出他丝毫的倒影。“顾总,”我开口,声音因为虚弱而低哑,
却清晰地在这冰冷的空气里传开,“我的身体,我自己负责。不劳您费心。
”顾沉舟的瞳孔似乎猛地收缩了一下,
显然没料到我用这样疏离的、公事公办的称呼和态度回应他。他周身的气压瞬间变得更低,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了。“苏晚,”他往前逼近一步,高大的身影投下浓重的阴影,
将我完全笼罩,那股熟悉的、带着侵略性的冷冽气息扑面而来,让我胃里一阵翻搅,
“别挑战我的耐心。跟我回去,别让我说第三遍。”他伸出手,
那只骨节分明、曾被我无数次描绘过的手,此刻却带着不容抗拒的力量,
径直朝我的手腕抓来!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我皮肤的瞬间,我用尽全身力气,
猛地往后一退!动作牵扯到腹部的伤口,一阵尖锐的剧痛袭来,眼前瞬间发黑,
冷汗涔涔而下。但我死死咬住下唇,硬生生挺住了,没有发出一丝痛呼。顾沉舟的手,
抓了个空。他停在半空,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目光沉沉地看着我,那里面翻涌着风暴,
是错愕,是震怒,还有一丝……难以置信?“顾沉舟,”我看着他停在空中的手,一字一句,
声音不高,却清晰地敲打在这凝滞的空气里,带着一种尘埃落定般的死寂,“孩子没了。
”我顿了顿,目光缓缓上移,再次对上他那双深不见底、此刻却翻涌着复杂情绪的眼眸,
继续用那毫无波澜的声音说:“如你所愿。”“现在,请你让开。”“我们之间,两清了。
”“两清?”顾沉舟像是被这两个字烫到了,他猛地收回手,
俊美的脸上第一次清晰地出现了裂痕。那是一种被冒犯、被彻底否决的狂怒,
混合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近乎失控的阴鸷。他死死盯着我,眼神锐利得像是要把我刺穿,
“苏晚,谁给你的胆子说两清?”他再次逼近,强大的气场压迫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伤口处的疼痛也更加剧烈。他俯视着我,声音压抑着狂暴的怒火:“你以为流掉孩子,
就能抹掉一切?就能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他的目光如同实质的冰锥,
狠狠钉在我的小腹上,那眼神复杂得可怕,有愤怒,有怨恨,
甚至……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痛楚?但这荒谬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立刻被滔天的恨意淹没。
“你擅自做主杀了我的孩子,”他每一个字都像是淬了毒,“这笔账,我们慢慢算!
”“你的孩子?”一直护在我身前的唐棠再也忍不住,她像一头被激怒的小狮子,
猛地推了顾沉舟一把,虽然撼动不了他分毫,但那份勇气和愤怒却爆发得淋漓尽致,
“顾沉舟你要不要脸?!那难道不是晚晚的孩子?不是你亲口在电话里命令她打掉,
好给你的薇薇腾位置、捐眼睛的吗?!现在孩子没了,你倒装起深情爸爸了?我呸!
你恶不恶心!”“闭嘴!”顾沉舟像是被戳中了最痛处,猛地转头,暴戾的目光射向唐棠,
那眼神里的凶戾足以让普通人胆寒。唐棠被他的气势慑得一滞,脸色白了白,
但依旧梗着脖子,毫不退缩地瞪回去。就在这时,顾沉舟口袋里的手机突兀地震动起来,
嗡嗡的声音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格外刺耳。他烦躁地掏出手机,目光扫过屏幕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