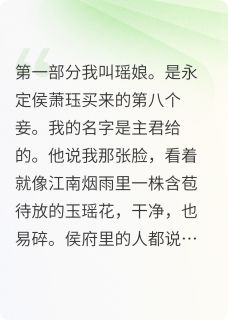
第一部分我叫瑶娘。是永定侯萧珏买来的第八个妾。我的名字是主君给的。他说我那张脸,
看着就像江南烟雨里一株含苞待放的玉瑶花,干净,也易碎。侯府里的人都说,
主君是真心疼我。只有我知道,他不是疼我,是喜欢我这副干净又易碎的模样。
就像猫喜欢爪下那只瑟瑟发抖的雀儿,不是为了果腹,只是为了享受那份生杀予夺的**。
因为,我本不叫瑶娘。我姓沈,名唤知意。我的父亲,是前朝内阁首辅,文华殿大学士,
沈惟。一年前,沈家被参结党营私,贪墨军饷,一道圣旨下来,满门抄斩。
父亲与兄长在西市的铡刀下身首异处,母亲与族中女眷或自缢,或流放,偌大的沈家,
一百七十八口,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而那本罗织了沈家所有罪名的奏疏,
就出自当今圣上最信任的孤臣,权倾朝野的永定侯,萧珏之手。我是沈家唯一的活口。
不是我命大,是萧珏留下的。他从教坊司的死牢里将我提出来,像买一件货物一样,
给了我新的身份,新的名字,然后将我锁进了这座比死牢更华丽的囚笼。他要我活着,
亲眼看着他这个仇人,是如何享尽荣华,权势滔天。他要折断我的骨头,磨灭我的心志,
让我从一个簪缨世族的嫡女,变成一个只能仰他鼻息、摇尾乞怜的玩物。
恨意是埋在腐肉下的种子,在黑暗里无声无息地疯长。但我不能表现出来。
我必须是那个最温顺、最怯懦、最不争不抢的瑶娘。萧珏来我房里的次数不多。
他像一尊没有温度的玉雕神佛,即便坐在我的床沿,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
也永远隔着一层冰冷的雾。他从不与我同寝,只喜欢看我为他煮茶。我的手不能抖。
哪怕那双递过茶盏的手,就是曾亲手签下抄没沈家文书的手。“手艺不错。”他呷了一口,
声音清冷,听不出情绪,“和你父亲一样。”轰的一声。我脑中的弦几乎要断裂。
他总是在不经意间,用最平淡的语气,将我钉在耻辱柱上。我垂下头,
长长的睫毛掩住眼底翻涌的血海,声音细若蚊蚋:“主君谬赞了。”他放下茶盏,起身,
修长的手指抬起我的下巴,强迫我与他对视。“记住,你现在姓瑶。”他的指腹冰冷,
像蛇的信子,“沈家那个不识时务的老东西,已经在地底下化成灰了。你若还念着他,
只会给自己招来祸事。”恐惧攥住了我的心脏,又或者是别的什么。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
那张俊美到毫无瑕疵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我忽然明白,他不是在威胁我。
他是在……驯养我。他要我忘记过去,忘记仇恨,心甘情愿地做他金笼里那只唱歌的雀儿。
我顺从地点头,眼泪恰到好处地滑落。他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松开手,
用一方锦帕拭了拭方才碰过我的手指,仿佛沾了什么脏东西,然后转身离去。门关上的瞬间,
我瘫软在地,浑身被冷汗浸透。我不能死。我要活着。活到……能亲手杀了他那一天。
转机发生在我入府的第三个月。起因是我的贴身侍女,青黛。
她是我从沈家带出来的唯一一个旧人,当年萧珏把我从教坊司提出,我跪在地上求他,
他或许是心情好,便允我带走了这个与我一同长大的丫头。在这座冰冷的侯府,
青黛是我唯一能汲取到暖意的地方。可我忘了,暖意,在这座府里是最奢侈,
也最致命的东西。府里风头最盛的,是刘姨娘。她是兵部尚书的庶女,为人骄纵,
最是看我不顺眼。那日,她新得了一匹云锦,唤各房的姬妾去她院里赏玩。我称病未去,
她便将火气撒到了去替我回话的青黛身上。等我再见到青黛时,
她已经被人从池子里捞了上来,浑身湿透,气息奄奄。
刘姨娘身边的婆子趾高气扬地站在一旁,冷笑道:“你这丫头,手脚不干净,
竟敢偷窃主子的珠钗,被发现了还想跳湖寻死。若不是我们姨娘心善,早就把你打死了事。
”我看着青黛苍白的脸,和她紧紧攥在手里,那枚属于我的、早已不值钱的旧银簪,血,
一瞬间冲上了头顶。那不是偷,是抢。是刘姨娘看上了我这枚簪子,青黛不给,
她们便下了狠手。“瑶娘,”青黛抓住我的手,气若游丝,
“别……别跟她争……我们斗不过的……”她咳出一口血,眼睛里的光,一点点地黯了下去。
我抱着她渐渐冰冷的身体,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哀莫大于心死。不,我的心没有死。
它只是被冻住了,冻成了一块淬着剧毒的寒冰。我将青黛葬在了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下。
那一夜,我没有睡。我坐在窗前,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脑中前所未有地清明。父亲曾说,
我于经史子看过不忘,有过目成诵之能。沈家藏书阁,号称收尽天下典籍,
我自七岁起便泡在其中,十年寒暑,那些书卷里的文字,早已刻进了我的骨血里。
那里不仅有诗词歌赋,
还有历朝历代的卷宗、百官的履历、世家大族的秘闻……那些被尘封在故纸堆里的东西,
是比刀剑更锋利的武器。我闭上眼。脑中那座庞大的记忆宫殿,开始缓缓运转。
一排排书架在我意识中浮现,我精准地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大周官员考绩录·卷七十三·兵部》。我看到了刘姨娘的父亲,兵部尚书刘振。【刘振,
景元二十三年进士,初任淮南盐运司判官……景元二十七年,淮南大旱,官仓亏空,
有盐商程某,献银十万两,助其填补亏空,后,程某垄断两淮盐路,获利巨万。
此事由时任巡盐御史张澄弹劾,然奏本未至御前,张澄便因“失足”落水而亡。同年,
刘振擢升兵部员外郎……】盐商程某。我记得这个名字。他是刘振的妻舅,
也就是刘姨娘的亲娘舅。原来如此。用人命和国帑,换来的官路亨通。这桩陈年旧案,
卷宗早已被销毁,知情人也死的死,散的散。但它却清清楚楚地,刻在我的脑子里。刘姨娘,
你最大的依仗,是你兵部尚书的父亲。那么,我就先毁了你的依仗。不。直接毁掉,
太便宜你们了。我要的,是诛心。第二日,我去给刘姨娘请安。这是青黛死后,
我第一次踏出自己的院子。刘姨娘正坐在上首,享受着众人的奉承,见我进来,
她连眼皮都未曾抬一下,只轻飘飘地说:“我当是谁,原来是病秧子妹妹。怎么,
你那短命的丫头死了,你倒有精神出来了?”周围传来一阵压抑的窃笑。
我没有理会她的挑衅,只是规规矩矩地行了礼,然后安静地坐到最末的位置上,垂着头,
仿佛一只受惊的鹌鹑。刘姨娘见我这副模样,愈发得意,她故意拿起手边的一只茶盏,
那茶盏是官窑新出的雨过天青色,极为珍贵。“说起来,”她摩挲着茶盏,意有所指,
“这人啊,就跟物件儿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官窑出来的,自然是金贵。
那些个民窑里出来的粗胚,就算洗得再干净,也上不得台面,只配在烂泥里待着。
”我依旧低着头,仿佛没听懂她的话。直到她身边的婆子端来一盘新切的蜜瓜,
我才缓缓抬起头,看着那翠绿的瓜皮,轻声开口。我的声音很小,
却足以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这蜜瓜,瞧着倒像是从淮南运来的。
我记得爹爹……我记得以前在家时,曾听人说起,淮南的瓜最是清甜,只是路途遥远,
运到京中,损耗极大,一斤瓜,价抵一斤盐呢。”场面瞬间安静了下来。刘姨娘的脸色,
微微变了。我像是毫无察觉,继续自言自语般地说道:“说起盐,我又想起一桩趣闻。
听说二十年前,淮南有个姓程的盐商,富可敌国,他家的宅子,比王爷府还气派。只是可惜,
后来不知怎的,一场大火,把程家烧了个干干净净,连片瓦都没剩下。”“住口!
”刘姨娘猛地将茶盏拍在桌上,茶水四溅,“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些什么!”我惶恐地抬起头,
一双眼睛蓄满了泪水,像是被吓到了:“姨娘息怒,我……我只是想起些旧闻,随口一说,
并无他意。”“什么旧闻!”刘姨...娘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尖锐的颤抖,
“我看你就是故意在此妖言惑众!”我怯生生地站起身,走到她面前,福了一福,
声音里带着哭腔:“姨娘恕罪。或许是我记错了。我只记得,那场大火后,
有人说在河里捞起了一具无名男尸,身上穿着巡盐御史的官服……想来,也是个可怜人。
”巡盐御史。这四个字,像一道惊雷,劈在了刘姨娘的头顶。她的脸,瞬间血色尽失。
她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不再是鄙夷和骄横,而是彻骨的恐惧。她不明白,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这些连她父亲都讳莫如深,早已烂在肚子里的陈年秘辛。
我看着她惊恐的脸,心中没有一丝波澜。我只是微微俯身,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
在她耳边轻语:“姨娘,你说,若是主君知道了这些事,尚书大人头上的这顶乌纱帽,
还戴得稳吗?”刘姨娘浑身一颤,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瘫倒在椅子上。我直起身,
退后两步,重新恢复了那副怯懦温顺的模样,对着她盈盈一拜。“姨娘若是不舒服,
便早些歇息吧。妹妹,就不打扰了。”说完,我转身,一步一步,
从容地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院子。阳光落在我身上,很暖。我知道,从今天起,
刘姨娘这只纸老虎,已经被我彻底废了。她不敢再找我的麻烦,
甚至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讨好我,堵住我的嘴。但这只是开始。一个兵部尚书的把柄,
还不足以撼动萧珏。我的目光,要放得更长远。我要的,是这满朝文武,是这整个大周朝廷,
所有藏在锦绣袍服下的污秽与不堪。我要将这些,一一握在手里。然后,织成一张天罗地网,
将萧珏,我那位高高在上的主君,死死地困在中央。我回到自己的小院,走到那棵海棠树下。
“青黛,”我轻轻抚摸着微凉的土地,“看见了吗?”“游戏,才刚刚开始。”风吹过,
海棠树的叶子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我。我抬起头,看向主院的方向,嘴角,
勾起了一抹冰冷的笑意。萧珏,你把我当成金笼里的雀儿。却不知,这雀儿,会用歌声,
为你唱一曲最华丽的葬歌。第二部分刘姨娘果然老实了。她不仅不敢再找我的麻烦,
还隔三差五地遣人送来些时新的料子和精致的点心,姿态放得极低。府里的人都摸不着头脑,
只当我得了主君的什么恩宠,连带着刘姨娘这等骄横的人也不得不避其锋芒。我照单全收,
却从不给她好脸色。恐惧是最好的缰绳。我要让她时时刻刻都活在被我揭穿的恐惧里,
让她知道,她的荣华富贵,她全家的性命,都只在我的一念之间。
萧珏似乎也察觉到了府里的风向变化。那晚,他又来了我的院子。
依旧是那副冷若冰霜的模样,坐在窗边,看我煮茶。月光透过窗棂,
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让他那张完美得不似真人的脸,更添了几分疏离。“你最近,
似乎过得不错。”他开口,声音平淡无波。我端着茶盏的手,稳稳当当,没有一丝颤抖。
“托主君的福。”我垂眸答道。“刘氏没再为难你?”“刘姨娘待妹妹很好。
”他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一丝不易察rayed的嘲弄。“是么。我倒听说,
她前日还将自己最心爱的那对南海珍珠耳坠送了你,只为赔你那丫头的不是。
”我的心猛地一沉。他在试探我。他府里的事,没有什么能瞒过他的眼睛。刘姨娘的反常,
他定然早已看在眼里。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知道刘家的秘密。那会暴露我的能力,
暴露我的威胁。一只会唱歌的雀儿是玩物,而一只会啄人的鹰,只会被毫不犹豫地拧断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