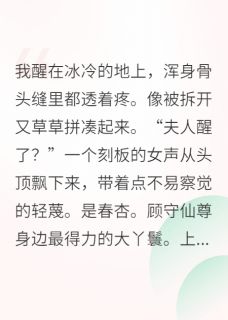
我醒在冰冷的地上,浑身骨头缝里都透着疼。像被拆开又草草拼凑起来。“夫人醒了?
”一个刻板的女声从头顶飘下来,带着点不易察觉的轻蔑。是春杏。
顾守仙尊身边最得力的大丫鬟。上辈子,就是她端着这碗黑漆漆、散发着苦腥气的“补药”,
一勺一勺,灌进我喉咙里,美其名曰仙尊怜惜我体弱。怜惜个屁。
那药是白柔那个**亲手调制的慢性毒,一点点腐蚀我的根基,掏空我的寿元。直到最后,
我形销骨立,咳血而亡,顾守也只是皱着眉站在几步开外,嫌恶地说:“夫人,你太吵了。
”“夫人?”春杏见我直勾勾盯着她手里的药碗,没反应,语气又硬了几分,“该用药了。
仙尊特意吩咐,务必看着您喝完。”特意吩咐?是啊,他特意吩咐毒死他明媒正娶的发妻,
好给他的白月光腾位置。脑子里像炸开了一锅滚油。
前世的画面疯狂涌入:初见顾守时他清冷如谪仙的侧脸,
我傻乎乎捧上的一颗真心;白柔楚楚可怜依偎在他身边,
他眼底的温柔几乎要溢出来;我呕心沥血为他打理偌大仙府,
换来的只有他越来越冷的背影和一句句“夫人,你逾矩了”;最后那几年,缠绵病榻,
咳出的血染红了半张帕子,连个像样的大夫都请不来,因为白柔说“凡俗药石对姐姐无用,
反添浊气”……爱?早在前世断气那一刻就烧成了灰。恨?有,但不多。不值得。重活一次,
我只想为自己活。“放着吧。”我撑着想坐起来,骨头咔吧作响,疼得我抽了口冷气。
这身体,比上辈子死前好不了多少。春杏没动,碗稳稳端在手里:“仙尊吩咐,
需婢子亲眼看着您服下。”又是仙尊吩咐。我抬眼,目光第一次认真落在春杏脸上。圆脸,
细眼,嘴角习惯性向下撇着,一副公事公办的冷漠。她是顾守的心腹,也是白柔的走狗。
前世我死时,隐约听见她在门外跟人低语,语气是压不住的兴奋:“……总算熬到头了,
柔姑娘的好日子近了……”好日子?用我的命铺就的好日子?一股戾气猛地从心底窜起。
我看着她,忽然扯开嘴角,笑了。春杏被我笑得一愣。“这药,”我声音嘶哑,像砂纸磨过,
“闻着就一股子阴沟里的味儿。”春杏脸色变了变:“夫人慎言!
这是柔姑娘费心为您……”“啪!”我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挥臂!
动作快得连我自己都意外。那只粗糙的陶碗飞了出去,狠狠砸在光可鉴人的青玉石地板上,
摔得粉碎。浓黑的药汁溅开,像泼了一地污血。空气死寂。春杏僵在原地,眼珠子瞪得溜圆,
像是第一次认识我。她大概从没见过温顺得像绵羊一样的“夫人”,
敢打翻仙尊“特意吩咐”的药。“你……”她指着地上的狼藉,指尖发抖,
“你敢……”“我怎么了?”我扶着冰冷的墙壁,一点点把自己撑起来,站直。
身体虚得厉害,摇摇欲坠,但背脊挺得笔直。“药太烫,没端稳。不行吗?”我盯着她,
眼神里没有往日的怯懦和讨好,只有一片冰封的湖,底下是看不见的暗流。“还是说,
你觉得我该像个死人一样躺着,任你灌?”“反了!反了天了!
”春杏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尖利刺耳,“夫人,您这是对仙尊不敬!我这就去禀报仙尊!
”“去。”我下巴微抬,指向门口,“现在就去。告诉他,他的‘补药’,我林醒,
消受不起。”春杏被我眼中那股陌生的狠劲儿慑住,一时竟忘了动作,只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还不滚?”我声音不大,却像淬了冰渣。她猛地一跺脚,恨恨剜了我一眼,转身冲了出去,
裙摆带起一阵风。房间里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药味和我粗重的喘息。腿一软,
我跌坐回冰冷的床沿。看着地上那滩污迹,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鼓。爽,**的爽!
憋屈了一辈子,第一次反抗,哪怕只是打翻一碗毒药,也痛快得像三伏天灌下一桶冰水。
可痛快过后,是更深更冷的寒意。顾守。那个我前世奉若神明、爱得卑微如尘的男人。
他现在在哪儿?大概在白柔的温柔乡里吧。听到他那个“温顺贤淑”的夫人突然发了疯,
打翻了他“精心准备”的药,他会是什么反应?愤怒?惊讶?还是……根本不屑一顾?
我闭上眼,强迫自己冷静。前世临死的剧痛和绝望是最好的清醒剂。哭?闹?上吊?
求他回心转意?省省吧。狗男人心里没你,你哭瞎了眼他也只觉得你吵闹。我林醒,
上辈子蠢够了。重活一次,我只做三件事:保命,搞钱,然后——休夫!念头一起,
一股前所未有的畅**冲刷着四肢百骸。休夫!休了那个眼盲心瞎的狗屁仙尊!光是想想,
就爽得头皮发麻。但我知道,这很难。修仙界实力为尊,顾守是高高在上的北境仙尊,
修为深不可测。我呢?一个靠着祖上一点微末恩情、侥幸攀上高枝的凡女,
空有“仙尊夫人”的虚名,在府里活得还不如春杏有体面。休他?无异于蚍蜉撼树。
可蚍蜉也有蚍蜉的路。我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思绪。当务之急,
是这具破败的身体和四面楚歌的处境。毒,不能再碰。人,一个都不能信。
我环顾这间华丽却冰冷得像坟墓的寝殿。这是仙尊夫人的居所,却处处透着疏离和禁锢。
连空气里都飘着白柔喜欢的“凝神香”,闻久了让人昏昏沉沉。不能待在这里。念头刚起,
门外就传来了脚步声。沉稳,有力,每一步都带着无形的威压,踩在人心尖上。来了。
门被一股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推开。他站在门口,一身纤尘不染的月白锦袍,
身姿挺拔如孤峰寒松。那张脸,依旧俊美得挑不出一丝瑕疵,眉目深邃,鼻梁高挺,
薄唇抿成一条冷淡的直线。阳光落在他身上,仿佛为他镀了一层神性的光晕。北境仙尊,
顾守。曾几何时,这身影是我全部的仰望和欢喜。如今再看,
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他目光扫过地上碎裂的陶片和污渍,
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随即落在我身上。那眼神,
像是在审视一件出了瑕疵、碍了他眼的摆设。“醒了?”声音清冷,听不出喜怒。
我扶着床柱,没行礼,也没像从前那样立刻垂下眼,而是直直地回视他。“嗯,醒了。
”嗓子还是哑的,但很平静,“托仙尊的福,没死透。”顾守的眉头蹙得更深。
他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在他印象里,他的夫人永远是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
哪怕受了委屈,也只是红着眼眶默默承受,从不敢顶撞半个字。“药怎么回事?”他问,
语气平淡,仿佛在问今天天气如何。“太苦,不想喝。”我言简意赅。“胡闹。
”他吐出两个字,带着上位者惯有的不容置疑,“那是柔儿费心为你调制的固本培元之物,
于你身体有益。任性妄为,成何体统?”柔儿。叫得真亲热。固本培元?有益?
我差点笑出声。这睁眼说瞎话的本事,不愧是仙尊。“哦?”我挑眉,故意拖长了调子,
“原来仙尊也知道我身体不好啊?我还以为您贵人事忙,
早忘了这清寂殿里还躺着个喘气的夫人呢。”顾守眼神陡然一厉,
一股无形的威压瞬间笼罩下来,空气都凝滞了几分。寻常人在这威压下早就跪伏在地,
瑟瑟发抖。我咬紧牙关,指甲狠狠掐进掌心,用疼痛抵抗着那股几乎要碾碎骨头的压力。
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冷汗瞬间浸透了里衣,但我梗着脖子,没退半步,更没低头。
“林醒,”他声音沉了下来,带着警告,“注意你的身份。”“身份?
”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胸腔震动,牵得五脏六腑都疼,“仙尊夫人?
呵……一个连一碗不想喝的药都做不了主、随时可能‘病逝’的夫人?
”我盯着他那双深不见底、永远装着天下苍生唯独装不下我的眼睛,一字一句,
清晰无比:“顾守,这夫人,我当够了。”话音落下的瞬间,空气死寂。
顾守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眸里,终于清晰地掠过一丝错愕,随即是更深的冰寒。
他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眼前这个顶着“夫人”名号的女人。春杏在他身后,吓得脸都白了,
大气不敢出。“你再说一遍。”顾守的声音不高,却像冰锥子,能扎透人的骨头缝。
威压更重了,我喉头一甜,腥气上涌。但我硬生生咽了回去,
扯出一个近乎挑衅的笑:“我说,这、夫、人,我、不、想、当、了!”最后一个字落下,
我清晰地看到他负在身后的手,指节捏得泛白。“放肆!”春杏终于忍不住尖声呵斥,
“夫人,您疯了!竟敢如此对仙尊说话!还不跪下请罪!”我连眼风都没扫她一下,
只盯着顾守。“疯?”我嗤笑,“或许吧。被关在这金丝笼里,日复一日喝着毒药,
等着被掏空最后一滴价值再无声无息地死去……不疯才怪!”“毒药?
”顾守捕捉到了这个词,眼神锐利如刀,“你胡言乱语什么?”“是不是胡言乱语,
仙尊心里没数吗?”我毫不退缩地迎上他的目光,“还是说,
白柔姑娘亲手为我‘固本培元’的‘良药’,仙尊您,也亲自尝过?”提到白柔,
顾守眼中闪过一丝愠怒:“住口!柔儿心地纯善,岂容你污蔑!”“心地纯善?
”我像是听到了世上最好笑的笑话,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是啊,纯善得巴不得我早点死,
好给她腾位置!顾守,你眼瞎心盲,把一条毒蛇当宝贝捧着,还要拉着我一起给她陪葬!
我告诉你,没门!”“够了!”顾守厉喝一声,袍袖无风自动。一股巨力猛地撞在我胸口!
“噗——”我再也忍不住,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向后倒去,
重重撞在冰冷的床柱上。剧痛瞬间席卷全身,眼前阵阵发黑。“夫人!
”春杏假惺惺地惊呼一声,实则眼底藏着快意。顾守站在原地,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狼狈地蜷缩在地,嘴角染血,眼神冰冷得不带一丝温度:“冥顽不灵,
恶语中伤。看来是本尊平日太过纵容,才让你如此不知天高地厚。”他顿了顿,
声音里淬着寒冰:“即日起,禁足清寂殿。没有本尊允许,任何人不得探视。药,照常送来,
必须喝。什么时候知错,什么时候再谈其他。”说完,他再不看地上如同烂泥的我一眼,
转身,月白色的衣袂划过一道冷漠的弧线,消失在门口。沉重的殿门轰然关闭,
隔绝了最后一丝光线,也彻底隔绝了我与外界的联系。
“咳…咳咳……”我蜷缩在冰冷的地上,每一次咳嗽都牵扯着碎裂般的疼痛。
喉咙里的腥甜不断上涌。禁足。断药是不可能的,毒药只会来得更勤。
顾守的态度再清楚不过。他不在乎我的生死,只在乎我是否“安分”,
是否碍着他和白柔的路。在他眼里,我大概连他养的一只灵宠都不如。
前世被这种冷漠伤透了心,如今只觉得讽刺。指望他?不如指望明天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挣扎着,用尽最后一点力气,一点点挪到墙角。冰冷的墙壁贴着滚烫的额头,
带来一丝微弱的清醒。不能坐以待毙。毒药必须想办法处理掉。这破身体也得尽快调养。
可我现在一穷二白,灵力微末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还被严密监视。唯一能依靠的,
只有脑子里那点可怜的前世记忆。前世快死的时候,为了活命,
我翻遍了清寂殿犄角旮旯里堆放的、无人问津的陈旧书简,
大多是些修仙界瞧不上的凡俗医书和杂记。当时只当是临死前的慰藉,
囫囵吞枣地记下不少偏方和药理知识。没想到,竟成了如今唯一的生机。
我记得……在殿后那个废弃的小花园角落,似乎长着一种不起眼的野草,叫“苦地丁”。
那东西在修仙界屁用没有,味道还苦得要命,连最低阶的灵兽都不屑啃。
但在一本破旧的《百草拾遗》里提过一句,此物性极阴寒,能中和烈性热毒。白柔的毒,
走的阴损路子,表面温和,实则内里炽毒攻心。苦地丁的寒性,
或许能起到一点以毒攻毒的缓解作用!至少能暂时压制毒性,给我争取时间!
这个念头像黑暗中划过的火星。我艰难地爬到窗边。窗户很高,被封死了大半,
只留下窄窄的一条缝隙透气。透过缝隙,能看到外面灰蒙蒙的天和被阵法笼罩的庭院一角。
那个荒废的小花园,就在视线尽头的角落。可怎么出去?门口肯定有守卫。就算溜出去,
怎么避开无处不在的阵法监视?正焦灼间,殿门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开了一条缝。
一个瘦小的身影端着托盘,像只受惊的兔子,飞快地溜了进来,又迅速关上门。是扫尘。
清寂殿里负责洒扫庭院的最低等小侍女,才十三四岁的样子,平时沉默寡言,总低着头,
像个影子。前世我对她没什么印象,只隐约记得她好像经常被春杏和其他大丫鬟欺负。
她端着托盘的手在抖,上面放着一碗新熬好的药,热气腾腾,
散发着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令人作呕的苦腥气。“夫……夫人,”扫尘声音细若蚊蚋,
带着哭腔,“药……药熬好了,春杏姐姐让……让奴婢看着您喝……喝完……”她低着头,
不敢看我,身体抖得像筛糠。春杏自己不敢来触霉头,就派这么个胆小如鼠的小丫头来。
我看着她单薄的身体和惊恐的眼睛,心里忽然一动。“扫尘,”我尽量放柔声音,
尽管喉咙疼得像刀割,“你过来。”她迟疑了一下,小步挪过来,始终低着头。“抬起头,
看着我。”她身体一僵,慢慢抬起脸。小脸蜡黄,没什么血色,一双眼睛倒是干净,
此刻盛满了恐惧和茫然。“怕我吗?”我问。她飞快地摇头,又猛地点头,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别怕。”我扯出一个虚弱的笑,指了指地上还没清理的药渍和碎片,
“刚才那碗,我不小心打翻了,惹仙尊生气,被禁足了。
这碗……”我看着托盘里那碗新的毒药,“你能帮我个忙吗?”扫尘茫然地看着我。“这药,
我不想喝。”我直截了当地说,“喝了会死。”她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下意识地后退半步。
“但我不喝,春杏会打死你,对吗?”我平静地陈述事实。扫尘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无声地点点头。她显然也知道这药有问题,但不敢反抗。“帮我倒掉它。”我看着她的眼睛,
“找个地方,倒得干干净净,别让任何人发现。碗,你就说……就说我喝了,不小心又摔了。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摔碗了。”扫尘愣住了,呆呆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倒掉仙尊吩咐、柔姑娘亲手调制的药?这在她小小的认知里,是天大的罪过。
“不……不敢……春杏姐姐会……”“她不会知道。”我打断她,
声音带着一种奇异的蛊惑力,“只要你做得干净。想想,她让你看着我喝完,
可我现在‘病重’,摔个碗不是很正常吗?她顶多骂你几句笨手笨脚,
不会真的为了一个破碗打死你。但如果你逼我喝这药……”我故意停顿,
看着她骤然惨白的脸,“我若真死了,你觉得,仙尊会为了一个死了的夫人,
去查他心爱的柔姑娘的药方吗?到时候,背锅的会是谁?”扫尘浑身剧震,小脸血色褪尽。
她年纪小,但不傻。在这个吃人的仙府里,底层奴婢的命贱如草芥。一个失宠夫人的死,
总得有个“伺候不周”的替罪羊。恐惧压倒了服从。“我……我……”她嘴唇哆嗦着,
看着那碗药,又看看我。“倒掉它。”我再次重复,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然后,
帮我做另一件事。做成了,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最后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