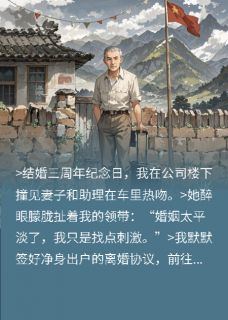
日子在山风呼啸和孩子们的读书声中,以一种近乎原始的节奏向前流淌。陈默渐渐习惯了清晨被冻醒,习惯了用冰凉的井水洗漱,习惯了那寡淡得几乎没有油星的饭菜,习惯了粉笔灰沾满手指的感觉。他和林溪的交流也仅限于教学和必须的校务,平淡得像这山间的溪水,清浅,无声。他沉默地教课,沉默地批改那些歪歪扭扭的作业,沉默地修补教室里漏风的窗户。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望着窗外连绵的、沉默的山峦发呆。那些山峦如同巨大的、无法逾越的屏障,将他与那个充斥着背叛和谎言的世界彻底隔绝开来。
这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推开自己那间小屋的门,准备去教室。脚步却在门槛处顿住了。
门楣上,窗棂的缝隙里,甚至那扇破旧门板的把手上,都被小心翼翼地、歪歪扭扭地插满了野花。那些花毫不起眼,大多是路边田埂上常见的品种:淡紫色的小蓟花顽强地伸展着带刺的茎叶;嫩黄的蒲公英毛茸茸地挤在一起;还有星星点点的蓝色小野菊,白色的不知名碎米花……它们被采摘下来显然有一会儿了,花瓣边缘有些蔫蔫的,沾着清晨的露水,在微凉的晨风中轻轻颤动。没有任何章法,也谈不上美感,就那么野蛮地、生机勃勃地占领了他这扇破败的门扉,像是山野本身对他笨拙而热烈的问候。
陈默怔怔地看着,指尖无意识地触碰到一朵蒲公英柔软的花球,绒毛瞬间四散飞开,像小小的降落伞飘向空中。一丝极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涟漪,在他沉寂如死水的心湖里轻轻漾开。
“噗嗤…”
一声没憋住的笑声自身后传来。
陈默回头。林溪正站在她自己的小屋门口,肩上挎着那个熟悉的帆布包,手里还捏着半个没吃完的烤红薯。她看着陈默那扇被野花“攻陷”的门,还有他难得一见的、有些无措的表情,眼睛弯成了月牙儿,清澈的笑意几乎要溢出来。
“陈老师,”她咬了一口红薯,声音含混不清,带着毫不掩饰的打趣,“你这造型…挺别致啊!”她伸手指了指他门上的“装饰”,“像个…像个移动的大花篮!还是野趣十足的那种!”
陈默下意识地抬手想拂掉那些花,动作却在半途停住了。他看着林溪笑得亮晶晶的眼睛,那里面没有丝毫恶意,只有纯粹的、山泉般的明快。他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有些生硬地转回身,避开那过于明亮的视线,低头走进了自己的小屋。身后,林溪清脆的笑声又响了一下,随即被关门的声音隔断。
他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边,目光却忍不住再次投向门口。几缕阳光透过门板的缝隙照进来,恰好落在一簇淡紫色的小蓟花上,那带刺的枝叶在光线下显得格外清晰。他伸出手,这次没有碰掉它们,而是极其小心地,把一朵快要掉落的蓝色小野菊,重新往窗棂的缝隙里塞了塞。
日子在粉笔灰和山风里继续翻页。野花成了陈默小屋门楣上的常客,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簇新的,颜色各异,无声地更换着。他渐渐能分辨出哪些是那个总爱流鼻涕的小男孩虎子放的(大多是粗壮带刺的),哪些是那个扎羊角辫、眼神怯生生的小女孩阿秀插的(总是小而精致的花)。他没有再试图清理它们,只是每次进出时,目光总会在那片小小的、生机勃勃的色彩上停留片刻。
山里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傍晚时分,原本只是阴沉的天空骤然泼墨般暗沉下来。狂风毫无预兆地卷起,疯狂地撕扯着屋顶的茅草和糊窗户的旧报纸,发出呜呜的尖啸,如同山魈的厉嚎。紧接着,豆大的雨点裹挟着冰雹,噼里啪啦地砸在屋顶和地上,瞬间汇成一片狂暴喧嚣的白噪音。远处传来沉闷的、令人心悸的轰隆声,像是山体在痛苦地**。
陈默正在他那间简陋的小屋里整理明天上课要用的图画纸。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了墨黑的天空,瞬间照亮了屋内家徒四壁的景象,随即是震耳欲聋的炸雷,仿佛就在屋顶炸开,震得整个土坯小屋都在簌簌发抖。狂风卷着冰冷的雨丝,从窗棂的破洞和门板的缝隙里猛灌进来,桌上的纸张被吹得哗哗作响,煤油灯的火苗疯狂摇曳,几乎熄灭。
他心头猛地一沉。老支书昨天就念叨过,后山那条通往外界的唯一泥路,靠近陡崖的一段本来就松垮得厉害。这么大的雨…他冲到门边,费力地拉开一道缝隙。外面已是混沌一片,密集的雨点砸在泥地上溅起浑浊的水花,狂风几乎让人站立不稳。雨幕深处,只有一片令人绝望的漆黑和震耳欲聋的轰鸣。山路,肯定断了。一种冰冷的、与世隔绝的孤绝感,伴随着这狂暴的风雨,瞬间攫住了他。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被风雨声几乎淹没的拍门声响起!
“陈老师!陈老师!开门!”
声音穿透风雨的咆哮,带着急切和喘息。
陈默一愣,猛地拉开门。一股冰冷的狂风裹挟着雨水瞬间扑了他满脸。门外,一个浑身湿透的身影几乎站立不稳。是林溪!
她没打伞,也没穿雨衣。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瘦削的轮廓,雨水顺着她湿透的发梢、脸颊、下巴,成股地往下淌。她背上斜挎着那个熟悉的、半旧的帆布包,此刻也吸饱了水,沉甸甸地坠着。裤腿和那双沾满泥浆的胶鞋,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她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四四方方、用塑料布层层包裹的盒子,塑料布边缘还在不断往下滴水。
“林老师?你…”陈默愕然,侧身让她进来,“快进来!这么大的雨!”
林溪踉跄着冲进小屋,带进一股浓重的土腥味和水汽。她顾不上自己,第一件事就是把怀里那个塑料布包裹的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在那张歪腿的木桌上,仿佛那是什么稀世珍宝。
“听说…”她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湿漉漉的头发黏在光洁的额头上,气息因为刚才的奔跑和攀爬而急促不稳,声音却在风雨的喧嚣里异常清晰,“听说有人今天过寿?”她抬起头,眼睛亮得惊人,即使在昏暗摇曳的煤油灯光下,也像落入了两簇跳动的星火。她指了指桌上那个塑料布包裹的盒子,脸上绽开一个混合着狼狈和温暖的笑容,“喏,老支书家婆娘蒸的,白面馍馍!抢出来的!”
陈默这才猛地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
这个早已被他自己刻意遗忘、连同过去一起埋葬的日子。
他怔在原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了。桌上那个滴着水的塑料布包裹,林溪浑身湿透、沾满泥泞的狼狈样子,还有她那亮得灼人的、映着微弱烛光的眼睛…这一切,像一把滚烫的烙铁,猝不及防地烙印在他冰封已久的心口上。
林溪却不管他的怔忡,她已经放下帆布包,动作麻利地解开那层湿透的塑料布,露出里面一个同样沾着水汽、但保存完好的白瓷盘,盘子里躺着三个白白胖胖的馒头。她又从那个湿漉漉的帆布包里摸索着,竟然掏出了几根小小的、细细的红蜡烛!蜡烛也沾了水,但她毫不在意,拿起桌上那半截快用完的粉笔头,在桌面蹭了蹭,蹭出些白粉,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蜡烛底部蘸上白粉,一根根稳稳地立在白面馍馍旁边。
她划亮一根火柴。微弱的火苗在狂风中挣扎着,几次险些熄灭。她用手拢着,护着那点颤巍巍的光,凑近蜡烛芯。橘黄色的烛光终于亮了起来,一点,两点…微弱,却顽强地驱散着陋室里的黑暗和寒意,跳跃着映在林溪专注而认真的侧脸上,也映在她湿漉漉的、睫毛上还挂着水珠的眼睛里。
就在这时,陈默放在木桌角落、一直处于信号微弱状态的旧手机,屏幕突然毫无征兆地亮了起来,伴随着一阵沉闷的、断断续续的嗡嗡震动。屏幕顶端,一条来自律师的新信息提示,顽强地穿透了这深山雨夜的隔绝,跳了出来。
陈默的视线下意识地被那微光吸引过去。他拿起手机,屏幕的光映亮了他骤然变得晦暗不明的脸。手指划开信息。
【陈先生,急事。苏晴女士动用所有关系疯狂寻找您下落,情绪异常激动。另:据查,其助理张扬已于三日前卷走公司及她个人账户大笔流动资金,去向不明。情况复杂,请务必尽快与我联系!】
冰冷的文字,像窗外砸落的冰雹,瞬间将他从眼前这点微弱的烛光温暖中狠狠拽回现实。那个被群山暂时阻隔的名字,那个他以为早已埋葬的过往,带着背叛的余烬和新的、更不堪的疮疤,以如此突兀的方式,再次蛮横地闯入这方狭小的空间。
屋子里很静,只有煤油灯灯芯燃烧的细微噼啪声,和窗外风雨的咆哮。烛光在林溪脸上跳跃,她正低头专注地调整着蜡烛的位置,试图让那点微弱的火焰燃烧得更稳些。她似乎察觉到了陈默的异样沉默,抬起头,目光掠过他握着手机、指节微微发白的手,又落回他脸上。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映着烛火,也清晰地映出了他此刻难以掩饰的僵硬和阴郁。
她唇边那抹温暖的笑意慢慢淡了下去,但没有追问,只是拿起一块干净的旧布,开始擦拭自己手臂上被荆棘划出的一道新鲜血痕。血痕在雨水浸泡下边缘有些发白。她的动作很轻,声音也放得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你前妻…”她顿了顿,似乎斟酌了一下用词,目光没有离开那道浅浅的伤口,语气平淡得如同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小事,“…好像找你有急事?”她拿起桌上备着的简易小药箱,打开,取出一根沾了碘伏的棉签,低头仔细地处理自己手臂上的伤口。碘伏的黄色在皮肤上洇开,带着消毒水的微涩气味。
“嗯。”陈默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个模糊的音节,像被砂纸磨过。他猛地按灭了手机屏幕,那点幽蓝的光消失了,小屋重新被摇曳的烛光和油灯昏黄的光晕笼罩。他把手机塞进裤兜,动作带着一种刻意的粗暴。律师冰冷的文字还在脑海里盘旋——苏晴的疯狂寻找,张扬的卷款潜逃…像两条冰冷的毒蛇缠绕上来,让刚刚被烛光烘暖的空气瞬间再次冻结。他闭了闭眼,试图将那些混乱不堪的画面驱逐出去,再睁开时,目光落在林溪正低头处理的手臂伤口上。那伤口不深,但被雨水和泥泞弄得有些狰狞。
“你受伤了?”他开口,声音依旧沙哑,却带上了一丝自己都未察觉的紧绷。
“没事,路上被刺条划了下,小意思。”林溪头也没抬,语气轻松,仿佛在谈论天气。她熟练地用棉签蘸着碘伏,小心地擦拭着伤口边缘的泥污。橘黄的烛光在她低垂的眼睫上投下小片颤动的阴影。她处理完自己的伤口,放下碘伏瓶子,又拿起一根新的棉签,目光转向陈默。“你腿呢?”她抬了抬下巴,示意他的裤腿,“刚进门我看你走路有点瘸,刮着了?”
陈默这才感觉到左小腿外侧传来一阵迟来的、**辣的刺痛。大概是刚才在泥泞里跋涉时不慎刮到了什么。他低头看去,深色的裤腿上果然被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边缘沾着泥浆,布料被洇湿了一片深色。
“不碍事。”他下意识地想退开一步。
“坐下。”林溪的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干脆,指了指那张吱呀作响的木床。她拿着棉签和一小瓶碘伏已经走了过来,动作自然而利落,仿佛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陈默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依言在床沿坐下。小屋空间逼仄,两人距离骤然拉近。他能清晰地闻到林溪身上混合着雨水、泥土、草木清苦味和淡淡碘伏的气息。林溪蹲下身,动作很轻地卷起他那条湿透的裤腿。烛光下,小腿外侧一道十几厘米长的刮伤暴露出来,不算深,但表皮翻卷,边缘红肿,渗着血丝和泥水。
“啧,口子还不小。”林溪皱了皱眉,声音低了些。她先是用干净的布蘸着温水(还是刚才陈默自己烧的那点热水),小心地擦去伤口周围的泥污。她的手指带着山泉般的凉意,动作却异常轻柔稳定。湿布擦过翻卷的皮肉边缘,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陈默的腿不自觉地绷紧了一下。
“忍着点。”林溪的声音很轻,像在安抚。她拿起那根新的棉签,重新蘸饱了棕黄色的碘伏。就在她屏住呼吸,棉签尖端即将触碰到那处翻卷的伤口边缘时——
“嘎吱——!!!”
一声刺耳到令人牙酸的急刹车声,如同锋利的金属片狠狠刮过玻璃,骤然撕裂了小屋外风雨的咆哮!那声音如此突兀、如此尖锐,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疯狂,近得仿佛就紧贴着这间土坯房的墙壁!
紧接着,“砰!”一声巨响!那扇本就单薄破旧的木门,被人从外面用巨大的力量猛地撞开!门板狠狠拍在土坯墙上,震落下簌簌的尘土。
狂风裹挟着冰冷的雨水和浓重的湿泥气息,瞬间灌满了整个小屋。煤油灯的火苗疯狂乱窜,险些熄灭,烛光也猛烈摇曳,将屋内的影子拉扯得如同鬼魅乱舞。
门口,一个湿透的身影矗立在风雨交加的黑暗背景中。苏晴!
她浑身都在往下淌水,昂贵的羊绒大衣吸饱了泥水,沉甸甸地裹在身上,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和款式。精心打理的卷发湿漉漉地黏在惨白的脸上,妆容被雨水冲刷得一塌糊涂,眼线晕开,像两个乌青的黑洞。嘴唇冻得发紫,微微颤抖着。她一手死死扒着门框,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似乎在痉挛。那双曾经顾盼生辉、此刻却只剩下歇斯底里和绝望的眼睛,如同濒死的野兽,直勾勾地、死死地钉在坐在床沿的陈默身上,以及,他旁边那个蹲在地上、手里还拿着沾碘伏棉签的女人身上。
小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只有风雨的嘶吼声,煤油灯芯燃烧的噼啪声,以及苏晴粗重而混乱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噪音。
林溪的动作完全僵住了。她蹲在那里,保持着即将处理伤口的姿势,手里那根沾着碘伏的棉签,在剧烈摇曳的烛光下微微颤抖着。她的目光从陈默腿上的伤口,缓缓移向门口那个如同水鬼般突然出现的、浑身散发着疯狂气息的女人,脸上那点专注和温和瞬间褪得一干二净,只剩下全然的惊愕和茫然。
苏晴的目光像淬了毒的钩子,狠狠刮过林溪沾着泥点却清秀干净的脸,刮过她手中那根微不足道的棉签,最后死死锁在陈默的脸上。她的胸膛剧烈起伏,牙齿因为寒冷和极致的愤怒而咯咯作响,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冰窖深处挤出来的,带着彻骨的寒意和疯狂的指控:
“陈默!你躲在这种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她猛地抬手,指向蹲在地上的林溪,指甲在昏暗中划过一道尖锐的弧线,声音陡然拔高,尖利得几乎要刺破耳膜,“…就是为了报复我?!用这种…这种乡下女人来报复我?!你以为这样就能…”
她的控诉如同失控的洪水,汹涌而恶毒。然而,就在这恶毒的洪流即将冲垮一切堤坝时,她的声音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扼住,戛然而止!那双死死盯着陈默的眼睛里,疯狂、愤怒、绝望…种种激烈的情绪如同沸腾的岩浆翻滚着,但在那岩浆的最深处,却骤然掠过一丝极其诡异的、近乎自毁的扭曲快意,像黑暗中窥伺的毒蛇吐出了信子。
她死死地盯着陈默的眼睛,那眼神怨毒得如同实质的尖刀,嘴角却咧开一个极其古怪、近乎狰狞的笑容,仿佛要亲手撕开一个埋藏多年、足以将一切焚烧殆尽的秘密:
“…你以为这样就能抹掉过去了?就能当那个**没存在过了?!我告诉你!当年…当年你那个宝贝初恋为什么会在手术台上大出血?为什么孩子没保住?!不是意外!是我!是我故意让人在她术前吃的药里动了手脚!是我让她一尸两命!你听见没有!是我——!!!”
“啪嗒。”
一声极其轻微的声响,在苏晴歇斯底里的咆哮之后,在这死寂般凝固的空气里,却显得异常清晰。
林溪手中那根沾着棕黄色碘伏的棉签,掉落在了陈默脚边满是泥水的地面上。那点微弱的黄色,瞬间被浑浊的泥水吞噬,消失不见。
她依旧保持着蹲着的姿势,像是被瞬间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和魂魄。她的头低垂着,湿漉漉的碎发垂落下来,遮住了她大半张脸。只能看到她放在膝盖上的那只手,正在无法控制地、剧烈地颤抖着。那颤抖如同电流般迅速蔓延至她的全身,连带着她瘦削的肩膀都在无声地耸动。她蹲在那里,像一尊被骤然冻结的冰雕,又像一个被无形重锤瞬间击垮的、失去支撑的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