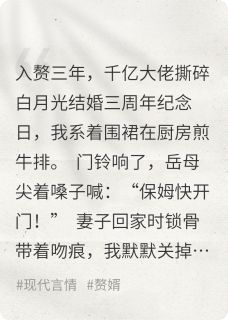
入赘三年,千亿大佬撕碎白月光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我系着围裙在厨房煎牛排。门铃响了,
岳母尖着嗓子喊:“保姆快开门!”妻子回家时锁骨带着吻痕,
我默默关掉炉火:“牛排焦了。”她当众甩我耳光:“废物连饭都做不好!
”家族会议逼我认下她腹中的私生子。满座哄笑中,我脱下围裙露出高定西装。
助理躬身递上文件:“陈总,千亿收购案等您签字。”对了。”我碾碎孕检单轻笑,
“孩子生父的破产流程——下周启动。”---厨房里,油烟机低沉地轰鸣,
像一头困兽在胸腔里焦躁地翻滚。平底锅里,两块上好的澳洲和牛在滚烫的黄油里滋滋作响,
边缘逐渐卷起诱人的焦褐色。陈默握着锅铲的手很稳,目光却有些空茫,
透过眼前氤氲的油烟,落在对面擦得锃亮的冰箱门上。那里映出一张模糊的脸,
胡子刮得干净,头发却有些凌乱,眼底沉淀着挥之不去的疲惫,像蒙了一层永远擦不掉的灰。
最扎眼的,是身上那件洗得发白、印着卡通小熊的旧围裙,滑稽又刺眼地裹着他。三年了。
今天是他和苏晚晴结婚三周年的日子。这个日子,在这个名为“家”的苏家别墅里,
似乎只有他还记得。空气里弥漫着煎肉的香气,带着一丝微妙的、即将烧焦的预兆。
门铃突兀地尖叫起来,划破了厨房里单调的油煎声。尖利,急促,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催促。
几乎同时,一个更加尖利、刻薄到骨子里的女声在玄关炸开,穿透厚重的门板,
直刺陈默的耳膜:“陈默!耳朵聋了?保姆还不快开门!想冻死我们吗?没用的东西,
一点眼力见都没有!”是岳母林美娟。她总是这样,仿佛他陈默的名字,
天生就该和“保姆”、“废物”这些词捆绑在一起。每一次呼唤,都是一次精准的羞辱。
锅里的牛排又发出一阵更响亮的“滋啦”声,几粒油星溅出来,烫在手背上,
留下一点微不足道的红痕。陈默面无表情地关小了火,指尖在围裙粗糙的布料上蹭了蹭,
那点灼痛很快就被更深沉的麻木覆盖。他转身走向玄关。拉开厚重的实木大门,
一股裹挟着深秋寒意的风猛地灌了进来,吹得他额前的碎发晃动。门外,
林美娟裹着件昂贵的皮草,保养得宜的脸上写满了不耐烦和鄙夷,那眼神,
像是看着一块挡路的脏抹布。岳父苏国栋则揣着手站在后面,挺着啤酒肚,
脸上是惯常的漠然,仿佛眼前的一切,包括陈默这个活生生的人,都与他无关。“磨蹭什么?
废物点心!”林美娟狠狠剜了他一眼,高跟鞋踩得大理石地面咔咔作响,
像钉子一样敲进陈默的骨头缝里,径直撞开他,走了进去。苏国栋紧随其后,
连一个多余的眼角余光都吝于给予。陈默沉默地合上门,将那冰冷的秋风隔绝在外。客厅里,
林美娟刻薄的数落声和苏国栋偶尔含混的应和声,立刻取代了厨房的油烟声,
成为新的背景噪音。他走回厨房,重新站在炉灶前,
锅里的牛排边缘已经带上了一圈难以忽视的黑焦。他拿起锅铲,轻轻翻动了一下。
肉块发出轻微的、令人不安的碎裂声。不知过了多久,外面传来汽车引擎熄火的声音,
接着是高跟鞋踩在台阶上清脆的笃笃声。是苏晚晴回来了。玄关处传来窸窸窣窣换鞋的声音。
陈默没有回头,只是专注地盯着锅里那块注定要失败的牛排。脚步声由远及近,
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甜腻得过分的香水味,越来越浓烈,取代了厨房里原本的油烟气息。
那香水味很陌生,不是苏晚晴惯用的清冷木质调。陈默终于关掉了炉火。
蓝色的火焰瞬间熄灭,只余下烧红的电热丝发出暗红的光。厨房里骤然安静下来,
客厅里林美娟和苏国栋的说笑声显得格外刺耳。他慢慢转过身。
苏晚晴就站在几步开外的厨房门口。她今天精心打扮过,一身剪裁利落的米白色羊绒套装,
衬得身段玲珑。长发微卷,慵懒地披在肩头。妆容精致,
眼角眉梢还残留着几分未曾褪尽的春意,双颊透着一种被滋润过的、娇艳的绯红。然而,
最刺眼的,是她左侧锁骨下方,靠近衣领边缘的地方。一小片暧昧的、深红色的印记,
如同雪地里突兀绽放的毒花,清晰地烙印在那里。那印记的形状和位置,
无声地宣告着它的来源。苏晚晴顺着陈默的目光,下意识地抬手,指尖飞快地拂过那处皮肤。
她脸上掠过一丝极快的不自然,但很快被一种混合着厌烦和理所当然的傲慢取代。
她微微扬着下巴,眼神居高临下地扫过陈默和他身上那件可笑的小熊围裙,
扫过锅子里那块卖相糟糕的牛排。“看什么看?”她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像是被过度使用过,语气却是冰凉的,“晚饭呢?就弄成这鬼样子?
”陈默的目光从她锁骨的红痕缓缓移开,落在她那双描画精致的眼睛上。三年婚姻,
一千多个日夜,他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她的冷漠,习惯了苏家加诸于身的轻贱。但此刻,
看着那块新鲜的、刺目的吻痕,看着这张熟悉又陌生的脸上毫不掩饰的厌弃,
心脏深处某个早已麻木的地方,还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闷闷地疼。他垂下眼,
声音很平,平得像一块沉入死水的石头:“牛排……焦了。”“焦了?
”苏晚晴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红唇勾起一个极其讽刺的弧度。她猛地向前一步,
高跟鞋在地板上敲出尖锐的声响,“陈默!你除了会说‘焦了’‘坏了’‘对不起’,
还会说点别的吗?连块肉都煎不好,你还能干什么?废物!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最后一个“废物”几乎是尖啸出来的。伴随着这声尖啸,“啪——!
”一记极其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毫无保留地掴在陈默的左脸上。力道之大,
打得他猝不及防地偏过头去。脸颊瞬间**辣地灼烧起来,耳朵里嗡嗡作响,
嘴里泛起一丝淡淡的铁锈味。围裙上那只憨态可掬的小熊图案,在剧烈的晃动中扭曲变形。
客厅里的说笑声戛然而止。林美娟和苏国栋出现在厨房门口,脸上没有丝毫惊讶,
只有一种看戏般的冷漠,甚至林美娟的嘴角,还噙着一丝快意的笑。空气凝固了。
只有脸上那**辣的痛感,和心脏深处那沉闷的钝痛,在无声地叫嚣。
苏晚晴甩了甩打疼的手,眼神如同淬了毒的冰凌,直直刺向陈默:“给我滚开!
看见你就恶心!”她撞开僵立着的陈默,气冲冲地走向客厅。
林美娟立刻堆起笑容迎上去:“哎哟我的乖女儿,回来啦?跟少峰玩得开心吧?
别为这种废物生气,气坏了身子妈心疼!快来坐下歇歇……”她扶着苏晚晴的胳膊,
目光意有所指地扫过苏晚晴的小腹。陈默站在原地,左脸麻木地胀痛着。他慢慢抬手,
用指腹蹭了蹭嘴角。指尖上,一点细微的猩红。他沉默地解下身上那件沾了油污的小熊围裙,
动作很慢,仿佛在卸下一件沉重的、沾满了屈辱的盔甲。围裙被随意地搭在冰冷的料理台上。
他弯腰,捡起刚才因那一巴掌而掉在地上的锅铲,把它放回原位。做完这一切,他才转过身,
走向客厅。步伐很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冰面上。苏家宽敞奢华的客厅里,
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
苏家几个说得上话的长辈——头发花白、眼神精明的二叔公,一脸刻薄相的姑妈苏丽萍,
还有苏晚晴的亲舅舅,都端坐在昂贵的真皮沙发上,个个面色沉肃,
眼神里却闪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审视和算计。焦点,自然是坐在主位单人沙发上的苏晚晴。
她微微昂着头,一只手习惯性地、带着一种刻意强调意味地轻轻搭在小腹的位置。
林美娟紧挨着她坐着,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和一种即将完成重大使命般的兴奋。
陈默像一个闯入者,沉默地走到沙发区域边缘,
在唯一空着的、最靠近角落的一张硬木矮凳上坐下。那凳子又小又硬,
与周围舒适宽大的沙发格格不入,
仿佛是他身份最直观的注脚——苏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永远只能坐冷板凳的赘婿。
没有人看他。他的存在,在此时此地,似乎只是为了充当一个背景板,
一个即将被宣布判决的囚徒。苏国栋清了清嗓子,作为名义上的家主,他率先打破了沉默,
声音刻意压得低沉,营造出一种严肃的氛围:“咳…今天把大家伙儿叫来,
是有一件…关系到我们苏家血脉、关系到家族未来兴衰的大事,要宣布,也要…做个决断。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最后落在角落里的陈默身上,
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意味:“晚晴她…怀上了。”客厅里瞬间响起几声刻意压低的惊呼,
随即是心领神会的沉默。二叔公捋了捋胡子,微微颔首。
姑妈苏丽萍的嘴角扯出一个刻薄的弧度。舅舅则端起茶杯,掩饰性地呷了一口,眼神闪烁。
“这是大喜事啊!”林美娟迫不及待地接口,声音拔高了几度,充满了炫耀,
“我们晚晴怀的,可是顾家少爷顾少峰的骨肉!顾家啊!在深城是什么地位,
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才是真正配得上我们晚晴、配得上我们苏家的血脉!
”她的话像一把把淬毒的匕首,精准地投向角落里的陈默。每一个字都在强调:顾家少爷,
尊贵的血脉。你陈默,低贱的尘埃。“不过嘛,”林美娟话锋一转,
脸上的得意换成了故作姿态的为难,“这孩子…眼下总归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得先上户口,对不对?不然传出去,对我们晚晴的名声,对顾家的脸面,都不好。
”她的目光终于转向陈默,眼神陡然变得锐利如刀,带着不容置疑的逼迫,“陈默,
你是晚晴法律上的丈夫。这孩子,你认下,就是你名正言顺的‘儿子’!以后,
苏家自然不会亏待你。你那个病秧子老娘,我们也会‘格外照顾’。”“格外照顾”四个字,
她说得意味深长,充满了**裸的威胁。苏国栋在一旁板着脸,沉声道:“这是家族的决定。
你入赘苏家三年,吃穿用度都是苏家的,也该为苏家做点贡献了。认下这个孩子,
以后安分守己,苏家还能有你一口饭吃。”“就是!”姑妈苏丽萍尖声附和,
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指几乎戳到陈默鼻尖,“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窝囊废,
白捡一个顾家的种,这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还不赶紧跪下磕头谢恩?装什么死人!
”“是啊是啊,”舅舅也放下茶杯,皮笑肉不笑地帮腔,“陈默,识时务者为俊杰。
能帮晚晴和顾家少爷解决这个麻烦,是你的荣幸。别不识抬举。”一句句,一声声,
如同冰雹,密集而冷酷地砸在陈默身上。他们逼迫他,一个男人,一个丈夫,
在众目睽睽之下,认下妻子腹中与别人通奸怀上的野种,还要感恩戴德。
理由冠冕堂皇——为了苏家的名声,为了攀附顾家。而他陈默的尊严,
他作为人最起码的感受,在他们眼中,连脚下的尘埃都不如。苏晚晴全程没有看他一眼。
她只是微微侧着头,欣赏着自己新做的美甲,脸上带着一丝事不关己的冷漠,
仿佛讨论的只是一个与她无关的物件。只有嘴角那一抹若有似无的弧度,
泄露着她此刻内心的快意——看吧,陈默,你这滩烂泥,永远只能匍匐在我脚下,
连我的污点,都要由你来背负。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陈默身上,
如同聚光灯下等待表演的小丑。空气紧绷得快要断裂,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恶意和期待。
就在这时,苏晚晴从她那只昂贵的爱马仕手包里,慢条斯理地抽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
她姿态优雅地将其展开,然后,带着一种施舍般的、高高在上的动作,随手一抛。
那张轻飘飘的纸,在空中打了个旋儿,像一片枯叶,最终落在了陈默脚边的地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