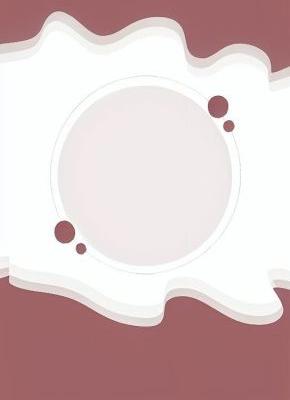
“公主,不好了!”
“国公爷……国公爷他,留书出走了!”
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镇国公府清晨的宁静。
昭阳公主李云裳正端着茶盏,闻声,那描金的茶盖在杯沿上磕出一声脆响。
她抬起眼,眸光清冷。
管家连滚爬爬地冲了进来,手里高举着一封信,脸色惨白如纸。
“公主!您快看!这是在国公爷书房发现的!”
信纸被呈上来。
没有署名。
但那字迹,李云裳认得,是她那个年过半百,沉迷美色的公爹,镇国公沈敬。
信上的内容不堪入目。
什么追求真爱,挣脱牢笼,什么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通篇都是对一个女人的爱慕与赞美。
那个女人,叫柳如烟。
是她丈夫沈修文的宠妾。
一个半月前,沈修文说要去江南巡查生意,便带上了柳如烟。
谁曾想,半路上,她的公爹,本该在皇庄休养的镇国公,竟也跟了过去。
当时只说是偶遇,父子同行,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
现在看来,全是预谋。
好一个父子同行。
好一个红尘作伴。
公爹带着儿子的妾私奔了。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李云裳捏着那封信,指节因为用力而泛起青白。
她能想象,明日一早,整个京城会如何议论镇国公府,又会如何议论她这个大周朝最尊贵的昭阳公主。
她的脸,皇家的脸,今天算是被这对不知廉耻的男女,扔在地上狠狠踩进了泥里。
“公主……”身边的侍女秋月声音发颤,担忧地看着她。
李云裳缓缓将信纸折好,放在桌上。
她没有哭。
也没有闹。
她的脸上甚至看不出什么表情,平静得可怕。
“修文呢?”她问,声音不起波澜。
管家一个哆嗦,“世子……世子爷他,昨夜就快马加鞭,说是要去把国公爷追回来。”
“哦?他倒是孝顺。”
李云裳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冰冷的弧度。
孝顺?
自己的妾跟亲爹跑了,他还有脸说孝顺?
简直是又蠢又坏。
“府中现在是谁在管事?”
“回公主,是……是赵姨娘。”管家答得小心翼翼。
赵姨娘,是沈修文的另一个妾,平日里最会看柳如烟的眼色行事。
让她管家,国公府的钱粮怕不是都要被搬空了去接济那对亡命鸳鸯。
“传我的令。”
李云裳站起身。
“即刻起,关闭府门,许进不许出。”
“府中所有管事、下人,全部到前院**。”
“通知赵姨娘,让她把府中所有对牌、账册,一并送到我这里来。”
她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
管家愣了一下,随即立刻躬身。
“是,公主!”
整个镇国公府,在这一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
下人们惶惶不安地被驱赶到前院,窃窃私语声不断。
“这是怎么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关府门?”
“听说了吗?国公爷跟那个柳姨娘……”
“嘘!你不要命了!这种事也敢乱说!”
赵姨娘很快就来了,脸上带着几分不情不愿。
“公主,您这是何意?世子爷刚走,您就把府里弄得鸡飞狗跳,这要是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我们国公府内宅不宁?”
她仗着自己也算半个主子,想给李云裳一个下马威。
李云裳看都没看她一眼。
“账册呢?”
赵姨娘脸色一僵,“账册都在账房,世子爷离京前吩咐了,任何人不得擅动。”
她把沈修文搬了出来当挡箭牌。
李云裳终于将目光落在了她的身上。
那目光里没有温度,像是在看一个死物。
“秋月。”
“奴婢在。”
“我记得宫里有种掌嘴的规矩,叫‘玉碎’,对吧?”
秋月垂首,“是,公主。取上好的汉白玉板,浸过冰水,掌嘴二十,保证不见血,但口中牙齿会尽数碎裂,与血水和唾沫一同咽下。”
赵姨娘的脸,“唰”一下就白了。
她双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
“公主饶命!公主饶命!我……我这就去取!”
她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再也不敢有半分顶撞。
李云裳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茶,轻轻抿了一口。
茶水苦涩,一如她此刻的心境。
但这点苦,还不够。
镇国公,柳如烟,沈修文……
这笔账,她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地跟他们算清楚。
她从来不是一个任人欺辱的女人。
以前不是。
现在,更不是。
很快,一摞摞账本被抬了进来,堆满了半个屋子。
赵姨娘像只斗败的公鸡,缩在角落里,不敢出声。
李云裳翻开第一本账册。
是采买账。
她看得极快,一目十行。
“这个月,采买胭脂水粉的银子,是上个月的三倍。为什么?”
负责采买的管事满头大汗地跪下。
“回……回公主,是柳姨娘说她新得了一张方子,要制什么……什么养颜膏,所以……”
“方子呢?”
“这……小的不知。”
李云裳合上账本,丢在一旁。
“下一个。”
她一本一本地看,一个一个地问。
从采买到修缮,从田庄到铺子。
每一个问题都精准地扎在要害上。
不过一个时辰,就有七八个管事被问得跪在地上,汗流浃背,话都说不清楚。
整个国公府的内账,就是一个巨大的筛子,千疮百孔。
而所有的漏洞,最后都指向了一个人。
柳如烟。
这个女人,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几乎将国公府的内库蛀空了一半。
而她的公爹和丈夫,对此视若无睹。
甚至,还在帮她遮掩。
真是,好大的一盘棋。
李云裳的眼神越来越冷。
她看向跪在院子里的乌泱泱的人群。
“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凡是拿过柳如烟好处,帮她做过事的,自己站出来。”
“我只问一遍。”
人群骚动起来,众人面面相觑,却无一人敢动。
李云…裳笑了。
“很好。”
她转向秋月。
“把柳如烟院子里的那个哑巴婆子带上来。”
片刻后,一个干瘦的老婆子被带了上来,眼神惊恐,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李云裳看着她。
“你是柳如烟从老家带来的,对她最是忠心。”
“我也不逼你开口。”
“我只问你,柳如烟平日里,最喜欢用哪家的点心,穿哪家的衣裳,用哪家的首饰?”
哑巴婆子愣住了。
她没想到公主会问这个。
李云裳继续说。
“你不用说话,我让秋月念,是哪家,你就点一下头。”
“秋月,从京城最有名的那几家开始念。”
秋月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起一个个商号的名字。
“宝珍斋……金玉楼……霓裳阁……”
当念到“霓裳阁”时,哑巴婆子的手指,微不可查地动了一下。
李云裳的目光一直锁定着她。
“停。”
她看向那个哑巴婆子,眼神锐利如刀。
“霓裳阁,是吗?”
哑巴婆子浑身一颤,猛地低下头,不敢再有任何动作。
但已经够了。
“来人。”
“去霓裳阁,就说我说的,他们铺子里最好的绣娘,被贼人拐走了。”
“让他们掌柜的,立刻、马上,滚过来见我。”
赵姨娘被彻底架空了权力,失魂落魄地跪在院中,看着那个曾经被她视为天神下凡的公主,如今却成了索命的阎罗。
李云裳的命令如同一道道惊雷,在国公府炸响。
府中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下人们连呼吸都小心翼翼,生怕下一个被清算的就是自己。
霓裳阁的掌柜来得很快,几乎是被人架着跑来的。
他一进门就跪下了,胖大的身躯抖得像个筛子。
“公主殿下!小人……小人不知是哪个不长眼的绣娘冲撞了您,您说!您说出来,小人立刻把她沉塘!”
李云裳坐在主位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你店里,是不是有个叫‘晚晴’的绣娘?”
掌柜的愣了一下,飞快地在脑子里搜索着。
“回……回公主,好像……好像是有这么个人,手艺不错,就是人有些孤僻,不爱说话。”
“她人呢?”
“这……她前日告了假,说是家里有急事,要回乡一趟。”掌柜的冷汗都下来了,“公主,可是她犯了什么事?”
李云裳没有回答他,而是转头看向跪在一旁的采买管事。
“我记得,柳如烟那个所谓的养颜膏方子,需要一味叫‘雪顶芙蓉’的药材,对吗?”
采买管事一哆嗦,“是……是的,公主。”
“这味药,整个京城,只有一家药铺有。”
李云裳的目光再次回到霓裳阁掌柜身上。
“而那家药铺,恰好就在你霓裳阁的隔壁。”
“掌柜的,你说,这是不是太巧了些?”
掌柜的脸色瞬间变得比死人还难看。
他“噗通”一声,重重地磕了个头。
“公主明鉴!小人……小人冤枉啊!我跟那药铺老板都不熟!”
“是吗?”
李云裳端起茶盏,用杯盖轻轻撇去浮沫。
“我的人查到,那个叫晚晴的绣娘,她的亲弟弟,就在隔壁药铺当学徒。”
“而你,每个月都会给她一笔远超她工钱的银子。”
“这些银子,兜兜转转,最后都进了一家南方的钱庄。”
“那家钱庄最大的东家,姓柳。”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掌柜的心上。
他瘫软在地,面如死灰。
完了。
全完了。
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却没想到,这位深居简出的公主殿下,只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将他的底细扒了个干干净净。
“说吧。”
李云裳放下茶杯,声音里带着一丝厌倦。
“他们往哪儿去了?”
掌柜的浑身剧颤,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他知道,一旦说了,柳家不会放过他。
可若是不说,眼前的这位公主,立刻就能让他生不如死。
“看来,你还是没想清楚。”
李云裳失去了耐心。
“秋月,传我的令,查封霓裳阁和隔壁的药铺,所有伙计、掌柜,全部下狱,严加审问。”
“另外,派人去一趟顺天府,就说镇国公府怀疑有江南巨商暗中勾结,意图不轨,请他们协助调查所有与柳家钱庄有往来的商号。”
“告诉顺天府尹,这是本宫的意思。”
“是,公主!”
掌柜的听到“顺天府”三个字,最后一丝心理防线也崩溃了。
查封店铺,他还能东山再起。
可一旦惊动了顺天府,那就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我说!我说!公主饶命啊!”
他涕泪横流地磕着头。
“柳姨娘……柳姨娘他们,往通州码头去了!他们包了一艘漕船,准备南下!”
“船号是‘顺风’!”
通州码头。
漕船。
李云裳的眼中闪过一丝厉色。
他们倒是会选地方。
通州码头鱼龙混杂,漕运又是朝廷命脉,盘根错节,一旦混入其中,便如鱼入大海,再难寻找。
“很好。”
李云裳站起身。
“备马。”
秋月大惊,“公主,您要亲自去?”
“不然呢?”李云裳反问,“指望我那个‘孝顺’的夫君吗?”
她走到门口,顿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院中跪着的众人。
“在我回来之前,府里所有人,各司其职,若有半点差池……”
她没有说后果。
但所有人都打了个寒颤。
京郊官道上,十几匹快马疾驰而过,卷起一阵烟尘。
为首的女子一身玄色劲装,身姿挺拔,正是换了男装的李云裳。
身后跟着的,是她从公主府带来的亲卫。
这些人,只听她一人的号令。
通州码头不远,快马加鞭,不到两个时辰便到了。
码头上人声鼎沸,扛着麻袋的苦力,吆喝着的小贩,南来北往的客商,构成了一副繁忙而混乱的景象。
要在这里找一艘船,无异于大海捞针。
李云裳勒住马,目光扫过停靠在岸边的无数船只。
“分头去找,找船号‘顺风’的漕船。”
“是!”
亲卫们立刻散开,融入人群之中。
李云裳翻身下马,牵着马,缓缓走在码头上。
她没有丝毫的慌乱。
越是危急的时刻,她越是冷静。
这是她从父皇那里学到的,身为一个皇族,永远不能让人看到你的失态。
一个亲卫很快跑了回来。
“公主!找到了!”
“那艘船在一个时辰前已经离港了!”
李云裳的心猛地一沉。
还是晚了一步。
“能确定他们就在船上吗?”
“能!码头的一个管事看见了,说是一个富家老爷,带着一个极美的女子上的船,身边还跟了几个护院。”
描述完全对得上。
李云裳的拳头瞬间握紧。
就这么让他们跑了?
她不甘心!
“公主,现在怎么办?水路难追,他们顺流而下,我们的马匹派不上用场。”亲卫队长焦急地问。
李云裳沉默了。
她看着眼前这条浑浊的运河,河水滔滔,向着无尽的远方流去。
难道,真的就只能到此为止了吗?
不。
绝不。
她李云裳的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
漕运,归漕运总督管辖。
而当今的漕运总督,是三年前她亲自向父皇举荐的。
那个人,欠她一份天大的人情。
“去驿站。”
李云裳翻身上马,声音果决。
“用八百里加急,给漕运总督衙门送一封信。”
“就说,本宫有要事相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