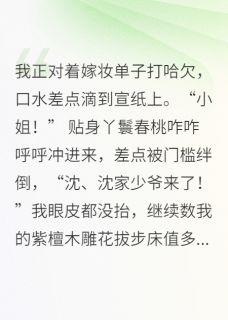
我正对着嫁妆单子打哈欠,口水差点滴到宣纸上。“**!
”贴身丫鬟春桃咋咋呼呼冲进来,差点被门槛绊倒,“沈、沈家少爷来了!
”我眼皮都没抬,继续数我的紫檀木雕花拔步床值多少银子。“来就来呗,下个月就成亲了,
他哪天不来晃悠两圈?”“不是啊**!”春桃急得跺脚,“他、他一来就问小荷!
问小荷在哪儿!”小荷?我笔尖一顿,墨团在“金丝楠木妆奁”旁边洇开一小块。
小荷是我娘特意给我挑的陪嫁丫鬟,老实巴交,话不多,干活挺麻利,
属于丢人堆里找不着那种。“找她干嘛?”我放下笔。
“说是…说是他祖母想抄几卷佛经供奉,听说小荷字写得好,想借去用两天。”春桃撇撇嘴,
“**您的字才叫好呢!他沈家又不是没人了!”正说着,
我那未婚夫沈砚的声音就从门外飘了进来,带着点刻意装出来的温润。“亭亭?在忙吗?
”沈砚掀帘子进来,一身月白长衫,人模狗样。他目光先是在屋里扫了一圈,掠过我的脸,
没多停留,最后定在角落里正安静擦花瓶的小荷身上,眼神明显亮了一下。“砚哥哥。
”我站起来,脸上堆起职业假笑,“稀客啊,今天怎么有空?”“咳,”他清了清嗓子,
视线总算落回我脸上,有点飘,“祖母礼佛心切,想抄几卷《金刚经》供在佛前。
听闻你身边的小荷姑娘写得一手好簪花小楷,不知可否……借去几日?”他这话是对我说的,
眼睛却不由自主地瞟向小荷。小荷立刻放下抹布,低着头,小碎步挪过来,
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少爷吩咐,奴婢自当尽力。”“嗯,好,好。”沈砚嘴角弯起,
那笑容比刚才对我真诚多了,“那就辛苦小荷姑娘了。我这就带你去见祖母?
”“急什么呀砚哥哥,”我一步跨过去,挡在他和小荷中间,笑嘻嘻地,“小荷是我的人,
祖母要用人,跟我说一声就行。抄经是好事,不过嘛……”我故意拖长了调子,看着沈砚。
“不过什么?”他有点急。“不过小荷是我房里的大丫头,她走了,我这儿一堆事谁管?
梳头、熨衣、管库房钥匙……离了她,我这日子可没法过。”我掰着手指头数,一脸为难。
沈砚眉头微蹙:“就几日功夫,亭亭你通融一下?祖母年纪大了,
就这点念想……”“通融……也不是不行。”我话锋一转,笑得像只狐狸,“这样,砚哥哥,
你把你书房里那方新得的澄泥砚押我这儿。等小荷完完整整回来了,我再还你。
万一祖母用着顺手,多留她几天,我这儿没个抵押,心里不踏实。”沈砚那方宝贝澄泥砚,
是前些日子他爹花大价钱弄来的,他天天显摆。他脸色顿时有点僵:“这……亭亭,
何必如此?”“哎呀,砚哥哥不会是舍不得吧?”我故作惊讶,“难道在你心里,
祖母抄经的心愿,还比不上一块石头?还是说……”我拖长声音,
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小荷,“你觉得小荷一去……就回不来了?
”沈砚被我噎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最后咬牙:“好!我这就叫人取来!
”小荷被沈砚的贴身小厮带走了。春桃凑过来,一脸愤愤:“**!您瞧见没?
沈少爷那眼睛,都快黏小荷身上了!借人抄经?我看他就是故意的!”我重新拿起嫁妆单子,
慢悠悠地说:“急什么。是我的,别人抢不走。不是我的,拴裤腰带上也得飞。
”话是这么说,心里那点不舒服还是像根小刺,扎着。接下来的几天,
沈砚往我家跑得更勤了。美其名曰商议婚仪细节,或者给我送些时兴的点心玩意儿。
但十次有八次,他**刚坐热,话题就会“自然而然”地拐到小荷身上。“亭亭,
祖母说小荷抄的经卷极好,字迹娟秀工整,心也静,老人家喜欢得紧,想多留她几日,
帮她整理一下佛堂的旧经书,你看……”“行啊。”我捏着一块他带来的桂花糕,咬了一口,
太甜,腻得慌。“留呗,记得我的澄泥砚就行。”他噎了一下,讪讪道:“自然,自然。
”又一天,他带来一幅画,说是新得的山水,邀我品评。我对着那山啊水啊看了半天,
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敷衍道:“嗯,挺好,山是山水是水。”沈砚却兴致勃勃,
指着画角落款处:“亭亭你看这题跋的小字,风骨俊逸……”我打断他:“砚哥哥,这字,
比起小荷的簪花小楷如何?”沈砚一愣,
随即脸上浮现出一种奇异的、混合着欣赏和回味的表情:“小荷姑娘的字……清丽婉约,
别有一番韵味,如同她的人一样,温婉可人,耐人寻……”“停!”我放下糕点,
拍了拍手上的碎屑,“砚哥哥,你是来跟我赏画的,还是来夸我的丫鬟的?
”沈砚的脸瞬间涨红,
尴尬地咳了几声:“我……我只是觉得小荷姑娘确实难得……”“难得?”我挑眉,
“我家丫鬟,自然是好的。不过砚哥哥,你这‘难得’二字,用的次数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坐立不安地喝了半盏茶,就借口有事匆匆走了。
春桃对着他的背影狠狠啐了一口:“呸!什么玩意儿!**,您就不该让小荷去!
”我端起凉掉的茶喝了一口,心里那点不舒服,从小刺变成了小石头。终于,小荷回来了。
人是沈砚亲自送回来的。不过十来天光景,小荷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身上那件半旧的青布衫子换成了簇新的水绿色绸裙,料子一看就不便宜。
头上那根素银簪子也不见了,换成了一支小巧的珍珠簪子,光泽温润。她低着头,
跟在沈砚身后半步,脸颊泛着淡淡的红晕,手指绞着新裙子的衣角。“亭亭,
小荷姑娘这些日子辛苦了,祖母很是喜欢。”沈砚的目光几乎没离开过小荷,
“我……我替祖母备了份薄礼,给小荷姑娘,也算酬谢。”他指了指小荷身上的衣裙和簪子。
“哦?”**在门框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沈少爷真是有心了。替我谢过老夫人。
”我特意加重了“替我”两个字。沈砚似乎没听出弦外之音,
又殷切地看向小荷:“小荷姑娘,以后若得空,祖母那边……”“沈少爷,”我打断他,
声音冷了下来,“小荷是我的丫鬟,她的‘空’,得由我来安排。祖母若有事,
直接吩咐我就是。人,我已经‘借’过一次了,没有下次。”沈砚的脸色终于变了,
有些难看。小荷飞快地抬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委屈中带着点依赖。“亭亭,
你何必如此……”“我累了。”我直接下了逐客令,“春桃,送沈少爷。”沈砚走后,
屋子里安静下来。小荷还站在那儿,穿着那身刺眼的新裙子。“**……”她怯生生地开口。
我走到她面前,围着她慢慢转了一圈,目光扫过那绸裙,那珍珠簪。“裙子不错,
料子是‘云锦阁’的吧?这簪子……东珠的,也不便宜。老夫人出手真大方。
”小荷的头垂得更低了,声音发颤:“是……是老夫人赏的……奴婢不敢推辞……”“是吗?
”我停下脚步,站在她正对面,盯着她低垂的眼睫,“是老夫人赏的,
还是你的‘砚少爷’赏的?”小荷浑身一颤,猛地抬头,脸色煞白:“**!奴婢不敢!
奴婢只是尽心伺候老夫人抄经……”“尽心?”我嗤笑一声,
“我看你是尽心得连自己是谁的奴才都快忘了!”“**息怒!”小荷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眼泪说来就来,簌簌往下掉,“奴婢对**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沈少爷……沈少爷他只是……只是怜惜奴婢出身微寒,识得几个字……”“怜惜?
”我蹲下身,捏住她的下巴,强迫她抬起头看着我梨花带雨的脸,
“他沈砚是我楚亭的未婚夫,他该‘怜惜’的人是谁?轮得到他来‘怜惜’你一个丫鬟?
”她的眼泪滚烫,滴在我手指上。那眼神,除了恐惧,
深处似乎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不甘?“奴婢知错了!**饶了奴婢这次吧!
”她哭得浑身发抖。我松开手,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她:“滚回你自己屋里去。
这身衣裳,这簪子,既然老夫人‘赏’了,你就留着。好好留着,当个念想。
”小荷连滚爬爬地退了出去。春桃气呼呼地进来:“**!您就这么放过她了?
瞧她那狐媚样子!还有沈少爷,眼珠子都快掉她身上了!”我走到铜盆边,
仔仔细细地洗着手,仿佛刚才碰了什么脏东西。“急什么。”我看着水波,声音没什么起伏,
“狐狸尾巴,藏不住的。”果然,小荷回来后,变得“娇弱”了。饭吃得少了,说是没胃口。
活儿干着干着,就捂着心口说头晕,要歇会儿。更离谱的是,有一次沈砚又借着送东西过来,
在花园“偶遇”正在“头晕”的小荷。我隔着假山,
清清楚楚听到小荷那柔得能滴出水的声音:“……多谢少爷关心,
奴婢只是……只是早起有些不适,
不碍事的……少爷您对奴婢真好……”沈砚的声音温柔得能拧出蜜:“快别这么说,
你身子弱,要多休息。上次送你的燕窝,可吃了?若不够,
我再让人送来……”我捏断了手里刚折的一支月季。好,真好。我的未婚夫,
拿着我未来婆家的钱,给我的丫鬟送燕窝养身子?日子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滑向我的婚期。
嫁衣送来了,大红的云锦,金线绣着鸾凤和鸣,华美得刺眼。我娘欢天喜地地拉着我试穿,
嘴里念叨着沈家如何体面,沈砚如何青年才俊。我像个木偶一样任她们摆布,
看着镜子里那个一身红妆、面无表情的自己。沈砚来“探望”的次数更多了,每次来,
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往丫鬟堆里瞟。小荷则愈发“弱柳扶风”,脸色苍白,走路都扶着腰。
府里的风言风语像长了脚,悄悄蔓延开。“听说了吗?西院的小荷,
怕是有身子了……”“真的假的?谁的?”“还能是谁的?那位天天往这儿跑的呗!啧啧,
还没过门呢,通房丫头先揣上了……”“嘘!小声点!让大**听见……”我坐在秋千上,
面无表情地听着墙根下两个婆子的窃窃私语。春桃气得脸都绿了,要冲出去骂人,
被我一把拉住。“**!”春桃急得快哭了,“您就由着他们这么糟践您?”“糟践?
”我轻轻晃着秋千,“嘴巴长在别人身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话虽如此,
心却一点点沉下去,像浸在冰水里。沈砚,小荷……你们最好别是真的。又过了几天,
一个闷热的午后。我嫌屋里憋得慌,想去后花园水榭边的凉榻上歪一会儿。那地方僻静,
挨着府里一处堆放杂物的旧书阁。刚走近书阁,就听见里面传来刻意压低的说话声。
一男一女。“……少爷,
奴婢害怕……要是被**知道……”是小荷那熟悉又陌生的、带着哭腔的娇柔声音。
“怕什么?”是沈砚,声音里透着安抚,还有一丝……急切?“她不会知道的。小荷,
你听话,再让我看看……你这字,真是越写越好了,
比那些所谓的才女强百倍……”我脚步钉在原地,血液似乎都冲到了头顶。
书阁的门虚掩着一条缝。我屏住呼吸,凑近那条缝隙。里面光线昏暗。沈砚背对着门站着,
小荷被他半圈在怀里,两人靠在一张堆满旧书卷的破桌子旁。沈砚一只手握着小荷执笔的手,
另一只手……正轻轻抚摸着她的腰背!“少爷……”小荷半推半就,脸颊绯红,
“您别这样……奴婢……奴婢的字不值一提……”“谁说的?”沈砚低头,
嘴唇几乎贴到小荷的耳朵,“在我心里,你就是最好的……”他握着她的手,
在纸上写着什么,身体贴得更紧。小荷发出一声似有若无的嘤咛。
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怒火瞬间烧光了所有理智。“砰!
”我猛地一脚踹开了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巨大的声响把里面两个偷情的人吓得魂飞魄散。
沈砚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松开小荷,转过身,脸上血色尽褪,
写满了惊恐和狼狈:“亭……亭亭?!”小荷更是吓得尖叫一声,
手里的笔“啪嗒”掉在地上,墨汁溅脏了她的新裙子。她瑟缩着躲到沈砚身后,
像只受惊的兔子,脸色惨白如纸。“好!好一对才子佳人!好一个‘怜惜’!
好一个‘教习书法’!”我站在门口,逆着光,声音冷得像淬了冰的刀子,
一字一句砸过去。沈砚慌乱地整理着自己微乱的衣襟,试图解释:“亭亭,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只是在教小荷写字!她……她最近想学……”“学写字?
”我一步步走进来,逼视着他,目光扫过他身后抖如筛糠的小荷,“学到需要搂着腰?
贴着脸?沈砚,你当我是三岁孩童,还是瞎了?!”“亭亭!你冷静点!
”沈砚被我逼得后退一步,脸上又急又怒,“小荷她……她只是我的丫鬟!
我对她……最多是怜其才情!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失了大家闺秀的风范!
”“大家闺秀的风范?”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指着他身后的小荷,
“就是看着自己的未婚夫,跟一个**的陪嫁丫鬟,在堆破烂的旧书阁里搂搂抱抱?!沈砚,
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小荷突然从沈砚身后冲出来,
“扑通”一声跪倒在我脚边,抱住我的腿,哭得撕心裂肺,“**息怒!都是奴婢的错!
是奴婢不好!
婢不该痴心妄想……是奴婢仰慕少爷才学……少爷只是可怜奴婢……少爷心里只有**您啊!
求您别怪少爷!”她哭得情真意切,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沈砚看着她跪地哀求的样子,
眼中闪过一丝心疼,看向我的目光也带上了责备:“亭亭!你看看!小荷她如此卑微!
你何必还要如此羞辱她!她只是个丫鬟!”“丫鬟?”我低头,看着脚边哭成泪人的小荷,
她仰起脸,那双泪眼朦胧的眸子里,除了恐惧和哀求,深处分明藏着一丝隐秘的得意和挑衅!
一股无法抑制的恶心感猛地冲上喉咙!“呕——!”我猛地弯腰,干呕起来。“**!
”春桃惊呼着冲进来扶住我。沈砚也吓了一跳,下意识想上前:“亭亭你怎么了?
”就在这时,跪在地上的小荷脸色突然一变,捂着嘴,也发出一声更剧烈的干呕:“呕——!
”她的反应比我大多了,整个人蜷缩起来,脸色瞬间由白转青,呕吐声一声接一声,
痛苦不堪。书阁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小荷撕心裂肺的干呕声。我捂着嘴,冷冷地看着她。
沈砚僵在原地,看着小荷痛苦的样子,又看看我,眼神惊疑不定。春桃扶着我的手,
在我耳边低语,声音带着惊骇:“**……她……她这反应……”我看着小荷吐得昏天黑地,
连胆汁都快呕出来的狼狈样子,又想起府里那些风言风语,
想起她最近的反常……一个可怕的、荒谬的念头,无比清晰地浮现在脑海。
“呵……”我直起身,擦掉嘴角并不存在的污渍,看着脸色煞白的沈砚,
又看看地上蜷缩成一团、还在干呕的小荷,发出一声极其冰冷的嗤笑。“沈砚,
”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像结了冰的湖面,“看来,你这‘怜惜’,‘怜惜’得挺到位啊?
连‘结果’都有了?”沈砚的脸,“唰”地一下,血色褪尽,变得惨白如纸。
他震惊地、难以置信地看向地上的小荷。小荷的呕吐声戛然而止。她猛地抬起头,
脸上毫无血色,眼神惊恐万状,像是被雷劈中。书阁里死一般的寂静。空气凝固得如同实质,
压得人喘不过气。只有小荷粗重而恐惧的喘息声,格外刺耳。沈砚像是被钉在了原地,
眼睛死死盯着小荷平坦的小腹,又猛地看向我,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
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那表情,混杂着震惊、茫然、被戳穿的恐慌,
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怪异。
“不……不是的……**……奴婢没有……”小荷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带着哭腔,
抖得不成样子,挣扎着想爬起来。“没有?”我往前走了一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声音不大,却像淬了毒的针,“那你这吐得天昏地暗,是吃坏了东西?还是……你肚子里,
揣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亭亭!”沈砚像是被惊醒,猛地冲我低吼,试图阻止我,
“你胡说什么!没有证据的事,怎能如此污人清白!”他额角青筋都暴了起来,
眼神却心虚地飘忽着,不敢直视我。“污人清白?”我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目光如刀,
在他和小荷之间来回扫视,“沈砚,你们俩刚才在这黑灯瞎火的书阁里,搂搂抱抱,
是当我眼瞎?现在她吐成这样,是当我傻?府里上下传得沸沸扬扬的风言风语,是当我聋了?
!”我指着小荷,每一个字都像冰雹砸下:“清白?你告诉我,她一个未嫁的丫鬟,
哪来的这种反应?!你告诉我!”小荷被我吼得浑身一颤,瘫软在地,只剩下绝望的呜咽。
沈砚被我逼得连连后退,脸上血色尽失,狼狈不堪,
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一种奇怪的无力感?他张了张嘴,最终却只是颓然地垂下头,
双手紧握成拳,指节捏得发白,却没有再反驳。他默认了。这个认知,像一把烧红的烙铁,
狠狠烫在我的心上。之前所有的怀疑、愤怒、恶心,此刻都化作了冰冷的、尖锐的痛楚。
“好……好得很!”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咙口的腥甜,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不发抖,
却带着一种玉石俱焚的决绝,“沈砚,带着你的心肝宝贝,给我滚出楚家!
”“亭亭……”沈砚痛苦地抬起头,还想说什么。“滚!”我用尽全身力气吼出这个字,
声音尖利得划破了凝固的空气,“立刻!马上!否则,我不介意现在就敲锣打鼓,
请街坊四邻都来看看,沈家未来的少奶奶还没进门,未来的姑爷是怎么疼惜她陪嫁丫鬟的!
”沈砚身体猛地一震,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他死死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复杂得难以形容,有愧疚,有难堪,似乎还有一丝……如释重负?他最终什么也没说,
弯腰,几乎是粗暴地一把将地上瘫软的小荷拽了起来。小荷被他拽得一个趔趄,
发出一声痛呼,脸上泪痕交错,眼神空洞绝望。沈砚半拖半抱着她,
踉踉跄跄地从我身边挤过,逃也似的冲出了破旧的书阁,消失在花园小径的尽头。
我站在原地,身体僵硬得像块石头。书阁里还残留着他们身上那股令人作呕的气息,
还有小荷呕吐物的酸腐味。“**……”春桃带着哭腔扶住我,声音里满是心疼和愤怒,
“您别气坏了身子……他们……他们简直猪狗不如!”我闭上眼,再睁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