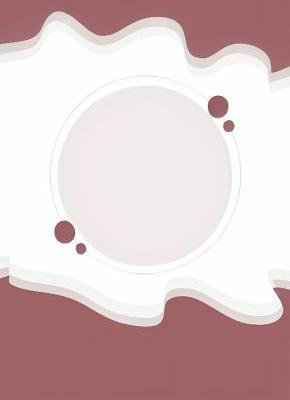
第一章:一纸契约会议室位于摩天大楼顶层,落地窗外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景色,
天际线在暮色中勾勒出冰冷的轮廓。沈知意坐在宽大的皮质座椅上,
只觉得那股寒意透过衣料,直渗进骨头缝里。她的对面,陆景珩将一份文件推了过来。
“沈**。”他的声音和他的表情一样,平静无波,像在讨论一笔再寻常不过的交易,
“这是协议。为期三年,你需要履行的义务,和你能获得的回报,都写得很清楚。
”沈知意的目光落在文件封面上。“婚姻协议”四个加粗黑体字,像四根冰冷的钉子,
钉在她的视线里。她伸出手,指尖有些发颤,翻开了第一页。条款细致到近乎苛刻。隐婚,
分居,每月固定生活费额度,
需要陪同出席的社交场合类型和频率……甚至包括在公共场合的称呼、肢体接触的界限。
最后,
续所有治疗费用、偿还家庭债务、还能让家里那个风雨飘摇的小印刷厂重新运转起来的巨款。
数字后面跟着的零,晃得她眼睛发涩。“为什么……是我?”她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
这个问题很蠢,在来之前,中间人已经说得很清楚。
陆景珩需要一个背景干净、没有复杂社会关系、且短期内急需用钱的“妻子”,
来应对家族催婚和一些不必要的商业联姻试探。而她,恰好符合所有条件,
尤其是最后一条——走投无路。陆景珩抬眼看了她一下,那眼神像在评估一件物品的实用性。
“你合适。”他言简意赅,重新看回腕表,“我需要一个省心、守约的合作方。
你父亲的病情,还有你家的债务,周延已经核实过。签下它,你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省心。守约。合作方。每一个词都精准地剥离了这桩“婚姻”最后一点温情脉脉的可能。
沈知意攥紧了放在膝上的手,指甲陷进掌心,细微的刺痛让她保持清醒。
她想起医院里父亲插着管子的虚弱模样,想起母亲偷偷抹泪时佝偻的背影,
想起家里那些跟了父亲十几年的老师傅们忧虑的脸。她没有别的选择。拿起笔,笔身冰凉。
她在乙方签名处,一笔一划地写下“沈知意”三个字。笔迹有些抖,但终究是签下了。
把自己未来三年的自由和“妻子”这个名分,明码标价地卖了出去。陆景珩等她签完,
拿过协议,目光扫过签名,点了点头。周延适时上前,收好文件。“明天下午,
周延会接你过去。你的物品不必多带,那边会准备必需品。”陆景珩站起身,
高大的身形带来无形的压迫感,“希望我们合作愉快,沈**。”他没有说“再见”,
只是微微颔首,便转身离开了会议室。昂贵的手工皮鞋踩在地毯上,几乎没有声音,
就像他这个人,存在感极强,却又带着一种拒人千里的寂静。
沈知意独自坐在渐渐暗下来的会议室里,窗外华灯初上,璀璨夺目,
却照不亮她心底那片冰冷的荒芜。---第二天,她带着一个小小的旧行李箱,
站在了那间传说中的顶层公寓门前。周延为她刷卡开门,语气礼貌而疏离地介绍着各个区域,
最后停在一扇房门前:“这是您的房间,沈**。陆总的主卧和书房在另一侧。
这是门禁卡、生活费卡,以及近期可能需要您预留时间的场合列表。”房间很大,
装修是统一的性冷淡风,灰白基底,线条利落,整洁得像五星级酒店的套房,
没有一丝烟火气。她打开行李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只有一本边缘磨损的素描本,
和一张嵌在简易相框里的全家福。她把相框放在床头柜上,素描本搁在空荡荡的书桌上,
这偌大空间里,才有了那么一点点属于“沈知意”的痕迹。陆景珩果然如周延所说,
极其忙碌。入住头三天,沈知意连他的面都没见到。她像个幽灵,
在这所奢华却冰冷的宫殿里悄无声息地游荡,自己做饭,自己看书,自己对着窗户画画。
偌大的空间,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第一次履行“义务”,是在一个商业酒会上。
礼服是提前送来的,尺码分毫不差。陆景珩看到她时,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大约两秒,
点了下头。“跟着我,微笑,不必多话。有人问起,统一回答是家族介绍,相处融洽。
”酒会觥筹交错,衣香鬓影。陆景珩无疑是全场焦点,
而他身边突然出现的、面容清丽却眼生的“陆太太”,也引来了无数探究的目光。
他挽着她的手,力度适中,姿态标准,向旁人介绍:“我太太,沈知意。”语气平淡,
听不出亲疏。沈知意努力维持着嘴角的弧度,应对着那些或好奇或审视的视线。
新鞋的鞋跟很细,渐渐磨痛了脚后跟。她悄悄调整重心,指尖掐着掌心。
陆景珩正与人交谈一个项目的前景,侧脸线条冷硬,眼神专注,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边女伴细微的不适。她忽然觉得有些可笑。这就是她未来的生活吗?
扮演一个精致的花瓶,站在他身边,装饰他的门面,忍受着物理上的疼痛和心灵上的隔膜,
换取家人安康。“累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忽然在耳边响起。沈知意蓦然回神,
发现陆景珩不知何时结束了谈话,正垂眸看着她。两人距离很近,
她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须后水味道。“还好。”她迅速调整表情,笑了笑。陆景珩没说什么,
只是手臂微微收紧了些,带着她走向休息区。“坐一会儿。还要半小时。
”这算是他难得的、近乎体贴的举动吗?沈知意不确定。
或许只是他察觉到“花瓶”状态不佳,可能影响展示效果。酒会结束回去的车上,
两人一路无话。陆景珩闭目养神,沈知意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流光溢彩,脚后跟**辣地疼。
---之后的日子,依旧平淡如死水。直到那天凌晨。陆景珩有应酬,
提前发信息告知会晚归。沈知意记得协议附件里那条:甲方晚归时,乙方需在公共区域等候,
营造家庭氛围。她谈不上心甘情愿,但既然签了字,该履行的条款她不会打折扣。
凌晨一点多,电子锁轻响。陆景珩走进来,身上带着夜风的凉意,
还有一丝极淡的、甜腻的女士香水味。他扯开领带,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目光扫过客厅,
忽然顿住。客厅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暖黄色的光晕洒下一小片温暖的范围。
沈知意蜷在沙发一角,身上盖着薄毯,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已经睡着了。
暖光柔和地勾勒出她安静的侧脸,长睫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看起来毫无防备。
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只小小的白色保温盅。陆景珩站在原地,看了她几秒。
他习惯了回家时空无一人的冰冷和黑暗,习惯了绝对的安静。眼前这一幕,陌生,突兀,
却奇异地……不让人讨厌。甚至,那暖黄的光,
让这间他住了多年却始终觉得只是个落脚处的房子,
有了一丝极其微弱的、不同于往常的气息。他走过去,脚步声很轻,但她还是醒了。
或许是睡得并不沉,她有些茫然地睁开眼,看清是他,立刻坐直身体,毯子滑落一些。
“陆先生,您回来了。”她声音带着刚醒的微哑,迅速恢复了平日的清醒疏离,拿起保温盅,
“这是醒酒汤,温度应该合适。您需要的话……”“放着吧。”陆景珩打断她,
目光落在她还有些惺忪的脸上,“怎么在这里睡?”“协议要求。”她回答得很快,站起身,
把毯子叠好,“您早点休息。”说完,便抱着自己的书,准备回房。“沈知意。”他叫住她。
她停在房门口,回头,眼神带着疑问。陆景珩看着那双清澈却总隔着一层雾似的眼睛,
一时也不知自己为何要叫住她。沉默了几秒,他才开口,
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低沉:“以后超过十二点,不用等。”沈知意微微怔了一下,
随即点头:“好的。”然后轻轻关上了房门。陆景珩走到沙发边,拿起那只保温盅。
盖子打开,温热的气息带着淡淡的药材清香扑面而来。他喝了一口,温度刚好,
暖流顺着食道滑下,缓解了应酬带来的些微不适。他端着汤盅,站在那盏落地灯旁,
暖黄的光将他挺拔的身影拉长投在墙上。这光,这汤,
还有刚才那个蜷在沙发上安静睡着的影子……某种极其细微的、陌生的东西,
在他习惯于精密计算和绝对掌控的世界里,悄无声息地撬开了一丝缝隙。而一门之隔,
沈知意背靠着冰凉的门板,抬手按了按心口。刚才被他目光注视的瞬间,
她竟有一丝莫名的心慌。是因为那陌生的香水味,还是因为他那句意味不明的“不用等”?
她摇摇头,甩开杂念。不过是契约,不过是各取所需。那盏灯,那份汤,
都是条款内的义务而已。只是心底某个角落,似乎有什么东西,被那抹暖黄的光,
轻轻地、不为人知地拨动了一下。第二章:无声渗透保温盅事件像一粒投入静湖的小石子,
涟漪微不可察,很快便消散了。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既定的轨道:陆景珩依旧忙碌,
沈知意继续在她安静的世界里画画、接稿,两人在宽敞公寓里维持着礼貌而疏远的同居模式。
变化是从细微处开始的。沈知意为了节省,午餐通常是自己简单做的三明治或沙拉,
有时忙起来甚至忘了吃。直到有一天,
周延再次提着那个熟悉的、印着某家顶级养生食府标志的餐盒出现。“沈**,陆总交代,
以后您的午餐由这边统一安排。”周延将精致的多层餐盒放在画室的小桌上,
“考虑到您需要维持良好状态以履行协议义务,营养均衡是必要的。
”沈知意看着餐盒里搭配精美、显然价格不菲的菜品,沉默了一下。
“陆先生他……怎么会知道?”周延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板:“陆总注意到您近期气色欠佳。
这不利于公共形象。”又是“协议义务”,又是“公共形象”。沈知意垂下眼睫,道了谢。
餐食很美味,但她吃得有些不是滋味。这份过于“周全”的照顾,像一道无形的栅栏,
提醒着她这段关系的本质。然而,没过两天,轮到她做出了“越界”的举动。一个清晨,
她起得早,去厨房倒水,隐约听到陆景珩在客厅压低声音讲电话,
语气有些不耐:“……知道了,老毛病,吃点药就行。”随即是抽屉拉开又关上的声音。
胃病?沈知意想起他饮食常常不规律,应酬又多。她什么也没说,默默回了自己房间。
但那天下午,她特意去买了上好的蜂蜜和金桂。第二天早餐时,陆景珩的位置上,
除了惯常的咖啡和财经报纸,多了一个小巧的玻璃罐。罐身透明,
里面是晶莹剔透的琥珀色膏体,沉浮着细碎的金色桂花,旁边贴着一张素色便签,
上面是清秀的字迹:“蜂蜜桂花酱,温水冲服,养胃。”陆景珩拿起报纸的手顿了顿,
目光在那个小罐子上停留了片刻。他没说什么,也没有动它,像往常一样用完早餐便出门了。
但那天晚上,沈知意在厨房清洗画具时,发现那个玻璃罐已经被洗净,
安静地立在专用橱柜的一角,里面空了一半。无声的交换,以“义务”和“无意”为名,
在这冰冷的空间里悄然进行。---第一次以“陆太太”身份参加陆家的家族聚会,
对沈知意而言,不啻于一场小型的公开刑。陆景珩父母早逝,由祖父带大,
如今老爷子半退休,家族内各路旁支亲戚心思活络。
沈知意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背景平平的“孙媳妇”,自然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以及某些人彰显自身优越感的靶子。“知意是吧?听说是学画画的?
”一位珠光宝气的堂姑打量着她身上那件并非当季最新款的礼服,笑容亲切,
眼神却带着衡量,“艺术家好,清高。不过嫁进陆家,以后那些抛头露面卖画的事,
是不是就得收收了?毕竟身份不同了嘛。”另一位年轻些的堂妹笑着接话:“是啊嫂子,
以后多跟我们逛逛会所、看看秀,学学怎么打理自己。景珩哥那么忙,
总得有个能带得出去的太太呀。”话语里的绵里藏针,沈知意听得明白。
她放下手中的骨瓷茶杯,抬起眼,脸上依然是温婉得体的微笑:“谢谢姑姑关心。
画画是我的专业和爱好,就像姑姑喜欢收藏珠宝一样,都是生活中的一点乐趣。
至于抛头露面,”她语气平和,“我觉得靠自己的手艺获得认可,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景珩也一直很支持我。”她不疾不徐,既没有怯懦回避,也没有尖锐反击,
四两拨千斤地将话题带过,甚至抬出了陆景珩——虽然她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支持”。
陆景珩坐在主位附近,正与一位叔公谈论股市,似乎并未留意女眷这边的机锋,
只是在她说完后,目光若有似无地朝她这边扫了一眼。聚会结束,回到车上,
陆景珩忽然开口:“下次需要衣服首饰,直接联系周延,或者让相熟的品牌送目录到家里。
陆太太不需要为这种场合费心置装。”他的话听起来像是责备她今晚不够光鲜,给他丢了脸。
沈知意抿了抿唇,心底那点因为他刚才那一眼而升起的微微暖意,又凉了下去。“知道了。
”她低声应道。几天后,沈知意在刷新闻时,偶然看到一则财经短讯,
提及陆家某位旁支参与的公司,在一个重要**项目中意外出局,原因语焉不详。她记得,
那家公司似乎是那位“亲切”堂姑的丈夫在打理。她盯着那则短讯看了几秒,
默默关掉了页面。---她的小工作室渐渐有了起色,接到的稿约多了,
却也引来了同行的侧目。一天下午,两个自称是某设计公司的人找上门来,
在她租用的共享工作室里,大声指责她近期一套商业插画“借鉴”了他们未公开的设计创意,
言辞激烈,引来不少其他工作室的人探头张望。
沈知意试图冷静解释创作思路和独立完成的过程,对方却不依不饶,
甚至开始用半威胁的语气要求赔偿和公开道歉。正当她感到孤立无援,
脸颊因难堪和气愤而微微发烫时,工作室玻璃门被推开了。陆景珩走了进来。
他显然刚从某个正式场合过来,穿着挺括的深色西装,气场凛然。
他甚至没看那两个闹事者一眼,径直走到沈知意身边,目光在她有些发白的脸上停留了一瞬,
然后转向那两人,语气平淡,
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关于我太太作品涉嫌抄袭的争议,
可以直接联系恒屿集团法务部提交证据。他们会负责评估,
并追究一切诽谤和不当竞争的法律责任。”“恒屿集团法务部”几个字,像一盆冰水,
瞬间浇灭了那两人的气焰。他们显然认出了陆景珩,脸色变了变,支吾几句,灰溜溜地走了。
围观人群散去,狭小的工作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沈知意松了口气,肩膀微微垮下,
低声道:“谢谢。”陆景珩看着她,她今天穿了件简单的棉质衬衫,袖口沾了点颜料,
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眼睛很亮。他“嗯”了一声,移开视线,看向她画板上未完成的草稿,
状似随意地说:“这里环境太杂。恒屿旗下有艺术孵化空间,安保和设施都好些,
我让周延帮你安排。”“不用了,”沈知意几乎是立刻拒绝,“这里挺好的,
离家……离公寓也近。而且,这是我自己的事,不想太麻烦你。”“麻烦?
”陆景珩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他看着她脸上明显的疏离和坚持,
最终没再说什么。“随你。”他转身朝门口走去,在推开门前,又停下,背对着她说了一句,
“有事打电话。”沈知意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心情复杂。他又一次替她解了围,
用的是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可她无法分辨,这维护背后,
有多少是出于“陆太太”这个身份不容侵犯,有多少是……别的什么。那句“有事打电话”,
比起命令,更像是一句生硬的……关心?她甩甩头,禁止自己深想。---打破平静的,
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深夜,雷电交加,暴雨如注,公寓所在的片区因电路故障骤然停电,
一切陷入浓稠的黑暗和震耳欲聋的雷声之中。沈知意怕打雷,
童年的阴影让她对这种天气有着本能的恐惧。停电时她正在客厅找一本画册,
瞬间的黑暗和接踵而至的炸雷让她僵在原地,心脏狂跳。她摸索着想回房间,
脚下却被矮凳绊了一下,低呼一声。“别乱动。”陆景珩的声音从书房方向传来,沉稳镇定。
接着,一点摇曳的暖光亮起,他举着一支应急蜡烛走了过来。烛光驱散了一小片黑暗,
映出他没什么表情的脸,却在这样的时刻,莫名给人一种安定的力量。他把蜡烛放在茶几上,
自己则坐到了沙发的另一端,拿起还有电的平板电脑,似乎打算继续处理工作。
两人之间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沈知意慢慢坐下,将自己缩在沙发角落里,每次雷声滚过,
身体都忍不住轻颤。她紧紧抱住膝盖,努力控制呼吸。陆景珩看着平板屏幕,
却有些心不在焉。眼角的余光能瞥见她苍白的脸和蜷缩的姿态。烛火在她低垂的眼睫上跳跃,
投下颤动的阴影。又一个惊雷仿佛在楼顶炸开,她猛地闭上眼,肩膀瑟缩,像只受惊的幼兽。
沉默在雷雨声中蔓延。只有烛芯偶尔噼啪轻响。过了一会儿,陆景珩忽然起身。
沈知意下意识抬头。他却只是走到储物柜前,拿出一条薄毯,走回来,递给她。“披上。
”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她伸手去接,指尖不经意擦过他的手指。他的手指温热干燥,
带着薄茧;她的确一片冰凉,甚至有些颤抖。两人同时一顿。沈知意飞快地抽回手,
用毯子裹住自己,低声道:“谢谢。”那瞬间的触碰,像一道微弱的电流,窜过她的指尖。
陆景珩收回手,重新坐下,指尖那冰凉柔软的触感却挥之不去。
他瞥了一眼她裹在毯子里仍显得单薄的肩膀,忽然开口,眼睛仍看着平板,
声音在雷雨声中显得有些模糊不清:“怕打雷?”沈知意轻轻“嗯”了一声。“过来。
”他忽然说。沈知意愣住了,以为自己听错了。陆景珩放下平板,转过头看她。
烛光在他深邃的眸子里跳动,映出一些她看不懂的情绪。他朝自己身边的位置抬了抬下巴,
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这边。窗户有缝隙,有风。”他的理由听起来有些牵强。
沈知意心脏怦怦直跳,犹豫着。又一串雷声滚过,她咬了下唇,最终还是抱着毯子,
慢慢挪了过去,在他指定的、距离他大约一臂远的位置坐下。靠近后,
能更清晰地闻到他身上清冽的木质香气,混合着一点点蜡烛燃烧的味道。两人都没有再说话,
但刚才那种紧绷的、独自面对恐惧的感觉,奇异地消散了不少。沉默依旧,却不再冰冷,
反而流淌着一种微妙而难以言喻的氛Χ。雷声渐远,雨势转小,但电力仍未恢复。烛光摇曳,
将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偶尔交叠。不知过了多久,久到沈知意的紧张渐渐放松,
甚至开始有些昏昏欲睡时,远处传来恢复供电的声响。随即,头顶的灯光“唰”地亮起,
瞬间驱散了所有暖昧的昏暗。光明回归,刚才那短暂共处时奇异的感觉也仿佛被照散。
陆景珩立刻站起身,神情恢复了平日的疏淡。“电来了。休息吧。”他走到她的卧室门口,
停下。沈知意跟在他身后,心底那点未散的波澜让她有些无措。他侧过身,看了她一眼。
灯光下,他的眼眸很深,像不见底的寒潭,但此刻,
潭水深处似乎有什么东西轻轻晃动了一下。片刻,他低声说:“晚安。”然后,
他转身走向自己房间。沈知意站在门口,看着他高大的背影消失在主卧门后,才轻轻关上门,
背靠着冰凉的门板。掌心似乎还残留着刚才触碰他手指时的温度,
耳边回响着那声在雷雨声中格外清晰的“晚安”。只是一个意外。只是一句寻常的告别。
可为什么,她的心跳,却久久无法平息?那被烛光和雷雨包裹的短暂时刻,
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散,再也无法回到最初的平静。
第三章:涟漪与决断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那场暴雨夜之后,
沈知意觉得某些东西变得不一样了。陆景珩依旧忙碌,两人见面的时间不多,
但偶尔在早餐桌上,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似乎长了那么一两秒。
他不再提让她换工作室的事,但周延送来的画材和艺术书籍却多了起来,
理由依旧是“合作伙伴赞助,用不上”。沈知意让自己更忙。
她接了一个儿童绘本系列的**插画,稿酬丰厚,周期也紧。她把自己埋进线条和色彩里,
试图用工作填满所有思绪可能飘忽的空隙。然而,有些波澜,并非埋头就能避开。
苏薇回国的消息,像一枚重磅炸弹,投掷进了她努力维持平静的生活。
起初只是财经版和娱乐版边角的零星报道:“著名钢琴家苏薇载誉归国,
或将与国内顶尖乐团合作。”很快,随着苏薇几次高调亮相,
与陆景珩过往的那段“金童玉女”的恋情被重新挖出,大肆渲染。
标题变得暧昧起来:“天才钢琴家回国首秀,恒屿总裁是否会现身捧场?”“破镜重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