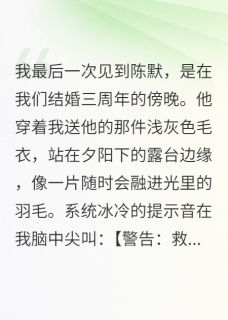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默,是在我们结婚三周年的傍晚。他穿着我送他的那件浅灰色毛衣,
站在夕阳下的露台边缘,像一片随时会融进光里的羽毛。
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在我脑中尖叫:【警告:救赎目标生命体征急剧下降】。我冲过去,
指甲抠进露台的金属栏杆,嘶喊得喉间涌起铁锈味:“陈默!我怀孕了!
你看看这个——”超声影像单在风中猎猎作响,黑白图像里那颗小小的孕囊清晰可见。
他回过头,眼底是一片我从未真正抵达过的、荒芜的寂静海。风吹起他柔软的额发,
他笑了笑,那笑容疲惫又温柔,像一张浸透了水的薄纸。“对不起,阿晚。”他说,
“……还有,谢谢你。”然后,他像一片被风吹落的叶子,悄无声息地坠了下去。没有惊呼,
没有巨响,只有楼下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足以将我整个人生砸得粉碎的钝响。
我的指尖还残留着抓握他衣角时,那件柔软羊毛的触感。系统提示音变成了悠长的忙音,
像某种哀悼。【第七次救赎任务失败。能量严重损耗。
强制重启倒计时:3、2、1——】*眼前刺目的白光散去,
耳边是盛夏特有的、令人烦躁的蝉鸣。粉笔灰在阳光里飞舞,
讲台上数学老师的声音像是从水底传来。我又回来了。高中教室。
肌肉记忆比我的绝望更快苏醒,我的视线第一时间就精准地锁向了那个角落——陈默的座位。
他果然在那里。几个男生正围着他,哄笑着。为首的那个,是陈默继母带来的儿子,赵峥。
他手里拎着一个脏兮兮的拖把桶,浑浊的污水正顺着桶壁滴落,眼看就要朝陈默头上浇去。
前七次,我会像一颗出膛的炮弹,毫不犹豫地冲过去,用尽全身力气推开赵峥,
把瘦弱的陈默护在身后,对着那群施暴者怒目而视,像一只护崽的母兽。每一次,
赵峥都会用那种混合着惊讶、嘲弄和更深恶意的眼神打量我,然后对着陈默嗤笑:“哟,
哑巴玩意儿,又找到新靠山了?这次能靠多久?”每一次,陈默都会在我身后微微颤抖,
湿漉漉的眼睛望着我,里面有劫后余生的惊恐,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微弱的希冀。
那丝希冀,是我七次轮回里唯一的燃料。可现在,这燃料烧尽了我的肝肠,烧死了我的孩子。
拖把桶倾斜的角度越来越大。陈默闭上了眼睛,长长的睫毛在苍白的脸颊上投下脆弱的阴影,
他习惯了,连躲避都是一种徒劳的仪式。他在等待那注定要降临的冰冷和耻辱。
赵峥脸上挂着残忍的快意。这一次,我没有动。心脏像是被冰封了,
又在冰层下裂开无数细碎的纹路。疼,但是一种麻木的、遥远的疼。在赵峥手腕发力,
污水即将泼出的瞬间,我猛地站起了身。桌椅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响声。全班的目光,
包括赵峥和他那群跟班,都聚焦在我身上。陈默也睁开了眼。
那双总是盛着不安和卑微的眼睛里,极其迅速地掠过一丝光亮,像灰烬里最后挣扎的火星。
他看向我,几乎是本能地,向我投来求救的视线。我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零点一秒。
那张清俊、苍白、总是带着伤痕的脸,曾让我无比心痛,无数次发誓要守护。如今,
却只让我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厌倦。我抬腿,没有丝毫犹豫,径直绕过了他。
衣角甚至没有碰到他冰冷的课桌。我走向了赵峥。赵峥脸上的狞笑僵住了,
转而变成错愕和戒备。他大概以为我要来一场激烈的对抗,甚至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我停在他面前,仰头看着这个高大、跋扈、把恶意写在脸上的少年。他的眼神凶悍,
像一头未被驯服的野兽。教室里静得可怕,只有窗外无穷无尽的蝉鸣。我听见自己的声音,
平静得可怕,像结了冰的湖面:“……杀了我。”赵峥瞳孔猛地一缩,
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变成“这人有病”的荒谬感。我没给他嘲笑的机会,继续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清晰地说道:“或者,带我走。”赵峥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那点荒谬感迅速被一种更浓的兴味取代。他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笑话,
夸张地咧开嘴,却没能立刻笑出声。他上下打量我,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我的脸。“顾晚,
”他叫我的名字,声音里带着浓浓的戏谑和探究,“**午睡没醒?还是吃错药了?
演什么苦情戏呢!”我没说话,只是依旧看着他。用我所有的绝望,所有的空洞,
所有七次轮回积累下来的、足以压垮整个世界的疲惫看着他。我的眼神里没有祈求,
没有表演,只有一片死寂的认真。赵峥脸上的嘲弄渐渐挂不住了。他试图与我对视,
但几秒后,他有些狼狈地率先移开了视线,喉结不自然地滚动了一下。
他烦躁地“操”了一声,猛地一脚踹在旁边跟班手里的拖把桶上。“哐当!”铁桶砸在地上,
污水泼了一地,溅湿了几个人的裤脚。“**晦气!没劲!”他恶声恶气地吼道,
像是在驱散某种萦绕不去的诡异气氛,“都滚!散了!”他甩手就要走,经过我身边时,
脚步顿了一下,侧头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最终却什么也没说,
带着一股莫名的火气,撞开教室后门走了。他的跟班们面面相觑,也赶紧溜了。
闹剧突兀地开场,又突兀地收场。教室里鸦雀无声,
只剩下角落里那个浑身湿透、显得更加单薄的身影。陈默还维持着那个微微仰头的姿势,
像一尊被定格的石膏像。他看着我,眼睛里的那点微光早已熄灭,
只剩下全然的茫然和不知所措,还有一丝被彻底遗弃后的、**裸的伤痛。
污水顺着他的发梢、脸颊滑落,像无声的眼泪。他似乎在等待,等待我像过去无数次那样,
走过去,掏出纸巾,轻声安慰他。
我的视线在他那双蒙着水汽、漂亮却无神的眼睛上停留了半秒。
那里面有我七生七世也填不满的黑洞。然后,我面无表情地转过身,走回自己的座位,
拉开椅子坐下。拿出下节课的课本,摊开。动作流畅,没有一丝滞涩。
我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预备铃尖锐地响起,打破了凝固的空气。角落里,
那个身影几不可查地晃动了一下。他始终仰着的头,一点点,一点点地,沉重地垂了下去。
湿透的脊背嶙峋地凸起,像一只被暴雨打湿翅膀、再也飞不起来的鸟。*接下来的几天,
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真空的影子。上课,下课,吃饭,回家。我对周遭的一切失去反应,
包括陈默那日益苍白沉默的身影,也包括赵峥那总是追随着我的、探究又烦躁的视线。
系统偶尔会发出微弱的电流杂音,像是故障的收音机,再没有发布任何任务指令。
也许我彻底摆烂的态度,也让这所谓的“救赎系统”当机了。直到那天下午的体育课。
自由活动时间,我找了个树荫下的角落坐着发呆。篮球场的方向传来喧闹声,
是赵峥他们又在打球。忽然,一阵激烈的推搡和争吵声传来。我抬眼望去,心里猛地一沉。
是陈默。他不知道怎么又惹到了赵峥,
被赵峥和几个篮球队的人推搡着到了操场边缘那个废弃的器材室后面。那是监控死角,
也是赵峥他们惯常“解决问题”的地方。前几次,我会毫不犹豫地冲过去阻止。这一次,
我的**像是被钉在了草地上。一种冰冷的预感攥紧了我的心脏——也许我不插手,
陈默今天就会被赵峥失手打死,或者重伤。那这个轮回是不是就能提前结束?
我这无望的任务是不是就算失败了?我能不能就此解脱?剧烈的心理挣扎让我浑身发冷。
我对陈默的爱和保护欲,经过七次死亡的淬炼,已经变成了某种深入骨髓的本能,
即使我的心死了,我的身体还记得。就在我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几乎要掐出血来时,
我看见赵峥猛地一拳挥出!然而,那一拳却狠狠砸在了陈默耳边的砖墙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赵峥的表情极其狰狞,胸口剧烈起伏,像是在压抑极大的怒火。他对着陈默低吼了句什么,
距离太远听不清,但绝对不是什么好话。然后,他居然没有再继续动手,
只是极其烦躁地一把推开陈默,狠狠唾了一口,带着人走了。陈默顺着墙壁滑坐在地上,
抱着头,肩膀缩成一团。赵峥阴沉着脸,大步流星地朝我这个方向走来。他经过我面前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