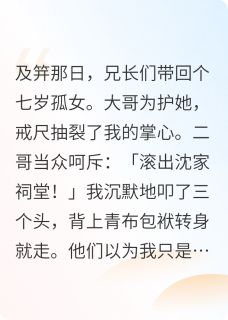
接下来的日子,像沉入一潭冰水,刺骨,却也麻木。
青禾用攒下的月例银子,在城西最偏僻的榆钱胡同赁了个极小的院子,只有两间正屋,墙壁斑驳,院中一口枯井。好在还算干净,遮风挡雪勉强够用。
她变卖了我几件不甚紧要的首饰,又接了些浆洗缝补的活计,日子清苦,却也安静。
我掌心那道被戒尺抽裂的伤口,在青禾小心清洗、敷上廉价的草药后,慢慢结了痂,留下一条扭曲丑陋的暗红疤痕,横贯整个手掌。
每次看到它,祠堂里那声脆响和大哥冰冷失望的眼神,便会在脑中清晰回放。
我把自己关在小屋里,近乎疯狂地翻阅着带来的几本旧书——一本残缺的《九州舆图志》,一本泛黄的《百工纪要》,还有母亲留下的、写满蝇头小楷批注的《脉经》。
指尖划过粗糙的纸页,那些山川河流、机关巧技、经络穴位的图谱与文字,成了唯一能暂时屏蔽掉心底那片荒芜冰原的东西。
青禾有时端了熬好的稀粥进来,看着我对着烛光出神地描摹舆图上的某处关隘,或是反复推演《百工纪要》里某个失传的机括,欲言又止。
最终只是默默放下碗,轻手轻脚地退出去。
日子在清贫与沉默中滑过,转眼便是年关。
爆竹声零星地在远处响起,带着点年节将近的稀薄喜气,却传不进这死水般的小院。腊月二十三,灶王节。
青禾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小块麦芽糖,在冰冷的灶台上勉强熬化了,小心翼翼地粘在灶王爷画像的嘴上。
“姑娘,好歹……甜甜嘴。”她把剩下的一小块糖递给我,眼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期盼。
那粘稠的、带着焦糊味的甜意在舌尖化开,却莫名勾出一股更深的苦涩,直冲鼻腔。我猛地别开脸,喉咙发紧。
就在这时,院门被“砰砰砰”地拍响,急促得像是催命。
青禾脸色一白,下意识看向我。
我定了定神,示意她去开门。
门外站着沈府一个面生的跑腿小厮,裹着厚厚的棉袄,帽子上积了层雪,呼出的白气在寒风中迅速消散。
他递过来一个沉甸甸的锦袋,眼神躲闪,不敢看我:“二、二爷让送来的……说是年节下的份例银子,还有……还有几块料子。”
他飞快地把东西塞到青禾手里,像丢开什么烫手山芋,含糊地补充了一句,“二爷还说……府里新请了江南的厨子,做了好些点心,三姑娘……云袅姑娘吃着很是喜欢……”
后面的话,被呼啸的北风卷走,听不真切了。但那句“云袅姑娘吃着很是喜欢”,却清晰地钉进了耳朵里。
锦袋入手冰凉沉重,里面是硬硬的银锭。
青禾抱着那几匹颜色鲜亮的锦缎,站在风雪里,脸上血色褪尽,嘴唇哆嗦着,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悲愤和无措。
我站在原地,风雪灌进单薄的衣领,冻得骨头缝都在发颤。掌心那道疤,似乎又在隐隐作痛。
二哥沈锐……他是在施舍?还是在提醒我,那个家里如今真正得宠的是谁?
“知道了。”我听见自己毫无波澜的声音响起,“东西放下,你回吧。”
小厮如蒙大赦,飞快地跑了。
青禾抱着东西进来,“哐当”一声关上院门,背靠着门板,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姑娘!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
“这样挺好。”我走过去,从她怀里抽出那几匹锦缎。
触手光滑细腻,是时下闺秀们最爱的云霞锦,一匹价值不菲。
我随手将它们丢在冰冷的土炕上,像丢开一堆碍眼的垃圾。那袋沉甸甸的银子,看也没看。
“收起来吧。总有用得着的时候。”
声音平静,心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透不过气。这银子,这锦缎,像一记无声的耳光,响亮地抽在脸上,比祠堂里那戒尺更疼。
除夕夜,万家灯火。
榆钱胡同的小院里,只有我和青禾两人。炭盆里火苗微弱,勉强驱散一点寒意。桌上摆着两碗素面,飘着几片寡淡的菜叶。
远处沈府的方向,隐约传来丝竹管弦之声,还有模糊的、属于孩童的清脆欢笑声,穿透风雪,丝丝缕缕地飘过来。
是云袅在笑吧?
我捏着粗糙的竹筷,指尖冰凉。碗里素面的热气扑在脸上,带着湿意。
“姑娘,”青禾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试图打破这死寂,“您……您还记得前年除夕,大公子带回来的那个会喷火的西域杂耍班子吗?您当时笑得可开心了……”
她的话戛然而止,像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惊恐地看着我。
我垂下眼,筷子拨弄着碗里糊掉的面条,声音轻得像叹息:“青禾,吃饭。”
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都成了碰不得的毒。一丝一毫,都能引燃那深埋的、足以焚毁一切的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