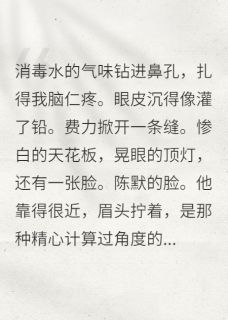
消毒水的气味钻进鼻孔,扎得我脑仁疼。眼皮沉得像灌了铅。费力掀开一条缝。
惨白的天花板,晃眼的顶灯,还有一张脸。陈默的脸。他靠得很近,眉头拧着,
是那种精心计算过角度的担忧,像排练过无数次的舞台剧。“哲思?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他的声音也带着恰到好处的沙哑,仿佛守了我三天三夜。胃里一阵翻搅。不是病,是恶心。
这张脸,这个人,我化成灰都认得。上辈子,就是这张写满“精英”标签的脸,
用温柔陷阱把我套牢,榨干我最后一滴血汗,直到我猝死在凌晨三点的办公桌前。床头柜上,
那份沾了咖啡渍的文件,标题刺眼——《关于黎哲思女士意外身故后的保单受益人确认》。
受益人:陈默。保额:五百万。我的命,就值这个数?在他眼里,
恐怕连他那个**版公文包都不如。“医生说你低血糖,加上疲劳过度。”陈默的手伸过来,
想碰我的额头。我猛地偏开头。他的手僵在半空,眼神里飞快掠过一丝错愕和不悦,
随即又被更深的“关切”覆盖。“吓死我了,哲思。以后别那么拼,项目是公司的,
命是自己的。”他叹口气,语气沉重又无奈,“等你好了,
我替你向张总申请调个轻松点的岗,钱少点没关系,我养你。”“我养你”。上辈子,
就是这三个字,像裹着蜜糖的砒霜。我信了。信了他的“上进”,信了他的“规划”,
信了他描绘的“我们的未来”。我像个永动机,白天黑夜连轴转,
工资全填进我们那个“共同未来”的账户里——那账户,只有他能动。
他穿着我供的高定西装,用着我买的奢侈腕表,出入高端酒会,人模狗样。而我,
穿着过季打折货,挤着末班地铁,吃着便利店冷掉的饭团,支撑着他光鲜亮丽的人设。最后,
用一条命,给他换来五百万的启动资金。**划算。“哲思?”他又唤了一声,
带着点试探的委屈。我没看他,目光扫过病房窗户。窗外,天蓝得晃眼。是夏天。我重生了。
重生在一切悲剧开始加速之前,重生在我还没完全被陈默吸干骨髓的时候。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不是激动,是劫后余生的冰冷愤怒,还有一丝……巨大的茫然。
重活一次,我该干什么?像那些重生爽文女主一样,疯狂打脸渣男,搞事业,走上人生巅峰?
想到“事业”,我只觉得一阵生理性的疲惫排山倒海般袭来。上辈子,我拼得还不够吗?
结果呢?“哲思,你脸色还是不好,再睡会儿吧。”陈默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
“我去给你买点粥。”他起身,背影挺拔,西装没有一丝褶皱。精英范儿十足。我闭上眼。
脑子里却像走马灯一样,闪过另一张脸。模糊的,带着点没心没肺的笑。王旭。
我的……前男友。
一个被陈默鄙夷地称为“烂泥扶不上墙”、“毫无上进心”、“注定社会底层”的男人。
分手,是陈默出现后,我自己提的。那时我觉得陈默说得对。王旭安于现状,
在个半死不活的小公司混日子,租着城中村的房子,
最大的爱好是打游戏和琢磨哪家外卖便宜又大碗。跟着他,能有什么出息?现在想想,
“出息”是什么?是陈默那种踩着别人尸骨往上爬的“出息”吗?
是把自己活成一台赚钱机器最后猝死的“出息”吗?胃里那股恶心感又涌了上来,
伴随着一种尖锐的空洞。重活一世,我他妈不想再要这种“出息”了!我只想喘口气。
只想……像个人一样活着。出院手续是陈默办的,他坚持送我回家。“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他语气温柔,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我的“家”,其实是我们租住的一套高级公寓。
地段好,环境好,租金自然也好——大部分是我付的。电梯镜面映出我和他的身影。
他西装革履,英俊不凡。我穿着洗得发白的病号服,脸色蜡黄,眼底青黑,
像个被吸干了精气的女鬼。真般配。开门进屋。窗明几净,装修简约现代,
是陈默喜欢的“精英品味”。空气里弥漫着他常用的那款昂贵须后水的味道。
以前觉得这味道代表“成功”和“品味”。现在闻着,只觉得呛人,虚伪。“你好好休息,
什么都别想。”陈默把我安置在沙发上,像对待一件易碎品,“厨房我收拾过了,
冰箱里有牛奶和吐司,饿了先垫垫。晚上我给你带‘福记’的养生汤回来。”他俯身,
想给我一个告别吻。我侧过脸。他的唇擦过我的耳廓。动作再次僵住。空气凝固了几秒。
他直起身,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眼神深了些。“好好休息。”他又重复了一遍,
拿起沙发上的公文包,转身离开。门锁“咔哒”一声合上。偌大的空间,只剩下我一个人。
死一般的寂静。上辈子,每次他离开,留下我一个人面对这空旷冰冷的“家”,
我都觉得是理所当然,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奋斗。现在,只觉得这地方像个华丽的坟墓。
我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下方蚂蚁般的车流和行人。阳光刺眼。活着。我真的还活着。
不再是那个倒在冰冷键盘上、连遗言都来不及说的黎哲思。一股难以言喻的冲动攫住了我。
逃离!立刻!马上!离开这个用我的血汗钱堆砌、却让我窒息的地方!离开陈默的掌控范围!
去哪里?一个名字毫无征兆地跳进脑海。王旭。
那个被我嫌弃“没出息”、“咸鱼”的前男友。上辈子分手后,听说他还在那个城中村住着,
干着那份饿不死也撑不着的工作,游戏段位倒是越来越高。咸鱼。这个词此刻在我心里,
不再带有贬义,反而充满了某种……近乎诱惑的安定感。至少,他活得真实。至少,
他不会吸干我的血。行动快过思考。我冲进卧室,拉开衣柜。
里面挂满了符合陈默审美的职业套装和所谓“有质感”的裙子。
我胡乱扯出一个最大的双肩包,抓了几件最舒服的旧T恤和牛仔裤塞进去。动作粗暴,
像是在撕扯某种无形的枷锁。然后,我冲向床头柜,拉开抽屉。
里面躺着我的身份证、几张银行卡,还有……那个我们“共同未来”的联名卡。
我盯着那张联名卡。上辈子,我所有的工资,除了基本生活费,都打进了这张卡。陈默说,
这是为我们买房、结婚准备的“梦想基金”。结果呢?我捏起那张薄薄的卡片,冰凉的触感。
冷笑一声。我把它掰成了两半。清脆的断裂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像某种宣告。
我把断卡扔进抽屉深处,眼不见为净。拿起自己的身份证和工资卡,塞进贴身口袋。
背上那个塞得鼓鼓囊囊的双肩包,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精致冰冷的“家”。头也不回地拉开门,
走了出去。城中村。空气里混杂着油烟、廉价香水和生活垃圾发酵的复杂气味。
狭窄的巷子两旁,是密密麻麻的“握手楼”,电线像蛛网一样在头顶交织。地面湿漉漉的,
不知道是刚下过雨还是泼的脏水。穿着背心裤衩的大爷摇着蒲扇坐在门口,
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格格不入的闯入者。我凭着模糊的记忆,在迷宫般的巷子里穿行。
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累,是一种混杂着陌生、忐忑,还有一丝……破罐子破摔的奇异兴奋。
终于,停在了一栋旧楼前。斑驳的墙壁,铁门锈迹斑斑。楼道里堆着杂物,光线昏暗。三楼,
最里面那间。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股熟悉的、浓郁的酸辣粉味道。抬手,敲门。
“咚咚咚。”里面传来拖鞋趿拉地的声音,由远及近。门开了。
一股更浓烈的酸辣粉味儿扑面而来。门口站着的人,顶着一头睡得乱糟糟的头发,
穿着洗得发白的灰色旧T恤和大裤衩,脚上是双人字拖。他手里还端着一个硕大的塑料碗,
里面是红油汪汪的粉,堆满了炸黄豆和酸豆角。王旭。他明显没睡醒,
眼神迷茫地聚焦在我脸上。几秒钟的呆滞。“噗——”他嘴里叼着的一根粉滑落回碗里,
溅起几滴红油。“黎……黎哲思?”他瞪圆了眼睛,像见了鬼,“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他下意识地想把手里那碗粉藏到身后,动作笨拙又滑稽。“那个……”他有点手足无措,
看看我,又看看自己这身行头,再看看手里那碗过于接地气的粉,
最后目光落在我身后那个巨大的背包上,更困惑了,“你……你这是?”“我无家可归了。
”我看着他,直截了当,声音有点哑,“能收留我几天吗?”王旭的嘴张得更大了,
能塞进一个鸡蛋。他看看我苍白的脸,又看看我身后那个鼓鼓囊囊、显得我更加单薄的背包,
眼神里的困惑慢慢被一种巨大的震惊和难以置信取代。“你……”他咽了口唾沫,
艰难地组织语言,“你跟陈默……吵架了?他欺负你了?”“分手了。”我吐出三个字,
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分……分手?!”王旭的声音陡然拔高,差点破音。
手里的酸辣粉碗也跟着晃了晃,汤汁差点泼出来。他手忙脚乱地稳住碗,眼睛瞪得溜圆,
死死盯着我,仿佛想从我脸上找出开玩笑的痕迹。“你……你认真的?”他结结巴巴地问,
“黎哲思,你脑子……被陈默气糊涂了?”我没回答,只是看着他。眼神疲惫,但很平静。
王旭脸上的震惊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的茫然和不知所措。
他抓了抓自己那头乱毛,又看看狭窄杂乱的楼道,
再看看我身上与这里格格不入的气息(尽管我穿着最旧的衣服)。
“我这儿……”他艰难地开口,声音干涩,“我这儿……太乱了,也太小了,
就一个单间……你住不惯的。”他试图劝退我,“真的,黎哲思,别赌气。
陈默他……条件那么好,你们……”“他条件好是他的事。”我打断他,声音不高,
但很清晰,“我就问你,王旭,你这地方,能让我暂时落脚吗?付你房租。
”王旭被我噎住了。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得像一团乱麻。有不解,有担忧,有习惯性的退缩,
似乎还有一丝……被我强硬态度激起的微弱反抗?他沉默了几秒,
像是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肩膀垮了下去,像是认命地叹了口气。
“行吧行吧……”他侧开身,让出门口的位置,语气带着点破罐破摔的无奈,“先说好,
我这狗窝,你别嫌弃。进来吧,大**。”他嘟囔着,转身往里走,
不忘小心翼翼地护着他那碗酸辣粉。我跟着他走进门。
一股混合着方便面、汗味、灰尘和淡淡烟味的气息扑面而来。房间很小,一眼就能望到头。
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被子没叠,皱成一团。床边是一张旧电脑桌,
上面放着个嗡嗡作响的旧电脑主机,屏幕还亮着游戏画面。桌子旁的地上,
堆着几桶吃空的泡面盒和几个捏扁的啤酒罐。唯一的“家具”大概就是墙角那个简易布衣柜,
拉链半开着,露出里面塞得乱七八糟的衣服。整个空间,
用一个词形容:乱中有序的……狗窝。王旭把酸辣粉碗放在电脑桌唯一还算干净的小角落,
手忙脚乱地去扯床上那团被子,试图把它叠得方正一点,结果越扯越乱。
他又想去踢开地上的泡面桶,动作笨拙。“别忙了。”我出声,把背包卸下来,
放在门口相对干净的地上,“就这样吧。”他停下动作,有些尴尬地看着我,
搓了搓手:“真……真住这儿?你受得了?”我没回答,目光扫过那张唯一的单人床。
王旭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脸腾地一下红了,结巴得更厉害:“你你你睡床!我我我打地铺!
我有凉席!”他几乎是窜到墙角,从一堆杂物里扒拉出一张看起来还算干净的草席,
又翻出一床薄毯。动作麻利得跟他平时慢悠悠的性子截然不同。“饿吗?”他铺好地铺,
直起身,指了指桌上那碗粉,“刚叫的外卖,
还没动几口……你要是不嫌弃……”我看着那碗红油赤酱、卖相粗犷的酸辣粉。
上辈子跟着陈默,出入高级餐厅,讲究营养均衡,精致摆盘,却吃得味同嚼蜡。
胃里适时地发出一阵空鸣。“有筷子吗?”我问。王旭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
赶紧去翻桌下的塑料袋,找出一双一次性筷子递给我,还细心地掰开了。我接过筷子,
走到电脑桌前,拉过唯一一张塑料凳坐下。端起那碗还温热的酸辣粉。
浓郁的酸辣味直冲鼻腔,带着一种粗粝的、鲜活的生命力。我夹起一大筷子,吸溜进嘴里。
酸、辣、烫!豆角的脆爽,黄豆的酥香,粉条的滑韧,还有那霸道直接的味道,
瞬间在口腔里炸开。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却有一种久违的、活着的痛**。
“咳……咳咳……”我呛咳着,眼泪汪汪。“哎!慢点慢点!”王旭吓了一跳,
赶紧去拿桌上那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太辣了?喝口水!”我没接水,
只是又夹了一筷子塞进嘴里,用力嚼着。眼泪流得更凶了。王旭站在旁边,
手足无措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不解。“黎哲思……你……你没事吧?
”他小心翼翼地问。我咽下嘴里的粉,抹了把脸,分不清是辣的还是别的什么。“没事。
”我吸了吸鼻子,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好吃。”王旭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
再看看我脸上未干的泪痕,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他默默地走到墙角,拿起扫帚,
开始笨拙地清理地上的泡面桶和啤酒罐。动作很轻,怕吵到我。
房间里只剩下我吸溜粉条的声音,和他扫地的沙沙声。城中村的日子,像被按下了慢放键。
没有没完没了的电话会议,没有凌晨响起的项目群消息,
没有陈默那张时刻提醒你“要上进”、“要规划”的脸。只有窗外永远嘈杂的人声车声,
隔壁租客夫妻时不时的争吵,还有王旭电脑里传来的、噼里啪啦的游戏音效。
我睡了重生以来第一个自然醒的懒觉。没有闹钟,没有KPI追魂。阳光透过蒙尘的窗户,
斜斜地照在脸上。睁开眼,看到的是天花板上剥落的墙皮,还有一只慢悠悠爬过的小壁虎。
很陌生。但……不讨厌。王旭已经醒了,正坐在地铺上,背对着我,戴着耳机,
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的电脑屏幕打游戏。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发出密集的哒哒声。
他穿着那件万年不变的旧T恤,背影看起来有点单薄。我没打扰他。起身,
走到那个小小的、油腻腻的洗手间洗漱。镜子里的脸,依旧没什么血色,
但眼底那层浓重的青黑似乎淡了一点点。洗漱完出来,王旭刚好结束了一局,摘下耳机,
长长舒了口气,转过头。“醒了?”他问,语气很自然,好像我住在这里是天经地义的事,
“饿不饿?我叫外卖?还是……出去吃?”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自己做吧。
”我说。王旭动作一顿,表情有点僵:“做?做……什么?”“有什么做什么。
到那个狭小的、只够一个人转身的“厨房”区域——其实就是窗边用一块板子搭起来的台子,
上面放着一个电磁炉和一个旧电饭锅。我拉开那个小小的、漆皮剥落的冰箱门。
里面东西不多:几个鸡蛋,一把蔫了吧唧的小白菜,半根火腿肠,还有两包速冻饺子。寒酸,
但真实。“煮面?”我拿出鸡蛋和小白菜。“啊?哦……行,行啊。”王旭挠挠头,
有点局促地凑过来,“我……我来洗菜?”“嗯。”他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
他笨手笨脚地把小白菜叶子掰开,在水下面冲洗。动作生疏,一看就不常干这个。
我找出一个小奶锅,接了水放在电磁炉上烧着。狭小的空间里,两个人挤在一起,
胳膊偶尔会碰到。谁也没说话。只有水流声,锅里的水开始冒泡的咕嘟声。
气氛有点微妙的尴尬。水开了。我把面条下进去,用筷子搅散。王旭终于洗好了菜,
湿淋淋地递过来,水珠滴在地上。我接过,撕成几段,丢进锅里。又打了两个鸡蛋进去。
蛋液在滚水里迅速凝固,变成白色的蛋花。最后,切了那半根火腿肠,丢进去。没有油,
没有复杂的调味,只撒了点盐和味精。清汤寡水的一锅面。盛在两个大碗里。端到电脑桌上,
塑料凳只有一张。王旭很自觉地拖过他的游戏椅给我坐,自己坐在了地铺边缘。
我们各自捧着碗,埋头吃面。面条煮得有点软,鸡蛋有点老,小白菜煮黄了,
火腿肠一股淀粉味。味道实在算不上好。但热乎乎的,能填饱肚子。我吃得很快。
王旭偷瞄了我几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忍住,
小声问:“黎哲思……你真打算……一直住这儿?”我放下碗,看着他:“嫌我占地方了?
”“不不不!绝对没有!”王旭连忙摆手,差点把碗打翻,
“我就是……就是觉得……你这条件,住这儿太委屈了。陈默他……”“别提他。
”我打断他,语气没什么起伏,“我住这儿,付房租。不会白吃白住你的。
”王旭被我堵得没话说,低下头,用筷子搅着碗里剩下的面汤,
嘟囔了一句:“谁要你房租了……”“要的。”我语气坚决,“亲兄弟明算账。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最终闷闷地“嗯”了一声。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我像一条真正的咸鱼,彻底躺平。大部分时间在发呆,看窗外晾衣杆上随风飘荡的衣服,
看楼下小贩推着车叫卖。偶尔用手机刷刷招聘网站,
看到那些要求“抗压能力强”、“接受996”、“狼性团队”的描述,就生理性反胃,
立刻关掉。王旭依旧上着他那份朝九晚五(偶尔加班)、工资不高但清闲的工作。
下班回来就打游戏,或者看动漫。他不问我为什么突然分手,为什么赖在他这里。
我也懒得解释。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他打他的游戏,我看我的天。他叫外卖,
会习惯性地问我要吃什么。我偶尔会去楼下买点简单的菜,煮个面或者煮锅粥。
味道依旧不怎么样,但王旭每次都吃得很干净。他好像……比上辈子印象中更安静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