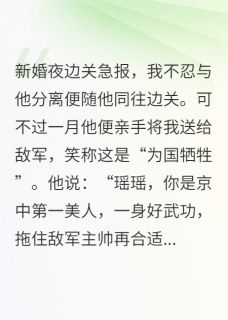
新婚夜边关急报,我不忍与他分离便随他同往边关。可不过一月他便亲手将我送给敌军,
笑称这是“为国牺牲”。他说:“瑶瑶,你是京中第一美人,一身好武功,
拖住敌军主帅再合适不过,等我加官进爵,定风风光光接你回来。”那一刻,我才看清,
青梅竹马的海誓山盟,抵不过他青云路上的一枚踏脚石。他骗我吃软骨散,毁我武功,
连他口口声声的“义子”,都是他与我“好妹妹”的骨肉!可他们算错了一点。
敌营那位传闻中的“杀神”王子,竟比我的枕边人更懂尊重。他解开我的镣铐,
递给我匕首:“伤好了,去留随你。”后来他跪在我面前哭红眼:“瑶瑶,跟我回去!
我是爱你的!”我冷笑着举起长枪:“你的爱,只配用血来偿!”—1—卫霖霄的话音刚落,
帐内的烛火像是被寒风卷过,猛地窜起半尺高。我盯着他年轻却冷硬的侧脸,
耳边的金戈铁马声仿佛都消失了,只剩下自己心脏擂鼓般的轰鸣,一下重过一下,
震得耳膜生疼。“你说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指尖死死攥着腰间的玉佩。
那是我及笄时他亲手雕刻的,上面还刻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小字。他转过身,
玄色的将军铠甲上还沾着未干的血渍,映得那双曾盛满星辰的眼睛格外陌生。“我说,
把你送给敌军主帅。”他重复得干脆利落,仿佛在说今日的军粮该加多少,
“章邯那边传来消息,敌军首领是个好色之徒,你是京中第一美人,送去谈和再合适不过。
”我踉跄着后退半步,撞到身后的案几,上面的青瓷茶杯“哐当”一声摔在地上,
碎裂声像极了我此刻的心。一个月前的大婚之夜,红烛高燃,他握着我的手说“瑶瑶,
等我击退敌军,便奏请圣上赐你为唯一的妻,再不要什么三妻四妾”。那时他眼里的郑重,
此刻想来竟比戏文还要虚假。“合适?”我笑出声,眼泪却先一步滚了下来,“卫霖霄,
你告诉我,什么叫合适?是合适把你新婚一个月的妻子,
送去给那些烧杀抢掠的蛮夷当玩物吗?”他皱起眉,像是不耐烦我的纠缠:“瑶瑶,你不懂,
如今我军节节败退,再不想办法,整个北境都会生灵涂炭,你牺牲一下,换两军和平,
是大功一件。”“牺牲?”我逼近一步,胸口的怒火几乎要将我焚毁,“你说的牺牲,
就是把我推出去?你忘了我们自小在国子监读书时,你说过要护我一生周全?
你忘了大婚那日,对着天地起誓说此生绝不负我?”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眼神闪烁了瞬,
随即又恢复了那副大义凛然的模样:“家国面前,儿女私情算得了什么?
”他伸手想碰我的脸,被我狠狠挥开。“况且,你不仅貌美,还有一身好武功。
”“到了敌军营中,只需用些手段拖住他们,我这边整顿好兵力,里应外合定能大胜。
”“到时候我加官进爵,便风风光光把你接回来,往后定好好补偿你。
”我看着他眉飞色舞地描绘着功成名就的蓝图,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原来那些年的青梅竹马,那些海誓山盟,在他眼里竟抵不过一顶官帽。敌军若真是蠢笨如猪,
怎会让他一路溃败至此?他哪里是想救我,不过是想用我的命,铺就他的青云路。“卫霖霄,
”我抹掉眼泪,声音冷得像帐外的冰雪,“你做梦。”他脸上的温情瞬间褪去,
换上了我从未见过的狠戾:“由不得你。”话音未落,帐外便冲进来两个膀大腰圆的士兵。
我下意识地想去拔腰间的软剑,却发现不知何时剑鞘已空。卫霖霄站在原地,
冷冷地看着他们将我按住。“把她关起来,”他背过身去,声音没有一丝温度,
“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再给她吃喝。”冰冷的绳索捆住了我的手腕,
粗糙的麻绳磨得皮肤生疼。我被拖拽着穿过营房,那些曾对我恭敬行礼的士兵,
此刻都低着头不敢看我。最后我被扔进一间阴暗潮湿的营帐,
沉重的木门“吱呀”一声落了锁。帐内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我蜷缩在床角。
原来从始至终,我都只是他权衡利弊时,可以随时舍弃的棋子。京中第一美人的名号,
自幼习得的武功,甚至那些年的情分,到头来,都成了他算计我的筹码。我望着帐顶的破洞,
月光从那里漏下来,像一把冰冷的刀,剖开了所有温情脉脉的假象。
—2—喉咙干得像要裂开。第二日晚上,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卫霖霄的身影逆着光站在那里,手里提着食盒,那点昏黄的光勾勒出他挺拔的轮廓,
可在我眼中,却只剩狰狞。“瑶瑶,”他走近几步,声音温柔得能滴出水来,
仿佛前日那个冷酷决绝的人不是他,“我知道你受苦了,这都是不得已。
”他将食盒放在地上,打开,
里面是精致的糕点和一碗热气腾腾的汤:“我怎么舍得让你受委屈?
你是我放在心尖上的人啊。”我冷冷地看着他,不发一语。他又往前凑了凑,
眼中满是“深情”,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恳求。“瑶瑶,你我青梅竹马,
这么多年的情分,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吗?”“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局。”“若你真的爱我,
就该为我牺牲这一次,就当是帮帮我,好不好?”那眼神太过真挚,恍惚间,
我似乎看到了年少时那个为我摘花、替我解围的少年。可下一秒,
他要将我送给敌军的话语又在耳边炸开,我猛地回神,心中只剩冰冷的嘲讽。“你的爱,
就是把我推出去当筹码?”我声音嘶哑,却带着刺骨的寒意。他脸上闪过一丝受伤,
随即又换上温柔的表情,拿起一块糕点递到我嘴边。“瑶瑶,先吃东西,你看你都瘦了多少,
我心疼。”他软声软语地哄着,“不管怎样,身体是要紧的。”或许是太过饥饿,
或许是心底那点残存的念想作祟,我竟鬼使神差地张开了嘴。糕点入口即化,
可还没等我品味出味道,四肢百骸瞬间变得无力。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看向卫霖霄。
他脸上的温柔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漠和算计,
嘴角甚至勾起一抹嘲讽的笑。“别怪我,瑶瑶。”他收回手,拍了拍上面的碎屑,
“留着你的武功,总是个麻烦。”“你……”我想质问,却发现连说话都变得费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好好等着吧,”他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等我和敌军商议好,
就送你过去,放心,到时候会给你解药的。”转而,他又换上那副深情的模样,叹了口气。
“瑶瑶,你要理解我,我太难了。”“敌军势大,我若不这样做,整个军队都可能覆灭。
”“等这一切结束,我保证,绝不会让你受一丝委屈,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
”委屈?我简直要笑出声来。现在把我关在这的是他。骗我吃下让我武功尽失的东西是他。
说要将我关到敌军军营中受辱,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正是他吗?他所谓的不委屈,
不过是建立在我忍辱负重的基础上,满足他的野心罢了。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心中最后一点对过往的眷恋也彻底熄灭。卫霖霄,你我之间,到此为止了。
—3—锁链再次哗啦作响时,我以为是卫霖霄去而复返。眼皮重得像坠了铅,
刚勉强掀起一条缝,就见个穿小兵服的身影逆光走来,脚步轻得不像常年练过武的汉子。
他停在几步外,抬手摘下头盔的动作带着几分刻意的优雅,青丝如瀑垂落肩头的瞬间,
我看清来人竟是颜巧云。她捏着我的下巴迫使我抬头。“姐姐还真是天真。
”她笑起来时眼角的梨涡和小时候一模一样,语气却淬了毒,“以为嫁给他就是赢家了?
如今还不是要被打包送给敌军当玩物?”我盯着她腕间那只缠枝莲银镯,
那是去年我亲手给她打的及笄礼。“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她俯下身,
“从他第一次上战场起,陪在他身边的就是我。”“不像姐姐,
只会躲在京城等着当将军夫人。”她忽然压低声音,热气喷在我脸上,“哦对了,
忘了告诉你,我上个月刚给他生了个儿子,眉眼像极了他。
”“儿子”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我心上。我猛地想起去年宫宴,她摔倒在卫霖霄怀里时,
他慌忙扶她的样子。当时他笑着解释“巧云毛手毛脚的”,我竟还笑着打趣他们兄妹情深。
“你以为他为什么总对我挑三拣四?”颜巧云用帕子慢条斯理擦着指甲,
“那是做给你看的呀。”“姐姐你家手握兵权,圣上又念着你父兄战死的情分不肯收回,
他不娶你,怎么名正言顺拿到那些兵权?”原来如此。那些年他对我的好,对我的誓言,
不过是冲着阮家的兵权。我想起父兄灵前,他攥着我的手说“瑶瑶别怕,以后我护着你”,
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在腐烂。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颜巧云突然狠狠扇了自己两耳光,
发髻散乱地跌坐在地。卫霖霄冲进来时,她立刻扑进他怀里哭道:“霖霄哥哥,
我只是想来劝劝姐姐,她怎么就打我……”卫霖霄的目光像淬了冰,
一把将我从地上拽起来甩到墙上。“阮乐瑶!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敢动她?
”后背撞在石壁上的剧痛让我眼前发黑,我咳着血笑出声:“我……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怎么打她?”他动作顿了顿,眼里闪过一丝犹豫,却很快被颜巧云的哭声淹没。“你闭嘴!
”他一脚踹在我膝弯,我“咚”地跪倒在地,“等把你送给敌军,我再慢慢算这笔账!
”他抱着颜巧云转身离去时,我望着他们交缠的身影,
突然想不起少年时那个替我摘槐花的卫霖霄长什么模样了。我们三人一起爬过的那棵老槐树,
他刻在树干上“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字迹,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场针对我的骗局。
爱了十几年的人,护了十几年的“妹妹”,联手给了我最狠的一刀。这世上,
再没有比我更蠢的人了。—4—小兵端着食盘进来时,木栏碰撞的声响格外刺耳。
他将青瓷碗重重搁在地上,粗粝的嗓音裹着谄媚的笑:“将军说了,
送您去敌军前可得养着这张脸,别辜负了京中第一美人的名头。
”我盯着碗里飘着油花的米粥,胃里一阵翻涌。“说起来将军真是大义,
”他蹲下身用袖子擦着碗沿,语气里满是推崇,“今儿刚收了义子办满月宴,
营里都在喝喜酒呢,连自个儿夫人都舍得送去议和,这等胸怀,难怪能当将军。”义子?
我扯了扯嘴角,血腥味又漫上舌尖。那分明是他和颜巧云的骨肉,
偏要披上“义子”的外衣自欺欺人。所谓大义,原来就是把发妻当贡品,
踩着我的清白去换他的功名利禄。第三日傍晚,卫霖霄踏着暮色而来。他身上还带着酒气,
玄色披风上沾着未干的酒渍。“瑶瑶,”他蹲下来握住我戴着手镣的手腕,
指腹摩挲着冰凉的金属,“那日踢你是我不对,近来战事吃紧,
我实在……”我别开脸不愿看他,他眼中的红血丝倒像是真的,可那点疲惫在我看来,
不过是权衡利弊后的惺惺作态。“来人,带夫人去梳洗。”他扬声唤道,
语气恢复了平日的沉稳。走进营帐时,颜巧云正坐在铜镜前描眉。她看见我被侍卫架着进来,
放下眉笔起身,笑盈盈地执起一把桃木梳:“姐姐,妹妹来替你梳妆。
”木梳**发丝的瞬间,她猛地向后一扯。头皮传来撕裂般的痛,我踉跄着差点摔倒,
却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软骨散的药性还没过去,四肢软得像棉花。“姐姐忍着些,
”她凑近我耳边,声音甜得发腻,“这发式可是敌军主帅最爱的样子呢。
”穿那件石榴红舞衣时,针尖猝不及防扎进腰侧。我闷哼一声,她却笑得更欢:“哎呀,
手滑了。”银簪簪进发髻时,她故意偏了半寸,尖锐的簪尖刺进头皮,
温热的血顺着鬓角往下淌。我望着铜镜里那个面色惨白、发丝凌乱的人影,忽然觉得陌生。
这就是京中人人称羡的阮乐瑶吗?被人剜了心,断了骨,还要被打扮成祭品,
送到虎狼窝里去。出营门时,暮色已染透天边。卫霖霄站在辕门外,玄甲在残阳下泛着冷光。
他伸手拂去我颊边的一缕乱发,指尖的温度烫得我发抖。“等我。”他望着我的眼睛,
那里面又盛起熟悉的深情,仿佛前几日踢我在地的人不是他,“最多三个月,
我一定接你回来。”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身后营地里飘起的炊烟。
那里正在为他的“义子”庆贺满月,而他的发妻,正被他亲手送往敌军营中。
风卷起我的裙角,带着塞外凛冽的寒意。卫霖霄,你我之间,早就不必等了。
—5—雕花窗棂外传来胡笳声,我攥着发钗的指节泛白,指腹被冰凉的金属硌出红痕。
这房间铺着波斯地毯,鎏金烛台燃着西域香料,处处透着奢靡,却比卫霖霄的地牢更像牢笼。
门轴转动的轻响惊得我猛地站起,发钗尖对准来人。却在看清他模样时愣住了。
玄色锦袍上绣着暗纹银线,男子缓步走来时衣袂翩跹,
竟比京中最负盛名的戏子还要俊秀几分。他眉眼间带着疏离的笑意,
目光扫过我紧握发钗的手,忽然嗤笑一声:“卫霖霄倒是舍得,把你这样的美人送来做筹码。
”我心头一紧,这人竟连卫霖霄的名字都直呼其名。“议和不是因为我们怕了他,
”他在紫檀木椅上坐下,指尖叩着桌面,声音清润如玉石相击,“北疆百姓早已厌战,
再打下去,只会尸横遍野。”他抬眼望我,眸色深邃:“我苍文昊虽被你们称为杀神,
却也知道,真正的胜仗从不是靠抢来的。”苍文昊?我手中的发钗“当啷”落地。
爹爹生前常提起这个名字,说北境有位将军,用兵如神却从不屠城,对待降兵也格外宽厚。
那时我只当是爹爹对敌手的客套称赞,却没想过“杀神”竟是这般模样。他忽然起身走近,
目光落在我手腕的镣铐印上。“传军医。”他扬声吩咐门外侍卫,语气陡然冷厉,
“取库房里的雪玉膏来。”侍卫应声而去时,他拾起地上的发钗,
指尖捻着钗尾的珍珠:“打算用这个自尽?”我别开脸不说话,喉间却有些发涩。
他忽然将一样东西扔到我怀里,沉甸甸的触感让我低头去看。竟是一把镶嵌着宝石的匕首,
鞘上的狼头纹栩栩如生。“卫霖霄用软筋散伤你,我不做那等龌龊事。”他转身走向窗边,
“等你伤好了,想走想留全凭你意,这府邸你随便出入,没人敢拦你。”军医来上药时,
我望着苍文昊离去的背影,忽然想起卫霖霄送我出营时说的“等我”。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酸意混着愧意涌上来。方才我竟以为他要用糖衣炮弹算计我,
倒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雪玉膏触到伤口时微凉,却奇异地缓解了疼痛。
我抚着腕间的药膏,忽然明白爹爹为何会对苍文昊有敬意。这北境的将军,
竟比我那同床共枕的夫君,更懂何为尊重。—6—小丫头捧着食盒进来时,
辫子上还别着朵小雏菊。她边摆碗筷边絮絮叨叨:“王子今早又去校场了,
听说练了两个时辰的剑呢。”我握着青瓷杯的手顿了顿:“你说……王子?”“是啊,
”她眨着圆眼睛,夹了块芙蓉糕放进我碟中,“苍文昊王子呀,咱们王最疼的小儿子,
前阵子又瞒着身份去前线,王都快气病了呢。”我望着窗外开得正盛的紫藤花,
指尖微微发颤。原来他不是敌军主帅,竟是北漠的王子。
那个被京中传言成杀人如麻的“杀神”,此刻想来,
眉眼间的温润倒比卫霖霄多了几分真性情。午后转去花园时,远远就听见低低的狼嗥。
绕过假山,正见苍文昊蹲在廊下,手里端着个铜盆,指尖漫不经心地梳理着一头雪狼的鬃毛。
那狼足有半人高,獠牙外露,在他手下却乖得像只猫。我爹当年镇守边关,
我自小见惯了猎场猛兽,倒不至于惊慌,只是在王府里养狼,终究是惊世骇俗。他闻声抬头,
玄色常服衬得肤色愈发白皙。“伤势好些了?”他语气平淡,像在问寻常的客人。
“劳王子挂心,已无大碍。”我福了福身,目光忍不住又落回那雪狼身上。
“这里不比京城精致,”他起身时,雪狼蹭了蹭他的手腕,“住得不习惯就说,
能办的都会办。”话音未落,我已忍不住伸出手。那狼通人性似的,歪头看了我一眼。
苍文昊想开口阻止,我指尖已触到了它的鬃毛,柔软得像上好的绸缎。变故只在一瞬。
雪狼猛地甩头,尖利的爪子扫过我的手背,几道血痕立刻渗出血珠。“阿雪!
”苍文昊低喝一声,迅速抓住狼的项圈。他转头看向我,眉头紧蹙,
竟亲自从怀中掏出手帕按住我的伤口,“愣着做什么?去叫大夫!”侍卫慌忙跑开时,
他正用清水仔细冲洗我的伤口。“北漠的狼野得很,认生。”他抬头看我,
眼中带着几分歉意,“委屈你了。”冰凉的帕子贴着皮肤,我却忽然想起去年在围场,
我被马蜂蛰了手背,卫霖霄只是皱着眉说:“多大点事,忍忍就过去了,
武将家的女儿哪能这么娇气。”那时我还觉得他说的是理,
如今被苍文昊冰凉的指尖触到伤口,才惊觉有些疼,本就该被人放在心上疼惜的。
雪狼在一旁呜咽着蹭他的裤腿,他拍了拍狼头,抬眼看向我时,目光温和:“伤口别碰水,
大夫很快就到。”我望着他转身吩咐侍卫的背影,忽然觉得这北漠的风,
似乎也没那么刺骨了。—7—小丫头的指尖沾着清凉的膏药,在我手背的伤口上轻轻打圈。
“王子特意吩咐了,这药膏是西域来的珍品,保证不会留疤。”她边说边抬眼,
笑得眉眼弯弯,“您瞧,这一箱子绫罗绸缎,还有那些珠钗玉器,都是王子让人送来的呢,
他说不知京中女子喜好什么,让您随便挑着解闷。”我望着桌上堆得像小山似的物件,
喉头有些发紧。这些东西,比卫霖霄成婚时送我的聘礼还要精致。
傍晚的风带着花香掠过回廊,我循着兵刃相接的脆响走到花园,正见苍文昊挥剑劈向木桩。
玄色劲装衬得他肩背挺直,剑光在暮色里划出银弧,竟有种惊心动魄的美。他见我来,
手腕轻转收了剑,额角的汗珠顺着下颌线滑落。“不必如此费心。”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没头没脑,声音轻得像风,“我不过是……”“不过是卫霖霄送来的棋子?
”他接过下人递来的帕子擦汗,语气听不出喜怒,“还是觉得我别有居心?
”我抬头撞进他的眼睛,那里澄澈得像未被惊扰的湖面,坦然得让我自惭形秽。
正要开口辩解,他却先笑了:“听闻阮**功夫不错,京中罕有对手。”他将长剑递给随从,
“等你伤好了,不如切磋一二?”话音刚落,就有下人匆匆来报:“王子,府外有乞儿乞讨。
”苍文昊挑眉,竟亲自迈步向外走。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站在朱漆大门后,
看着他蹲在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面前,声音放得极柔:“饿了吧?
”他命人取来刚出炉的肉包,又从钱袋里摸出几锭银子塞进孩子手里。
那两个孩子怯生生地接过,他还笑着揉了揉其中一个的头。“王子一直这样。
”小丫头在我身边轻声说,“府外的乞丐总来,谁都知道王府心善,说不定有一半是假的呢,
可他每次都亲自来看,该给的从不少。”我望着苍文昊转身回来的背影,
忽然想起随卫霖霄来边关的路上。那时也遇到个乞讨的老婆婆,我刚要递出干粮,
就被他一把攥住手腕。“粮草紧张,”他皱眉看着那老婆婆,语气冷硬,
“谁知道是不是敌军派来的细作?”冷风卷着暮色穿过门廊,我拢了拢衣袖。
原来同是身处边关,有人把百姓当筹码,有人却把百姓放进了心里。苍文昊走过我身边时,
见我望着府外发怔,随口问:“怎么了?”“没什么。”我低下头,掩去眼底的涩意,
“只是觉得……这里和我想的不一样。”他轻笑一声,没再追问,转身往内院走去。
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青石板上,竟有种说不出的安稳。
—8—小丫头推着我往书房去时,食盒里的桂花糕还带着余温。
她笑得眼睛弯成月牙:“王子见了姐姐亲手做的点心,定会高兴的。”我却攥紧了食盒提手,
指尖微微发颤。这半月来山珍海味从未断过,可亲手做吃食送人,竟是头一遭。
推开书房门时,苍文昊正坐在矮案前用餐。夕阳从雕花木窗漏进来,
恰好落在他面前的陶碗上,里面是糙米饭配着两碟青菜,连点荤腥都不见。
我站在门口忽然僵住,食盒里的芙蓉鱼片、翡翠虾饺仿佛在灼烧我的掌心。“愣着做什么?
”他抬头看过来,嘴角噙着浅淡的笑意,“闻着挺香。”我把食盒放在案上,
揭开盖子的手有些不稳:“略备了些点心,不成敬意。”他竟直接拿起一块桂花糕放进嘴里,
咀嚼时眼神清亮:“手艺不错。”丝毫没有顾忌吃食里会不会有问题,坦荡得让我心头一震。
当年在京中学厨艺时,母亲总笑我:“将来嫁了卫霖霄,总不能让他日日吃军营冷食。
”那时我想着红烛帐暖,为心上人洗手作羹汤是何等惬意,何曾想过,第一次亲手做的吃食,
竟是送到了敌军王子面前。“你的饮食……”我终究还是没忍住,目光扫过那碗糙米饭,
“为何如此素净?”他放下糕点,用帕子擦了擦指尖:“城中百姓尚有断炊的,
我怎能独自奢靡?”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日天气,“粮草本就该先紧着守城的兵士和百姓,
王族的体面,远不如他们的温饱重要。”我怔在原地,
忽然想起卫霖霄营中那桌满月宴的酒肉,想起他为了“义子”大摆宴席时,
帐外还有士兵啃着冻硬的麦饼。苍文昊见我不语,又拿起一块虾饺:“你若吃不惯吃食,
明日让厨房多换些花样便是。”食盒里的热气渐渐散去,我望着他平静的侧脸,
突然明白父亲当年为何提起他时,语气里满是敬意。所谓杀神,原来并非嗜杀成性,
而是把百姓放在了最前头。而我倾心十几年的卫霖霄,却连施舍一个乞儿都要算计利弊。
我垂下眼睫,掩去眸中的涩意:“不必了,现在的饮食,很好。
”—9—小丫头将我的话传给苍文昊时,我正坐在窗前看月光穿过梧桐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