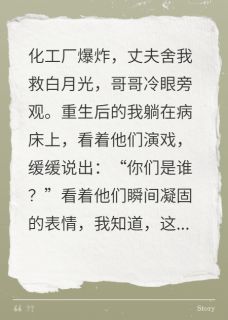
化工厂爆炸,丈夫舍我救白月光,哥哥冷眼旁观。重生后的我躺在病床上,看着他们演戏,
缓缓说出:“你们是谁?”看着他们瞬间凝固的表情,我知道,这场好戏该换我来导了,
他们都得疯!1我重生在了我的“死期”前一个月。上一世,就在今天,
我作为虞氏集团准继承人,主持人生中最重要的股东大会时,旗下的化工厂突然爆炸。
我的丈夫傅砚舟,在火光和气浪袭来的瞬间,像忘记了我的存在,疯了一样扑过去,
将他那前来送文件的白月光初恋纪清蕊,死死地护在身下。我被失控的设备砸断双腿。
在医院的无菌病房里,我隔着一层玻璃,亲耳听到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敲定了我的末日。我的丈夫傅砚舟,那个靠着和我联姻才坐稳CEO位置的凤凰男,
语气冰冷得像手术刀:「舆论已经压下去了,没人会查到爆炸是我们故意制造的安全疏漏。」
我的亲哥哥虞铮,那个从小把我捧在手心的男人,
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但晚晚的腿……砚舟,让一个医生在手术里动了手脚,
让她这辈子都站不起来,是不是太狠了?」「狠?」傅砚舟嗤笑一声,「虞铮,
你难道不清楚**妹的性格?骄傲、强势,不肯输。让她完好无损地把虞家的一切,
心甘情愿地让给清蕊未出世的孩子,你觉得她会点头吗?」「只有让她彻底变成一个残废,
一个必须仰仗我们鼻息才能活下去的废物,她才会明白什么叫‘认命’。我们这是为了她好,
也是为了清蕊好。」「清蕊……当初为了救我,勇敢地站出来给我换血,差点丢了性命。
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我躺在ICU里,全身麻痹,只有眼泪像岩浆一样,
灼烧着我的太阳穴。好一个「为了我好」。好一个「勇敢献身」。原来,
我才是那块他们通往康庄大道的垫脚石。需要我时,我是虞家大**,是未婚妻;不需要时,
我就是那块可以随意丢弃、砸烂、碾成粉末的垃圾。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无声地笑了。
上一世,我就是听了这些鬼话,真的信了傅砚舟的深情,信了我哥的无奈。
直到我像一条狗一样被囚禁在别墅的阁楼里,看着纪清蕊穿着我设计的西装,
戴着我母亲的遗物,宣布她腹中的孩子将是虞家唯一的继承人。
直到我那个忠心耿耿的助理阿兰,被打得半死,也要爬到我面前,告诉我真相。
当初傅砚舟急性溶血症,需要极其稀有的Rh阴性血。是我,虞晚,瞒着所有人,
一次次地躺在冰冷的病床上,把自己的血输给他。纪清蕊,不过是在他清醒前一刻,
哭着握住他的手,演了一场“救命恩人”的戏。我好恨。我恨得五脏六腑都在燃烧。所以,
我制造了一场车祸,开着我那辆定制的劳斯莱斯,连人带轮椅,冲进了滚滚的江水里。
让他们永远找不到我的尸体。让他们午夜梦回,都会被我这张在水里泡得浮肿腐烂的脸,
惊出一身冷汗。而现在。我回来了。这一次,垫脚石,也该换人当当了。2我醒来时,
入目是熟悉的惨白。消毒水的味道像一条毒蛇,钻进我的鼻腔。傅砚舟坐在床边,
下巴上冒出了青涩的胡茬,眼睛里布满了血丝。看见我睁眼,
他脸上迸发出一种像是劫后余生的狂喜,紧紧抓住我的手。“晚晚!你终于醒了!谢天谢地!
”他声音嘶哑,像个没能保护好心爱玩具的孩子一样,眼泪大颗大颗地砸下来。
我哥虞铮也扑了过来,一拳砸在墙上,手背瞬间血肉模糊。“都怪我!是我没保护好妹妹!
我这双手,还留着有什么用!”他说着,竟然真的要去拔旁边医生托盘里的手术刀。演。
真会演。奥斯卡都欠你们一人一座小金人。我虚弱地眨了眨眼,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声音气若游丝:“不怪你们……是我……命不好。”怪我,上辈子眼瞎心盲。爱错了畜生,
信错了**。他们两人神色更加悲痛,对视一眼,傅砚舟小心翼翼地开口,
仿佛怕声音大点就会把我震碎:“晚晚,医生说……爆炸的冲击太大了,
你……你的腿神经受损严重,可能……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他死死盯着我的脸,
捕捉着我每一丝情绪。“但是你放心!这件事,媒体那边我已经封锁了!我不会嫌弃你的,
晚晚,你永远是我最爱的人!”“等你身体好一点,我们就……我们就去国外找最好的医生,
或者……我们领养一个孩子,好不好?”领养一个孩子?是领养纪清蕊肚子里的那个吗?
让我亲手,把害死我的仇人的孩子,养在身边?我的心在冷笑,脸上却是一片茫然。
我缓缓地,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一般,转动着眼珠,看着他们。“你们……是谁?
”两个男人脸上的悲痛,瞬间凝固了。“晚晚,你说什么?”虞铮的声音都在抖。
“我……不认识你们。”我眼神空洞,像个被抽走了灵魂的娃娃,
“我的腿……没有感觉……这是哪里?”他们慌了。手忙脚乱地叫来医生,
做了一系列的检查。最终,
主治医生(我提前花重金买通的)一脸沉重地宣布:“病人因为脑部受到剧烈撞击,
导致选择性失忆,同时伴有认知障碍。简单来说,她不记得你们了,
甚至可能……智力也受到了影响。”傅砚舟和虞铮的脸色,比死了爹还难看。
他们要的是一个听话、顺从、能被他们掌控的废人。不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需要人从头教起的傻子。看着他们眼中的惊疑、失望、甚至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烦躁,
我闭上眼,在心里笑出了声。真好。这场戏,总算可以,换我来导了。
3我被接回了那栋熟悉的别墅。不是我曾经的主卧,而是三楼一间朝北的客房,阴冷、潮湿,
像一座精致的牢笼。傅砚舟的解释是:“主卧采光太好,医生说你现在需要静养,
不能被强光**。”多么体贴入微的借口。上一世,他们就是这样,把我扔在这里,
任由我的伤口发炎、溃烂,高烧不退。而主卧里,傅砚舟和纪清蕊夜夜笙歌,
笑声能穿透整个楼板。这次,我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像个真正的痴呆儿,不哭不闹。
纪清蕊很快就来了。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连衣裙,挺着微微隆起的小腹,
脸上挂着纯洁无瑕的担忧。“晚晚姐,你还好吗?我听砚舟哥说你……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好担心你。”她说着,就要来拉我的手。在她碰到我的前一秒,我像是受惊的兔子一样,
猛地缩回手,嘴里发出一连串意义不明的尖叫。“啊!走开!走开!
”傅砚舟和虞铮立刻冲了进来。纪清蕊已经泪眼婆娑地躲进了傅砚舟怀里:“砚舟哥,
我……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看看姐姐,她好像很怕我……”傅砚舟心疼地搂着她,
看向我的眼神,第一次没了伪装的耐心,只剩下冰冷的斥责。“虞晚!你闹够了没有!
清蕊是关心你,你发什么疯!”虞铮也皱着眉,语气里满是失望:“晚晚,
你怎么能这么对清蕊,她肚子里还有孩子,吓到她怎么办?”我看着他们三个。
多么和谐的一家三口啊。我,虞晚,才是那个不合时宜的外人,那个疯疯癫癫的闯入者。
我停止了尖叫,呆呆地看着傅砚舟脖子上那个崭新的、暧昧的红痕。然后,我抬起手,
指着他,吐出两个字:“脏。”傅砚舟的脸,瞬间黑如锅底。
他猛地把纪清蕊往虞铮怀里一推,上前一步,像是要掐死我。“你说什么?
”“脏……你脏……”我像是学舌的鹦鹉,执拗地重复着,然后蜷缩进被子里,瑟瑟发抖,
“我怕……出去……你们都出去……”虞铮拉住了暴怒的傅砚舟。“算了,
她现在脑子不清楚,你跟她计较什么。”他们走了。
我能听到傅砚舟在门外压抑的怒吼和纪清蕊嘤嘤的哭泣。“你看她那样子!就是个疯子!
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娶她!”“砚舟哥,你别生气了,
姐姐她也是可怜……”门外安静下来后。我的助理阿兰,被一个保镖推了进来。
她脸上带着伤,看到我的瞬间,眼眶就红了。“**……”她扑到我床边,压低声音,
快得像是在赶时间,“这是先生和太太留给您的那份海外信托文件,我拼死藏起来了,
他们还没找到!”她从袖子里掏出一个U盘,塞进我的枕头底下。“还有,
我已经联系上了您之前资助过的那个……瑞金医院的李主任,他会想办法帮您!”“**,
您一定要撑住!”我看着她,眼神依旧空洞。但藏在被子里的手,
却死死地握住了那个小小的U盘。这,才是我为他们准备的,第一份大礼。
4我的“病情”时好时坏。大部分时间,我都像个自闭的儿童,抱着一个娃娃,
一坐就是一天。偶尔,我会突然尖叫,把昂贵的餐具扫落在地,指着所有人喊“坏人”。
傅砚舟和虞铮的耐心,正在被一点点耗尽。他们请来了全城最好的精神科医生,
给我做了一轮又一轮的评估。而我,
则完美地扮演着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伴随严重认知倒退”的病人。医生得出的结论,
正中他们的下怀:我已经不具备任何民事行为能力。这意味着,我名下所有的资产,
包括虞氏集团那百分之三十的原始股,
都可以由我的“监护人”——我的丈夫傅砚舟和兄长虞铮,全权代管。
股东大会重新召开的那天,天气晴好。我被阿兰用轮椅推到了落地窗前,像个展品一样,
沐浴着阳光。楼下,傅砚舟和虞铮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地走向专车。
纪清蕊穿着一身藕粉色的香奈儿套装,站在车边,柔情款款地为傅砚舟整理着领带,
踮起脚尖在他唇上印下一个吻。多么刺眼。多么像一幅完美的、戳进我眼球里的全家福。
“**,”阿兰在我身后,声音平静,“都安排好了。您之前让我联系的那些‘记者’朋友,
已经全部就位。
”“那份您亲自操刀的、关于傅砚舟和虞铮这些年如何利用虞氏集团的海外账户,
做空对手公司、转移资产的做空报告,也已经人手一份了。”“只等您一声令下。
”我看着楼下那辆黑色的宾利绝尘而去,脸上慢慢露出了一个,痴傻的,纯真的笑容。
“阿兰,”我轻声说,“你说,烟花……什么时候放,才最漂亮?”阿兰笑了:“当然是,
在所有人,都看得见的时候。”我点点头,像个得到糖果的孩子。“嗯,那就……开始吧。
”就在傅砚舟和虞铮春风得意地走进股东大会会场,
准备宣布他们“代管”我所有股权的决定时。会场外,
忽然涌入了数十名扛着长枪短炮的财经记者。闪光灯像密集的子弹一样,向他们扫射过来。
“傅总!虞副总!请问网上流传的这份,
指控你们涉嫌巨额职务侵占、恶意做空、内幕交易的报告,是真的吗?
”“请问虞氏集团在巴拿马的离岸公司,是否是为了方便你们洗钱?
”“听说虞**的‘意外’也和你们有关,是为了侵占她的财产,请问你们有何回应?!
”傅砚舟和虞铮的脸,在那一瞬间,白得像纸。5丑闻像病毒一样,
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商界。虞氏集团的股价,开盘即跌停。傅砚舟和虞铮焦头烂额,
被董事会和**的人轮番盘问,狼狈得像两条丧家之犬。他们终于想起了我。当晚,
别墅的门被狠狠撞开。傅砚舟一身酒气,双眼赤红,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野兽。
他冲到我的床前,一把掀开我的被子,将我从床上粗暴地拎了起来。“是你!是你做的,
对不对!”他怒吼着,力气大得几乎要捏碎我的骨头,“你根本就没傻!你一直在耍我们!
”虞铮跟在后面,脸色铁青,他一把抓住傅砚舟的手腕。“砚舟你冷静点!她一个残废,
能做什么!”“残废?”傅砚舟疯了似的笑了起来,他指着我的脸,“你看看她!
你看她那眼神!哪里像个傻子!我们都被她骗了!”他把我狠狠地掼在地上,
冰冷的地板硌得我浑身生疼。可我的脸上,却依旧挂着那种天真无邪的笑容。我抬起头,
看着他,歪了歪脑袋,口齿不清地说:“疼……叔叔,你弄疼我了……”这一声“叔叔”,
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了傅砚舟的怒火上。他怔住了,眼中的疯狂慢慢褪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深的恐惧和怀疑。难道……真的不是她?她已经废了,又傻了,
怎么可能有能力策划这一切?虞铮把我从地上抱起来,放回床上,
动作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他看着我,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一丝恳求:“晚晚,
你告诉哥哥,那些东西……到底是谁给记者的?你是不是……见过什么人?”我摇摇头,
抓着我的小熊玩偶,缩在床角。“没有……晚晚谁都没见……晚晚乖……”就在这时,
纪清蕊白着一张脸冲了进来,手里举着她的手机。“砚舟哥!哥哥!不好了!
我们的孩子……网上有人爆料,说……说他根本不是虞家的血脉!
说我是故意怀孕来骗取虞家财产的!”她哭得梨花带雨,下一秒,双腿一软,
就那么直挺挺地晕了过去。“清蕊!”傅砚舟和虞铮同时惊呼出声,也顾不上我了,
手忙脚乱地抱起纪清蕊就往外冲。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门口的背影,脸上的傻笑,
终于一点点地收敛起来。我慢慢地,慢慢地,从轮椅的夹层里,抽出了一份文件。
那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纪清蕊腹中的孩子,与傅砚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