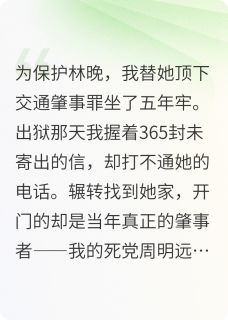
为保护林晚,我替她顶下交通肇事罪坐了五年牢。出狱那天我握着365封未寄出的信,
却打不通她的电话。辗转找到她家,开门的却是当年真正的肇事者——我的死党周明远。
“她现在是我太太,儿子都三岁了。”他笑着递来喜糖。我浑浑噩噩离开,
却在垃圾堆看到今天的报纸头条:《周氏总裁自曝五年前旧事:年少轻狂车祸,
挚友义气顶罪》。手机突然响起,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我狂奔回老家,只看到一座新坟。
---铁门在身后合拢时,那一声沉重的“哐当”像是直接砸在我的脊椎骨上。阳光,
白得刺眼,带着一种久别重逢的陌生蛮横,兜头浇下,烫得皮肤微微发痛。
我下意识地抬起手背挡在额前,指缝间漏下的光线切割着眼前空旷的水泥地坪。风是自由的,
带着远处野草和尘土的气息,卷过裤脚,
吹得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硬、褪色严重的旧夹克空荡荡地晃。五年。两千多个日夜,
就锁在那方寸之地,被高墙电网切割成单调的灰白格子。时间在里面流淌得黏稠而滞重,
每一秒都带着铁锈和消毒水的味道。支撑我熬过那些漫长而窒息夜晚的,只有两个字:林晚。
她的名字是刻在骨头缝里的烙印,是支撑我脊梁不至于彻底垮塌的唯一支柱。
我替她扛下了那场改变一切的车祸——那场该死的、失控的、最终撞向路人的惨剧。
方向盘后本应是她的手,惊恐的尖叫划破夜色的也是她。我冲过去,
把她从驾驶座拖出来塞进副驾,自己坐进去时,冰冷的方向盘硌得掌心发麻。
警笛声由远及近,红蓝的光在车窗上疯狂闪烁,我死死按住想要开口的她,
眼神里的恳求几乎要溢出来:“别出声!信我!”混乱,恐惧,
还有……某种近乎悲壮的决心。那一刻,我只想护住她,像护住一块易碎的琉璃。所有责任,
我担。五年刑期尘埃落定,沉重的镣铐锁住手脚时,
我隔着冰冷的铁栏杆看她哭得撕心裂肺的脸,心里竟还有一丝不合时宜的暖意。值得,
为了她,什么都值得。监狱里的日子,是能把人熬成灰的。高墙隔绝了整个世界,
只剩下单调的哨声、沉重的脚步声和无休止的压抑。唯一的光,是每天短暂的放风时间,
仰望那一小片被铁丝网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我开始写信。
用监狱里那种粗糙发黄的劣质信纸,用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的力道。一天一封,从未间断。
写给林晚。写高墙外的云今天是什么形状,写放风时看到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鸟,
写同仓那个老犯人讲的他年轻时的荒唐事,
写食堂永远煮不烂的豆子硌得牙疼……更多的是写思念,写回忆,
写我们那些微不足道却足以点亮整个囚笼的过往。写她第一次笨手笨脚给我煮糊的面,
写她笑起来时眼角弯起的弧度,写我们挤在狭小的出租屋里看一部老掉牙的电影,
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每一笔,每一划,都蘸着蚀骨的思念和熬过明天的勇气。
365封信。厚厚的一沓,用监狱里发的、洗得发白的旧毛巾仔细包好,
此刻正沉甸甸地压在我单薄的夹克内袋里,紧贴着心脏的位置。我能感觉到它们粗糙的边缘,
像一个滚烫的承诺,一个支撑我走到此刻的锚点。五年了,我终于出来了。林晚,我回来了。
几乎是凭着本能,我走向监狱大门外那个孤零零矗立在风中的、锈迹斑斑的公用电话亭。
金属投币口冰凉。我颤抖着手,
从裤兜最深处抠出仅有的几枚硬币——出狱时狱警塞还给我的可怜家当。
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将那枚冰冷的硬币塞进投币口。
“嘟……嘟……嘟……”听筒里传来的忙音,空洞而机械,像一根冰冷的针,
毫无预兆地刺穿了我胸腔里鼓胀了五年的热气球。预想中林晚带着哭腔或惊喜的“喂?
”没有出现。只有这单调重复的忙音,一遍又一遍,在寂静的电话亭里被无限放大,
撞击着我的耳膜。不可能。一定是她换了号码,还没来得及告诉我。对,一定是这样。
我用力甩甩头,试图驱散心头那丝骤然升起的寒意。手指却不听使唤地再次拨号,
更加用力地按下每一个数字键,指甲敲在坚硬的塑料按键上,发出急促的“哒哒”声。
“嘟……嘟……嘟……”还是忙音。冰冷的,毫无回应的。硬币耗尽,通话被强制切断。
我握着突然沉寂下来的听筒,里面只剩下电流微弱的“滋滋”声。一股巨大的茫然攫住了我。
阳光依旧刺眼,风还在吹,可世界仿佛在瞬间失去了声音和色彩。五年牢狱,
我从未像此刻这般,感到彻骨的孤立无援。去哪里?我站在陌生的街边,
看着车水马龙呼啸而过。五年前熟悉的城市地标,如今被更高更冷的玻璃幕墙取代,
霓虹闪烁,带着一种拒人千里的冰冷繁华。我像个闯入者,格格不入。身上的旧夹克,
脚上磨得发白的解放鞋,还有眉宇间洗刷不掉的、属于“里面”的痕迹,
引来路人或好奇或嫌恶的短暂一瞥。茫然无措间,
一个模糊的地址碎片猛地闪过脑海——林晚曾无意中提过一句,她家在城西某个高档小区,
叫“云栖苑”?当时她语气里带着向往,说那是周明远家开发的楼盘。
周明远……我曾经的死党,家境优渥的公子哥。林晚那时常和我提起他,语气熟稔。
心口莫名地紧了一下,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凭着这点模糊的记忆碎片,
我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在庞大的城市里乱撞。问路时,对方看到我的穿着和神情,
眼神里的戒备和敷衍毫不掩饰。公交车坐过了站,又徒步走了很久。
高楼大厦渐渐被修剪整齐的绿植和低密度的别墅群取代。空气似乎都变得不同,
带着昂贵的植物清香和绝对的安静。终于,在一片精心规划的园林深处,
我看到了那个气派的大门——“云栖苑”。纯铜的大门紧闭着,门卫穿着笔挺的制服,
眼神锐利得像鹰隼。他上下打量着我,那目光如同实质,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和鄙夷,
仿佛在评估一件闯入富人区的垃圾。“找谁?”声音冷硬,没有丝毫温度。“林晚。
”我报出这个名字,喉咙干涩得发紧。“请问林晚住哪一栋?”门卫皱起眉,
眼神里的轻蔑更浓了:“林晚?没这个人。业主名单里没有。”“不可能!”我脱口而出,
声音因为急切而显得有些嘶哑,“她以前说过住这里!麻烦您再查查?或者……周明远?
周明远家总在这里吧?”听到“周明远”三个字,门卫的眼神明显变了一下,
从单纯的鄙夷转为一种微妙的警惕和探究。他再次审视了我一遍,像是在确认什么,
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丁点,但依旧疏离:“周先生?你是他什么人?”“……朋友。
”我艰难地吐出这两个字,感觉舌尖都带着铁锈味。五年牢狱,
早已磨平了我所有的棱角和底气。门卫拿起内部对讲机,低声说了几句,眼神不时瞟向我。
放下对讲机,他指了指大门旁侧一个不起眼的、供访客登记的小门房:“等着吧。
周先生家有人出来接。”等待的时间无比漫长。我站在门房狭小的阴影里,局促不安。
高档小区特有的、带着花香和昂贵建材气味的空气包裹着我,却只让我感到窒息。
内袋里那沓信纸的边缘,似乎变得格外硌人。不知过了多久,一辆低沉的引擎声由远及近,
打破了这片区域的宁静。一辆线条流畅、光泽锃亮的黑色轿车无声地滑到门禁前停下,
车窗缓缓降下。驾驶座上,露出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是周明远。五年时光似乎格外优待他。
精心打理过的发型一丝不苟,脸庞比记忆中更显成熟,也更具棱角。剪裁合体的深色衬衫,
袖口随意地挽起一截,露出价值不菲的手表。
他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成功人士特有的、养尊处优的从容气场。看到我,
他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随即被一种更深的、带着玩味的笑意取代。“陈默?
”他开口,声音清朗,带着惯有的、能轻易拉近距离的熟稔腔调,“真的是你?今天出来?
”车门打开,他迈步下车。锃亮的皮鞋踩在光洁的路面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他朝我走来,
步履从容,带着一种主人般的姿态。
他的目光在我身上那件破旧的夹克和解放鞋上停留了一瞬,那眼神里没有明显的鄙夷,
却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洞悉一切的怜悯。“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他笑着问,
语气轻松得像是在问候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友。那笑容很标准,露出洁白的牙齿,
却像一张精心描画的面具,透着骨子里的疏离和虚假。我张了张嘴,
喉咙像被砂纸磨过:“我……我找林晚。”声音干涩得几乎不成调。
周明远脸上的笑容更深了,甚至带上了一丝奇异的、难以言喻的满足感。他微微侧身,
朝着那扇紧闭的、雕花精美的别墅大门方向抬了抬下巴,姿态优雅而笃定。
“林晚啊……”他拖长了调子,像是在品味这个名字,“她现在是我太太。”他顿了顿,
欣赏着我瞬间僵住的表情,嘴角的笑意加深,“儿子都三岁了,刚上幼儿园。”每一个字,
都像一把烧红的钝刀子,狠狠捅进我的胸腔,然后残忍地搅动。嗡的一声,大脑一片空白。
世界瞬间失声,只剩下他清晰的话语在耳边反复回荡。
“我太太……儿子……三岁……”五年?我坐了五年牢!林晚的孩子三岁?
时间线像一条冰冷的毒蛇,瞬间缠紧了我的心脏,带来窒息般的剧痛和荒谬感。这不可能!
一定是哪里错了!我替她顶罪时,她明明……“喏,
”周明远仿佛没看到我惨白的脸色和摇摇欲坠的身体,他变戏法似的,
从西装内侧口袋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打开,里面是几颗包装鲜艳的糖果,“喜糖。
一直想给你送去,可惜没机会。今天正好,补上。”他拈起一颗,用两根手指优雅地夹着,
递到我面前。那糖果的包装在阳光下闪着廉价而刺眼的光,像是对我五年付出最恶毒的嘲讽。
我盯着那颗糖,视线模糊,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一股腥甜猛地涌上喉咙口。我死死咬住牙关,
才没有当场失态。身体里的力气仿佛被瞬间抽干,连抬手的动作都变得无比艰难。
我几乎是凭着本能,僵硬地、极其缓慢地抬起手。指尖触碰到那颗糖光滑冰冷的包装纸时,
像被毒蛇的信子舔过。我猛地一缩手,仿佛被烫到。糖果掉落在脚下的尘埃里,滚了两圈,
沾满了灰。周明远脸上的笑容终于淡去了一瞬,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霾,
随即又被更浓的、带着施舍意味的虚假笑容覆盖。他无所谓地耸耸肩,收回手,
仿佛丢掉了一件垃圾。“看来心情不太好?也难怪,刚出来嘛。”他语气轻松,
像是在谈论天气,“既然来了,要不要进去坐坐?看看我们家?林晚她……”他故意顿了顿,
目光带着探究和戏谑,“今天刚好带儿子去上早教课了,不在家。真不巧。”“不用了。
”这三个字仿佛是从我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血腥味。我猛地转身,几乎是踉跄着逃离。
背后那道带着笑意的、冰冷的目光,像芒刺一样扎在我的脊背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片富人区的。双腿沉重得像灌满了铅,每一步都踩在虚空里。
眼前的景象光怪陆离地晃动、旋转,高楼、行人、车辆都扭曲变形,模糊成一片刺眼的色块。
耳边嗡嗡作响,周明远那轻描淡写的话语和林晚哭泣的脸庞在脑中疯狂撕扯、重叠。
“我太太……儿子三岁了……”“别出声!信我!”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
那场车祸……那场让我失去五年自由、背负一生污点的车祸!方向盘后坐着的,
真的是林晚吗?还是……那个此刻正志得意满享受着娇妻幼子的周明远?一个可怕的念头,
像冰冷的毒液,瞬间流遍全身,冻僵了四肢百骸。我替谁坐了牢?我拼死守护的,
究竟是一个无辜的爱人,还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把我推向深渊的阴谋?巨大的眩晕感袭来,
我再也支撑不住,膝盖一软,猛地扶住了旁边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
是街角一个巨大的、散发着恶臭的绿色垃圾箱。油腻的污渍蹭在了我的袖口上,
令人作呕的气味直冲鼻腔。胃里翻腾得更厉害了,我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
却什么也吐不出,只有酸涩的胆汁灼烧着喉咙。冷汗瞬间浸透了破旧的夹克,
黏腻地贴在背上。就在这时,垃圾箱敞开的盖口边缘,一张被揉皱、沾满油污的报纸一角,
突兀地闯入了我模糊的视线。那报纸的头版位置,一张清晰无比的、熟悉得刺眼的照片,
如同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我的视网膜上!照片上的人,正是周明远。
他穿着考究的西装,站在一个灯光璀璨的发布会背景板前,面带自信从容的微笑,
正对着无数话筒侃侃而谈。那姿态,俨然是聚光灯下的成功人士,人生赢家。而照片上方,
一行加粗的、巨大的、血红刺目的标题,像一把淬毒的匕首,
准地捅穿了我最后一丝摇摇欲坠的理智:**【周氏总裁自曝五年前旧事:年少轻狂酿车祸,
挚友义气挺身顶罪】**年少轻狂?挚友义气?这几个字在我眼前疯狂跳动、放大,
每一个笔画都带着狰狞的嘲讽和淋漓的鲜血!
年少轻狂……所以那场导致无辜路人重伤、改变我一生轨迹的车祸,在他口中,
只是轻飘飘的“年少轻狂”?挚友义气……所以我这五年的牢狱之灾、身败名裂、前途尽毁,
在他口中,成了彰显他个人魅力的“义气”?成了他如今站在高处、博取掌声和同情的谈资?
!“轰——!”脑子里像引爆了一颗炸弹。所有的声音、色彩、感知瞬间被撕得粉碎。
世界彻底陷入一片死寂的、刺眼的白光。心脏像是被一只巨手狠狠攥住、捏爆,
剧烈的绞痛从胸腔炸开,瞬间蔓延到四肢百骸。喉咙里涌上浓重的铁锈味,眼前阵阵发黑。
我死死地盯着那张报纸,眼球像是要瞪出血来。照片上周明远那张志得意满的笑脸,
仿佛在无声地嘲笑我的愚蠢、我的牺牲、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和彻头彻尾的失败!
原来……原来如此!原来所谓的“保护”,从一开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林晚……周明远……他们联手,把我推下深渊,然后踩着我的尸骨,
享受着他们的荣华富贵和美满人生!而我,像个彻头彻尾的傻瓜,还在那不见天日的牢房里,
一天一封地写着那些可笑的、寄托着所有思念的信!“呃啊——!
”一声野兽濒死般的嘶吼终于冲破喉咙,却因为剧烈的颤抖和窒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