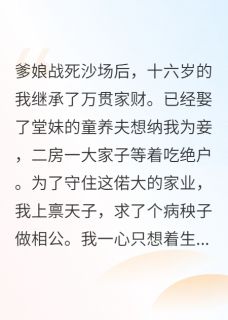
白芙蕖母女陷害我一事人证物证俱全,起初她们还狡辩,受了刑后都老实了。
她们大抵知道此次难逃一劫,不敢连累二房其他人,谁也没供出来就认了罪。
最终白芙蕖母女并春桃、福全四人被处斩。
李择明虽然未受牵连,可当日那般情景被人撞破,他也无颜见人。
只好告了病假,终日闭门不出。
二房乱成了一锅粥,老夫人病得卧床不起,我那二叔在朝堂之上被御史骂得抬不起头。
但听说五皇子外祖赵太师一派的朝臣都在为二叔说话,和御史台那帮人吵得不可开交。
与此同时,白府的暗桩传信给我,二叔近日常夜访五皇子府,许久才离开。
五皇子仍被禁足,此时为避嫌,与二叔划清界限才是上策。
此举属实耐人寻味,除非二叔于他还有用处,或者……他有把柄在二叔手上?
我按下心中思绪,吩咐暗桩盯紧二叔,若有异动,即刻禀告。
我心中不安,总觉得或许还有大事发生。
这种不安持续到了夜间,谢珣没有回房。
谢珣身子不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以休养为由与我分房而睡。
少则两三日,多则半个月,其间闭门不出,除了请脉的太医,谁也不肯见。
近段时间更频繁了些,且白日朝堂出了事,夜里谢珣就病了。
我心中总是不安。
趁天色不算晚,我亲自做了碗甜羹给谢珣送去。
谢珣的贴身侍卫拦在门外,「夫人请回吧,殿下睡了。」
我软了语气求他,「我放心不下,想进去看一眼,殿下无碍我也就放心了。就看一眼,绝不
打扰殿下歇息,你看成吗?」
侍卫拦在门前,屹然不动,「夫人还是不要为难属下。」
听夏不满,要上前理论。
我拦住她,「罢了,先回去吧。」
闻冬伺候我梳洗,见铜镜中的我愁眉不展,问道:「姑娘在担心什么?」
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只是心中不安,这朝中局势复杂,怕是有异变。」
闻冬神情严肃起来,「三皇子向来远离朝堂纷争,即便局势有变,也应当牵连不到咱们。」
我叹口气,「可我担心皇后,她恐怕不会放过我。」
闻冬宽慰我。
「如今五皇子被罚,皇后自顾不暇,又如何寻您的麻烦?
「再者您是功臣遗属,如今又是皇子妃,只要寻不到错处,皇后也不敢明面上为难您。
「即便是在暗处使劲儿,我与听夏总会护着您的。」
我握住闻冬的手,发自内心感叹,「幸好还有你和听夏,我才不至于感到孤立无援。」
